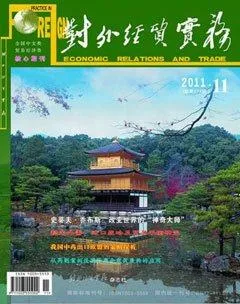美國債務危機及其影響分析
美國債務危機持續發酵,已成為國際焦點問題。本文謹探討美國債務危機的基本概念,探究危機的成因,并分析上述危機對世界經濟及我國發展戰略的影響。
一、美國債務與債務危機
(一)美國外債基本構成
美國對外債務由政府債務、公司債務和美國居民的債務三大部分組成。據統計,美國目前14.3萬億美元的公共債務系指聯邦政府的負債,并未涵蓋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約2.5萬億美元的債務規模,以及房利美和房地美等得到政府信用擔保的“政府支持企業”約6.6萬億美元的債務。
從債務構成情況看,美國現有公共債務里,約4.45萬億美元由外國投資者持有,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單一債務持有國,占12%左右。美聯儲是僅次于中國的第二大美國債持有主體,持有額占10%左右。由此可見,美國國債中有將近70%由美國政府或本國投資者持有。從債務規模看,在2010年美國聯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居民、非金融企業的總債務共計約36萬億美元,相當于同年GDP的246%。據美財政部統計,2008年以來,聯邦政府為實施緊急救助和刺激經濟復蘇,導致國債陡增5萬億美元之多。再加上金融部門共14萬億美元的債務(內含“政府支持企業”約6.6萬億美元的債務),美國債務規模超過50萬億美元,占GDP的比重約為343%。進而言之,美國還存在大量隱性債務。美國長期實行高福利政策,以期維持和促進社會穩定。隨著美國人口不斷擴張,隨著老年人口比重不斷增加,美國在社保基金、醫療保險等領域負債經營狀況愈發嚴重。據美國勞工部統計,2010年,全國范圍社保基金隱性負債多達13.5萬億美元,醫療保險隱性負債則高達85.7萬億美元,兩者相加,政府隱性總負債高達102萬億美元。
(二)美國債務特點
目前看來,美國債務主要呈現下列特點:
其一,隱形債務規模龐大。觀察美國債務風險大小,不僅要其聯邦政府負債,而且要看地方政府、居民、非金融企業和金融機構負債;不僅要觀察現有債務規模,而且要看其增長態勢。這是因為,債務危機一旦爆發,所有部門的債務風險會迅速轉化為主權債務風險,進而推高美國政府和機構的融資成本,導致信貸萎縮,驅使經濟下行。據美國政府前總審計長、美國彼特·皮特森基金會總裁兼執行董事長大衛·沃爾克(Laurence J. Kotlikoff)估計,2007年全球GDP大約54.3萬億,也就是說,美國一個國家的債務,已與當年全球GDP總額基本持平。再加上100余萬億美元的隱性債務,美國早已進入破產狀態。
其二,美債增長態勢難以控制。美國于1985年結束了凈債權國長達70年的歷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凈債務國。此后,海外各界持有的美國債券規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2003年至2010年期間,美國外債負債率分別為62.3%、70.4%、75.0%、83.6%、95.4%、95.2%、95.9%和96%。至2010年,美債總額已占全球債務余額的24%左右,且以每年9%的速度上漲。與此同時,美國常年可持續的經濟增速僅有3%。更為重要的是,二戰以來形成的7,800萬嬰兒潮人口均已進入高齡狀態。據美國勞工部數據,未來15至20年間,美國政府每年需要支付養老金人均40,000美元,年均總量3萬億美元。因此,美國經濟遲早會受債務危機牽連。
其三,美國償債能力難有保障。依據國際慣例,美國需要在每個財年內將其外債的還本付息額占當年或上一年出口收匯額的比率控制在20%以下。據美國商務部數據,2010年12月,美國對外貿易總額3665.1億美元。其中,出口1629.6億美元,進口2035.5億美元,逆差405.8億美元。服務貿易方面,進出口總額798.3億美元,出口464.1億美元,進口334.2億美元,順差129.8億美元。從財政收入方面看,2001年至2010年間,美國財政收入每年基本穩定在20,000萬億美元的水平,其中一半左右需要依法支付國民的福利開支,因此政府歷年需要大量舉新債,還舊債。從這個意義上說,高福利開支,尤其是養老金缺口將構成未來美債的黑洞,遲早將拖垮美國經濟和債務清償能力。美國債務總量已經大大超出政府的實際支撐能力,債務危機已經到達必須加以解決的地步。
二、美國債務危機成因分析
(一)經濟全球化因素
經濟全球化先后通過資本鏈將生產和服務網絡推向全球范圍,進而通過信息網絡在全球范圍配置資源組織生產與銷售,最終通過金融創新將衍生產品的銷售推向實施對外開放的所有國家和經濟體。在整個全球化進程中,美國主導并且充分利用全球生產與消費領域的信用革命,將世界經濟與本國的資本、貨物、技術和信息市場融合在一起,將全球信用關系融入到本國經濟與社會再生產的全部過程,最終通過債務關系主導和影響全球宏觀經濟的發展趨勢。正是在上述全球化經濟發展態勢作用下,發生在美國的金融危機很快釀成國際金融危機,并且由虛擬經濟蔓延至實體經濟,進而致使許多國家陷入主權債務危機,最終美國也未能幸免。
歷史地看,誘發這場仍在擴散的主權債務危機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創新,而這場金融創新的發源地是美國。為滿足資本擴張對消費擴張的需求,美國金融業長期呈現畸形發展狀態,導致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嚴重脫節。與此同時,美國金融當局與政府部門受本國經濟發展利益驅使,對金融創新疏于監管,導致衍生品市場交易泛濫。以房地產領域次級住房貸款為例,在金融機構層層創新和保障下,原先每單元僅值100美元的產品,通過證券杠桿最終放大到5,000至10,000美元。起先總額僅僅數千億美元的問題次級貸款,經過層層包裝形成金融衍生投資品,在全球范圍流通,每個單元的衍生產品被交易N多次,最終在金融市場被放大成幾萬億美元的有毒資產窟窿。正是這個窟窿,最終引發了國際金融危機,迫使政府實施全面緊急救助,并將美國再度拖向債務危機邊緣。
(二)國際貨幣制度因素
美元和美債構成是推動美國經濟運行的兩個車輪。依據美國憲法,美國政府不能發行美元,只能通過發行國債進行融資。與此同時,美聯儲也不能任意發行美元,而必須依據購買國債的數量發行相應數量的美元。因此,美元本位制實質上成為美債本位制。在這個體制下,美國通過印刷美元輕而易舉地從全球范圍獲得勞動力、商品、資源和市場,而世界各國則用對外貿易獲得的美元購買美債和美元金融資產,進而為美國債務融資提供資金來源。就這樣,上述狀態周而復始,從二戰結束以來一直延續至今。美國通過美元和美債把全球經濟牢牢地捆綁在一起,基本上納入到本國債務循環之中,通過貨幣發行獲得“鑄幣稅”,通過利率獲取“通脹稅”,并通過匯率變動相應“寫掉”本國的外債。同時,美國推行的經濟、財政與金融政策也不時將美國推向債務危機邊緣。
(三)政黨政治因素
美國國會的立法制度從根本上制約了政府控制債務的能力。在現行委員會制度下,每個委員會及其相關成員對諸多法案擁有生殺大權。各委員會成員出于選區利益或集團利益考慮,經常在諸多法案中搭載與本選區相關的發展項目條款,并且利用法案審議規則形成相互支持對方提案的“選票交換”制度。例如,不同的委員會今天會聯手支持農業委員會提出的關于提高農業補貼的法案,明天又會聯手支持退伍老兵事務委員會提出的關于提高退伍軍人醫療保險的法案。其結果,大量“民意和民生工程”不斷將美國債務推向新的高峰。與此同時,在選舉政治作用下,政府官員和立法成員為迎合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