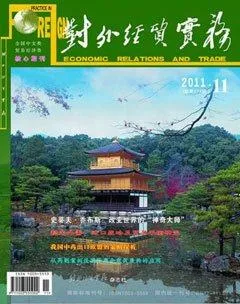歐盟涉華案件中對WTO反傾銷非歧視性原則違反的探討
一、引言
非歧視原則是WTO基本原則之一,但是,它在WTO龐大的法律體系的各個部門法中的具體落實情況卻異常復雜。在WTO反傾銷立法領域,非歧視原則主要通過WTO《反傾銷協議》第9.2條[1]加以規定。根據WTO反傾銷非歧視原則,進口成員方“如果征收反傾銷稅,就應當對己被認定傾銷和造成損害的所有來源(all sources)的進口產品根據每一案件的情況在非歧視基礎上收取適當金額的反傾銷稅,接受價格承諾的產品除外。” 歐盟通過《歐盟反傾銷條例》第9.5條[2]將WTO反傾銷非歧視原則納入其反傾銷法律體系,要求“反傾銷稅在各種情況下都應當以適當的數額進行征收,并對被認定傾銷和引起損害的任何國家進口的產品采取不歧視的原則,除非進口是來自那些根據本規則的條款其價格承諾已被接受的國家”。
縱觀GATT/WTO反傾銷爭端解決史,涉及WTO《反傾銷協議》第9.2條的爭議并不多。但是,近年來隨著中歐貿易、投資關系發展,中歐之間涉及該條的爭端呈現出增加之勢。[3]本文所要討論的案件是,2008年年底慈溪江南化纖有限責任公司等八家中國進出口商會成員在歐盟初審法院狀告歐盟理事會違反《歐盟反傾銷條例》的9.5條和WTO《反傾銷協議》第9.2條所確立的非歧視原則(本文簡稱聚酯短纖案)。本案審理進程的緩慢并不影響筆者依據該案原告的起訴書和被告在反傾銷調查中形成的相關文件為研究材料,探討歐盟反傾銷立法與WTO非歧視原則之間存在的沖突以及對形成WTO反傾銷非歧視原則核心內容的WTO《反傾銷協議》第9.2條的解釋進行探討。
二、聚酯短纖案案由
近20年來,歐盟對輸歐聚酯短纖發起了為數眾多的反傾銷調查并采取了相應措施,調查范圍涉及到中國大陸、中國臺灣、美國、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韓國、馬來西亞、墨西哥、羅馬尼亞、沙特阿拉伯、泰國和土耳其等WTO成員方。但是,歐盟在采取反傾銷措施環節,并不對在同時接受調查的涉案產品一視同仁。
在歐盟進行的某些反傾銷調查中,雖然針對不同WTO成員方輸歐聚酯短纖的反傾銷調查發起調查的時間存在差異,但是,由于前后案件的時間上的重疊,致使出現在某一時段數個不同WTO成員方輸歐聚酯短纖同時被采取反傾銷措施的情形(出口承諾除外)。2003年12月19日歐盟委員會發布反傾銷調查公告,決定對源自中國大陸和沙特阿拉伯的聚酯短纖展開反傾銷調查并同時依據《歐盟反傾銷條例》第11.3條決定對源自臺灣地區和韓國的聚酯短纖啟動臨時復審調查。2005年3月10日,歐盟理事會作出終裁,對聚酯短纖案的八家原告征收稅率從24.6%到49.7%不等的反傾銷稅并同時宣布終止對臺灣地區的臨時復審調查程序。2006年4月12日,歐盟委員會應申請啟動對源自馬來西亞和臺灣地區的聚酯短纖發起反傾銷調查并對源自馬來西亞的聚酯短纖征收稅率從12.2%到23%不等的臨時反傾銷稅,對源自臺灣地區的聚酯短纖征收稅率為29.5%的臨時反傾銷稅。可見,自歐盟對馬來西亞和中國臺灣輸歐聚酯短纖被采取反傾銷措施起,中國大陸、沙特阿拉伯、馬來西亞和中國臺灣都同時被采取反傾銷措施。
歐盟對于同時被采取反傾銷措施的聚酯短纖區分不同的來源地,以其區域立法為依據,終止一部分案件的程序,而繼續進行一部分案件的程序,從而形成歧視。2007年5月23日,歐盟委員會在向理事會反傾銷咨詢委員會提交報告的同時向理事會提交建議終止對馬來西亞和臺灣地區聚酯短纖反傾銷調查的建議草案,同日,申請人撤回對馬來西亞和臺灣地區聚酯短纖反傾銷調查的申請。2007年6月19日歐盟委員會依據理事會決議終止了對馬來西亞和臺灣地區聚酯短纖反傾銷調查。鑒于理事會決議終止了對馬來西亞和臺灣地區聚酯短纖反傾銷調查,同年8月30日歐盟委員會依職權提起針對源自中國大陸和沙特阿拉伯等國家聚酯短纖反傾銷調查部分臨時復審依據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來確定是否也終止對源自中國大陸和沙特阿拉伯等國家聚酯短纖反傾銷調查。此間,鑒于歐盟對馬來西亞和臺灣地區聚酯短纖反傾銷調查已經終止,中國進出口商會以WTO反傾銷非歧視原則為依據致函歐盟委員會,要求也立即終止對中國大陸涉案產品的反傾銷措施并與歐盟委員會進行了多次交涉。于是,歐盟委員會只得依職權啟動對中國大陸輸歐聚酯短纖的共同體利益審查。但是,歐盟理事會《第893/2008號條例》作出否定性認定:終止針對源自中國大陸和沙特阿拉伯等國家聚酯短纖所采取的反傾銷措施不符合共同體利益。這樣一來,歐盟一方面在終止了對源自馬來西亞和臺灣地區聚酯短纖的反傾銷調查,一方面繼續對源自中國大陸的聚酯短纖征收反傾銷稅。
中國大陸涉案產品出口商指出,WTO《反傾銷協議》第9.2條和《歐盟反傾銷條例》第9.5條都要求WTO進口成員方“如果征收反傾銷稅,就應當對己被認定傾銷和造成損害的所有來源的進口產品根據每一案件的情況在非歧視基礎上收取適當金額的反傾銷稅,接受價格承諾的產品除外。” 簡言之,依據WTO反傾銷非歧視原則,歐盟要么針對所有已經滿足反傾銷措施要件的輸歐聚酯短纖不分來源地地同時征稅,要么針對所有已經滿足反傾銷措施要件的輸歐聚酯短纖不分來源地地同時終止征稅。就本案而言,既然歐委會已經終止針對馬來西亞和中國臺灣輸歐聚酯短纖采取反傾銷措施,就應當同時終止其針對中國大陸輸歐聚酯短纖的反傾銷措施。否則,即為對WTO反傾銷非歧視原則的違反。
2008年12月8日中國涉案產品出口商慈溪江南化纖有限責任公司等八家中國進出口商會成員就歐盟理事會《第893/2008號條例》涉嫌違反《歐盟反傾銷條例》第9.5條和WTO《反傾銷協議》第9.2條所確立的非歧視原則等相關問題向歐盟初審法院提起訴訟。
三、歐盟對WTO反傾銷非歧視原則的違反
(一)歐盟理事會《第893/2008號條例》違反WTO《反傾銷協議》第9.2條
WTO《反傾銷協議》第9.2條指出,進口成員方“如果征收反傾銷稅,就應當對己被認定傾銷和造成損害的所有來源的進口產品根據每一案件的情況在非歧視基礎上收取適當金額的反傾銷稅,接受價格承諾的產品除外。”根據對本條的文意解釋,我們可以歸納出WTO反傾銷非歧視原則的基本含義。首先,進口產品分別來自不同的WTO成員方。本案原告方認為,“來源”是一個國別概念,即WTO成員方。歐盟也做同樣理解。其次,進口產品已經滿足被采取反傾銷措施要件,即對己被認定傾銷和造成損害,且進口成員方決定征收反傾銷稅。再次,進口成員方根據每一案件的情況在非歧視基礎上收取適當金額的反傾銷稅,接受價格承諾的產品除外。也就是說,進口成員方一旦決定征收反傾銷稅,除了接受價格承諾的出口商外,都應當根據各自傾銷情況征收適當金額的反傾銷稅,不得歧視性地只征收某一來源的產品的反傾銷稅而放棄征收另一來源的產品的反傾銷稅。
聚酯短纖案中,根據WTO反傾銷非歧視原則,歐盟既然已經認定來自馬來西亞、中國臺灣、中國大陸、沙特阿拉伯等WTO成員方的聚酯短纖構成傾銷并對歐盟產業造成損害,并且也不存在達成價格承諾的情況,如果要征收反傾銷稅,就應對所有來源的進口產品當根據每一案件的情況在非歧視基礎上收取適當金額的反傾銷稅,即,對聚酯短纖案的八家原告征收稅率從24.6%到49.7%不等的反傾銷稅,對源自馬來西亞的聚酯短纖征收稅率從12.2%到23%不等的臨時反傾銷稅,對源自中國臺灣的聚酯短纖征收稅率為29.5%的臨時反傾銷稅。然而,歐盟理事會《第893/2008號條例》卻以其區域立法為依據,終止了針對源自馬來西亞和中國臺灣的聚酯短纖的反傾銷措施,而繼續針對源自中國大陸的聚酯短纖的反傾銷措施。可見,歐盟理事會針對構成傾銷并造成損害的相同輸歐產品,根據輸出國家或者地區不同而在采取反傾銷措施時加以區別對待,顯然有悖于WTO《反傾銷協議》第9.2條所確立的WTO反傾銷非歧視原則。
值得指出的是,關于歐盟理事會《第893/2008號條例》是否違反WTO《反傾銷協議》第9.2條,雙方的爭議焦點之一是如何理解條文中“己被認定傾銷和造成損害”的含義。歐盟理事會辯稱,它并未對馬來西亞和中國臺灣輸歐聚酯短纖是否存在傾銷和損害性作出最終認定,因而不構成違反WTO《反傾銷協議》第9.2條。原告認為,在歐盟委員會向理事會提交的針對中國臺灣和馬來西亞不予征稅的建議草案中,歐盟委員會已經證實了其對存在傾銷和損害的認定,而理事會沒有就此作出最終認定的原因在于,申請人撤回了申請而沒有必要作出最終認定。而且,理事會基于公共利益考慮不對中國臺灣和馬來西亞采取反傾銷措施這一事實也表明源自中國臺灣和馬來西亞的涉案產品存在傾銷和損害事實,否則,理事會沒有必要考慮公共利益問題。因此,盡管歐盟理事會沒有對是否存在傾銷和損害性作出最終認定,但是,實際情況表明源自中國臺灣和馬來西亞的涉案產品存在傾銷和損害事實,因而滿足了WTO反傾銷非歧視原則中“已被認定傾銷并造成損害”的要件。筆者認為,這里主要涉及兩個方面的爭議,一是作出認定的時間問題,一是認定的正式程度問題或者認定機關的權威性問題。特別是因WTO各成員方國內反傾銷機構的分工差異而可能使該問題進一步復雜化。
(二 )申請人撤回申請制度與WTO反傾銷非歧視原則之間的沖突
歐盟理事會稱,之所以終止對來源自臺灣和馬來西亞的聚酯短纖實施反傾銷措施,而對中國大陸輸歐聚酯短纖繼續征稅,原因之一是對來自臺灣和馬來西亞的聚酯短纖提起反傾銷調查申請的申請人撤回了調查申請,與此同時,對源自中國大陸的輸歐產品提起反傾銷調查的申請人并未撤回調查申請。《歐盟反傾銷條例》第9.1條規定:“如果反傾銷調查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程序即可終止,除非終止調查程序將不符合共同體利益”,而歐盟理事會通過審查共同體利益,認為終止針對源自臺灣和馬來西亞的聚酯短纖反傾銷程序是符合共同體利益的。可見,歐盟理事會準許反傾銷調查申請人撤回申請的法律依據是《歐盟反傾銷條例》第9.1條。
《歐盟反傾銷條例》第9.1條要求調查機關將“共同體利益”作為限制申請人行駛申請撤回權的唯一法定事由,即一旦調查機關判斷申請人撤回申請符合共同體利益即可終止反傾銷程序,而沒有考慮到程序的終止可能導致對不同來源地的相同產品進口的歧視。所以,《歐盟反傾銷條例》第9.1條規定本身(as such)與WTO反傾銷非歧視原則之間存在沖突,因而,作為系爭措施本身(measure at issue as such)違反WTO反傾銷非歧視原則。
本案中,歐盟理事會《第893/2008號條例》適用《歐盟反傾銷條例》第9.1條的結果,造成了對源自中國大陸的輸歐聚酯短纖的歧視。所以,歐盟理事會《第893/2008號條例》作為《歐盟反傾銷條例》第9.1條的系爭措施的適用(measure at issue as applied)也違反了WTO反傾銷非歧視原則。
(三)共同體利益制度與WTO反傾銷非歧視原則之間的沖突
首先,我們討論歐盟理事會在適用共同體利益條款時對WTO反傾銷非歧視原則的違反。本案中,歐盟理事會依據《歐盟反傾銷條例》第9.1條和第21.1條等有關共同體利益的規定,終止了對部分國家地區產品的反傾銷措施,而繼續對另一部分國家產品采取反傾銷措施。在歐盟法層面,歐盟反傾銷調查機關是依法行事,但是,其行為的結果卻違反了WTO反傾銷非歧視原則。另外,即使是在適用共同體利益條款時,衡量是否符合共同體利益的標準也因當事人撤T3x5RCISUxnX6sA5+mChPQ==回申請和歐盟委員會依職權進行而有所差異。歐盟理事會認為,申請人撤回申請所涉及的共同體利益標準與歐盟委員會依職權進行所涉及的共同體利益標準是不相同的。前者涉及到利益平衡是否如此之積極以至于歐盟委員會原本應該依職權繼續反傾銷程序,即使沒有了申請人的支持。后者涉及到利益平衡是否如此的消極,以至于應當終止采取措施。歐盟采用所謂“積極利益平衡”標準,認為請求對源自臺灣地區和馬來西亞的輸歐產品啟動反傾銷調查的申請人撤回申請符合共同體利益,從而終止了對臺灣和馬來西亞的反傾銷調查程序并退還了業已征收的臨時反傾銷稅;與此相對,在依職權權衡終止對中國大陸涉案產品是否符合共同體利益時,采取了“消極利益平衡”標準。總之,歐盟理事會《第893/2008號條例》作為《歐盟反傾銷條例》第9.1條和第21.1條系爭措施的適用違反了WTO反傾銷非歧視原則。同時,根據“符合國內法的規定不得作為實施違反國際義務的行為的抗辯”這一國際法的基本原理,歐盟理事會不得以其行為符合歐盟區域立法作為其違反WTO反傾銷非歧視原則的抗辯。
至于歐盟理事會《第893/2008號條例》所依據的《歐盟反傾銷條例》第9.1條和第21.1條等有關共同體利益的規定本身的違法性的判斷較之其適用違法性的判斷則要復雜得多。《歐盟反傾銷條例》第9.1條規定,如果反傾銷調查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程序即可終止,除非終止調查程序將不符合共同體利益。《歐盟反傾銷條例》第21.1條規定,如果基于提交的所有信息能夠明確地得出采取此類措施不符合共同體利益的結論,盡管存在傾銷和損害的認定,調查當局可以不采取措施。但是,都沒有對因實施這些條款時如何避免可能造成的歧視性后果作出規定。
我們知道,一方面,將公共利益條款納入各成員方國內立法是WTO所鼓勵的行為。詳言之,WTO《反傾銷協議》第9.1條允許WTO各成員方的國內反傾銷立法納入公共利益條款,旨在減少反傾銷措施的采用,以削弱反傾銷立法可能給國際貿易帶來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落實WTO反傾銷非歧視原則,必然要求對于所有來源是否采取反傾銷措施原則上要一視同仁。WTO反傾銷非歧視原則的位階顯然高于WTO反傾銷領域的公共利益條款的位階,歐盟要避免其共同體利益立法本身違反WTO非歧視原則,只需按其各自的位階作出調整即可。總之,在作出調整之前,歐盟反傾銷公共利益條款立法本身也違反了WTO非歧視原則。
總之,WTO《反傾銷協議》第9.2條在中歐之間貿易爭端之中占據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從國內立法層面看,由于立法技術等種種原因,可能出現其反傾銷具體制度設計與WTO反傾銷非歧視原則之間發生沖突。如,本案歐盟有關申請人撤回申請制度和公共利益制度的規定。再如,《歐盟反傾銷條例》第9.5條有關適用于非市場經濟地位出口商或者生產商的單獨裁決標準規定。但是,隨著中歐貿易爭端解決的推進,WTO《反傾銷協議》第9.2條所建立的反傾銷紀律必須進一步得到澄清和加強。
參考文獻:
[1]如對任何產品征收反傾銷稅,則應對己被認定傾銷和造成損害的所有來源的進口產品根據每一案件的情況在非歧視基礎上收取適當金額的反傾銷稅,來自根據本協定條款提出的價格承諾己被接受的來源的進口產品除外。主管機關應列出有關產品供應商的名稱。但是,如涉及來自同一國家的多個供應商,且不能列出所有供應商的名稱,則主管機關可列出有關供應國的名稱。
[2]反傾銷稅在各種情況下都應當以適當的數額進行征收,并對被認定傾銷和引起損害的任何國家進口的產品采取不歧視的原則,除非進口是來自那些根據本規則的條款其價格承諾已被接受的國家。裁定征收反傾銷稅的決定應對各個出口商指定反傾銷稅;或者,如果這樣不可行,在第2條第7款的情況下,一般來說,應對有關的出口國規定反傾銷稅。
[3]據筆者掌握的資料,迄今為止,WTO爭端解決機制層面僅有中歐之間的反傾銷爭議在實體上涉及到WTO《反傾銷協議》第9.2條。中國政府2009年年底就歐盟對華緊固件反傾銷措施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 ,開了中國通過WTO解決中歐貿易爭端的先河;2010年年初又就歐盟對華皮鞋反傾銷措施訴諸WTO爭端解決機構 。在這兩個案件中,中國均指控歐盟相關立法本身及實施違反了WTO《反傾銷協議》第9.2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