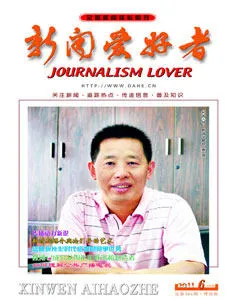新時期小說中的寓言化敘事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活著》(余華)、《爸爸爸》(韓少功)、《小鮑莊》(王安憶)等小說的出現令眾多評論者為之矚目,或歡呼,或指責,褒貶不一。
當論爭的硝煙散去,冷靜反思,這類小說其實預示了一種潮流:即新時期年青一代作家對批判現實主義式的傳統小說敘事正在逐漸失去興趣,突破對現實社會的摹寫,表達具有永恒意味的主題,才是他們共同的追求。因此,寓言化敘事進入他們的創作視野。所謂寓言化敘事,當是指以虛構還原真實,以有限的敘事符號直抵無限深邃的精神彼岸,意在傳達一種被非現實世界所能夠直視的哲理內涵。在中國文學中,寓言化敘事濫觴于先秦,早在孟子、莊子、韓非子等論說文章中,便出現了眾多借寓言故事表達作者思想的表達手法。但在現代小說中,因為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寓言化敘事因其遠離現實而不受重視。所以,直到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新時期小說敘事創新與探索的熱潮中,這種敘事形態才重新浮現。
通過小說來講述生存世界的寓言,以余華、殘雪等為代表。在余華的小說中,命運作為一種殘忍無比的力量,造成了暴力、死亡重復地、循環地發生。《活著》以主人公福貴的苦難一生作為故事線索,真實而深刻地揭示了人的生存困境的荒誕以及人在頹敗不堪的處境中對苦難的承受能力,構筑起一個獨特的關于生存的象征世界。在這部僅僅10萬字的小說里,作者寫了福貴充滿苦難、充滿悖論的一生,父母、妻子、兒子、女兒、女婿、外孫等親人一個個從他身邊離去,死亡在這篇作品中失去了它在傳統話語中固有的道德意義和社會意義,人生苦難成為主人公身外世界的漸漸剝離,從而使作品成為一篇超出道德與社會政治意識的哲理性作品,表現出“人對苦難的承受能力,對世界的樂觀態度”,“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而不是為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①的主題。類似這樣對生存世界的寓言化敘事,在新時期還有殘雪、格非的一系列小說。
也有作家將小說演繹成為關于文化的寓言,如阿城的《棋王》、韓少功的《爸爸爸》、王安憶的《小鮑莊》等。《棋王》中洋溢著對道家文化的追捧,對王一生棋場鏖戰后的肖像描寫頗具老子的神韻,與其說這是一個神情專注的棋手,毋寧說這是民族文化精神融鑄而成的一個“棋魂”,遠非某一具體現實人生所能拘囿,而具有與遠古、現在、未來,與宇宙、人生同在的永恒意蘊。《小鮑莊》中透過村民們的一切現象——如小翠逃婚、拾來挨打、撈渣神化、文瘋子的命運等,表層的“仁義”與深層的功利目的形成鮮明的悖論和反諷,表達了作者對儒家文化的“仁義”精神及對這一精神崩潰的理解。《爸爸爸》中一生只會說“爸爸爸”和“×媽媽”兩句話的丙崽,卻是遠古英雄刑天的后裔,其對傳統文化的諷刺意味更是令人警醒。
李銳的《厚土》系列小說,劉恒的《伏羲伏羲》、《狗日的糧食》等小說講述的則是關于人性的寓言。《厚土》系列小說揭示的是偏僻山村農民愚昧、麻木的人性:《假婚》中的光棍漢子,心里咒罵著將女人“過了一水”的隊長,而一腔怒氣卻傾瀉在女人身上以求平衡;《看山》中,隊長要撤換老牛倌的差事,老牛倌縱使有萬般不愿卻并不辯解,但當他無意中看見隊長的婆姨上茅廁的情形時,報復的快感卻油然而生,屈辱的心理得以緩和。劉恒小說講述的是人們為最基本的生存要求苦苦掙扎的人性悲劇:《伏羲伏羲》中講述了在性欲在倫理道德壓抑下產生的人性畸變;《狗日的糧食》則告訴讀者,生存才是人類最為本性的存在。
新時期小說中的寓言化敘事,大抵可以歸屬在上述三種類型之中。作為一種寫作策略和表意景觀,寓言化敘事為新時期小說帶來了價值取向、表現手法上的新變。
在表意方式上,注重象征世界的營造。新時期小說中的寓言化敘事,使象征不再是某個局部、某件事物的象征,而是一個整體的象征系統,共同指向一個哲理命題,整個小說文本成為一個完整的象征世界。小說《活著》中,對苦難的講述不加節制,筆調冷靜平淡,使文本表意空間純粹而透徹;同時設置“我”作為旁聽者,拉開了讀者和故事空間的審美距離,避免陷入一種“固定的,死去的現實”,對象征世界的追求得以實現。《厚土》系列小說中,寫人是為了寓意,寫景是為了寓意,同樣,寫雞們、樹們、牛們,也都帶著很強的象征意味,因此形成一個大的象征文本。品味《小鮑莊》、《爸爸爸》等作品,其象征意蘊也都是整體的而非局部的。
情節構思上,追求奇異性。寓言化敘事與寫實類敘事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其故事講述不是要把讀者的注意力引向生活本身,引向客觀世界的真實存在,而是要導向實在背后的隱喻。情節的奇異性是阻斷讀者關注現實本身的重要手段。例如《活著》中人物接二連三的死亡,便構成了小說情節的奇異性;《小鮑莊》中一開始便是小鮑莊祖先的故事,一連串與九相關的數字羅列,孤老頭子鮑秉義唱的蒼涼的鼓詞,更是增強了小說的傳奇色彩。《厚土》系列中的《合墳》講述的則是為一個死去的女知青因冥婚而合墳的故事,滿含著迷信、荒謬的色彩。即使在故事講述相對曲緩的《狗日的糧食》中,導致曹杏花離開人世的糧本最終失而復得,不能不說是故事情節的巧妙偶合。設置奇異的故事情節,使讀者不會關注現實生活,也不會關注故事自身,迫使其不得不思索喻體背后的寄寓。
時空設置上,模糊性特點較強。為追求一種超越具體事實、具體情境的哲理化啟迪,寓言化敘事有意抹去人物和事件的地域與時代標志,使小說的時空背景相當模糊,從而達到一種高度的普適性和涵蓋性。《爸爸爸》中有意淡化故事的背景,把雞頭寨放在白云繚繞的深山里,模糊了故事講述的時空;而小說中的“打冤”、“逃難”等場景,更是令人難以說明其發生在何時何地。《活著》的故事時間自民國至“文化大革命”后,空間經歷了村莊、戰場、村莊多個場景的轉換,時空變化復雜多樣。《小鮑莊》、《棋王》等作品,可以得知主人公生活的大致時代,卻不能準確定位故事發生的時間和地點;而在殘雪的《山上的小屋》中,故事發生地更是無從可知。這與寫實類小說截然不同,譬如自稱是法國社會“書記官”的巴爾扎克,恩格斯從其《人間喜劇》里,“甚至在經濟細節方面(如革命以后動產和不動產的重新分配)所學到的東西,也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里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②從這一角度看,寓言化敘事中是不可能達到的。
人物塑造上,多以扁平人物形象為主。扁平人物和圓形人物相對,出自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對小說人物的劃分。所謂圓形人物,指人物的性格豐富而多樣,難以簡單地概括;而扁平人物則是指人物的性格單一,讓人可以輕易把握。在寓言化敘事中,寫作重心是建構總體性的隱喻和象征進而傳達某種理念,人物基本上都符號化了。小說《活著》的主人公福貴是作品表達的哲理內涵的承擔者:一生被高度地潔凈化,濃縮了人生的全部磨難。《厚土》系列中共有十幾個短篇小說,但作者并沒有著意塑造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人物在這里,似乎只是一種文化的代碼。這些或以人稱代之或以職務代之的人物,“實際上可以歸納為三類的角色——隊長、女人和老實卻又無能的男人。他們充當了這個特定世界里的形成要素,他們的活動構成了窮鄉僻壤最常見的生活場景”。③《小鮑莊》中人物本身的性格是靜止的,每個人物都代表著作者強加于他身上的理念,也是一種扁平化人物。盡管福斯特認為圓形人物藝術價值高于扁平人物,但是通過西方的現代主義小說已經充分看到,扁平化人物其實是另一類具有高度美學內涵的人物:因為他們揭示真相的銳利和深刻。從這方面來看,寓言化敘事豐富了新時期小說人物形象塑造。
寓言化敘事顛覆了傳統現實主義的小說敘事模式,引領新時期小說思考關于存在、關于本性、關于靈魂等更為本質的問題,洋溢著作家們的睿智與深刻。米蘭·昆德拉在分析小說的存亡時說:“我不想預言小說未來的道路,對此我一無所知;我只是想說:如果小說真的要消失,那不是因為它自己用盡自己的力量,而是因為它處在一個不再是它自己的世界中。”④所謂的“它自己的世界”,就是形而上的世界,或者說,是形而上程度很高的世界。這一論斷顯示了小說追求哲理化內涵的必然性,也預示了寓言化敘事的光明前景。
注 釋:
①余華:《〈活著〉前言》,見《余華作品集》(2),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62~463頁。
③李慶西:《古老大地的沉默——漫說〈厚土〉》,載于《文學評論》,1987(6)。
④米蘭·昆德拉[捷克]著:《小說的藝術》,三聯書店,1992年版,第16頁。
參考文獻:
1.米蘭·昆德拉[捷克],《小說的藝術》,三聯書店,1992年版。
2.愛·摩·福斯特[英],《小說面面觀》,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3.余華:《余華作品集》(1-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
4.阿城:《棋王》,《上海文學》,1984(7)。
5.李銳:《厚土》,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單位:河南教育學院工會)
編校:董方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