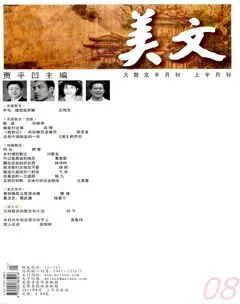互相篡改的散文和小說
何平
生于上個(gè)世紀(jì)60年代末,現(xiàn)執(zhí)教于南京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1990年代后期開始從事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和當(dāng)代文化批評(píng)。做規(guī)矩的學(xué)術(shù)論文,也做不規(guī)矩的文藝評(píng)論和媒體書評(píng)。近年在《當(dāng)代作家評(píng)論》《上海文學(xué)》等發(fā)表文學(xué)批評(píng)40余篇,曾獲《當(dāng)代作家評(píng)論》獎(jiǎng)。
那天旅途中看韓寒的《1988我想和你談?wù)劇罚≌f就像題目的“散文”氣味。忽然想,如果讓“小說”對(duì)“散文”說,“我想和你談?wù)劇保换蛘摺吧⑽摹睂?duì)“小說”說,“我想和你談?wù)劇保麄儠?huì)說什么呢?遙想舊年,“散文”和“小說”并沒有現(xiàn)在這樣以鄰為壑的生分。我們讀先秦諸子,比如說莊子的《庖丁解牛》,你說這是“散文”還是“小說”?至于說《史記》,今天我們說它是“歷史散文”,其實(shí)它又實(shí)實(shí)在在是中國小說的一個(gè)源頭。
散文和小說,什么時(shí)候單立門戶?是兩好,還是兩傷?這都是專家們做的大題目。我只想說的是,對(duì)一個(gè)寫作者而言,寫的是散文,還是小說?這也許不是一個(gè)問題。怎么會(huì)不是問題呢?你肯定會(huì)說,我們現(xiàn)在確確實(shí)實(shí)還株守著散文和小說文類之別。如果沒有散文和小說文類上的差異,那么像《收獲》《人民文學(xué)》《鐘山》這些綜合的文學(xué)刊物也不要?jiǎng)谏裨谛≌f之外給散文單獨(dú)折騰出欄目,像《美文》這樣專門的散文雜志也可以把手伸得更長撈到更多的“美”文了。而另一方面卻是,雖然明明有個(gè)散文和小說的文類邊界在,這樣的文類邊界總是不斷被兩邊的越境者突破和篡改,以至于所謂的邊界常常弄得犬牙交錯(cuò)曖昧不清。尤其是小說家,較之散文家似乎更主動(dòng)更具有侵犯性和攻擊力。汪曾祺就說過:“我的一些小說不大像小說,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說。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講故事。我也不大喜歡太像小說的小說,即故事性很強(qiáng)的小說。故事性太強(qiáng)了,我就覺得不大真實(shí)。我初期的小說,只是相當(dāng)客觀地記錄對(duì)一些人的印象,對(duì)我所未見到的,不了解的,不去以意為之做過多的補(bǔ)充。后來稍稍展開一些,有較多的虛構(gòu),也有一點(diǎn)點(diǎn)情節(jié)。有人說我的小說跟散文很難區(qū)別,是的,我年輕時(shí)曾想打破小說、散文和詩的界限。《復(fù)仇》就是這種意圖的一個(gè)實(shí)踐。”(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說>自序》)不僅是部分的援“散文”入“小說”,幾乎沒有一個(gè)小說家不寫叫“散文”的東西。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說好的小說家都有著不俗的散文功底。其實(shí),這個(gè)問題很有趣,當(dāng)這些“小說”家擱下“小說”去弄“散文”的時(shí)候,他們是怎樣把小說和散文彼此之間的差異“格”得清爽的?
在小說家眼里,散文或許比小說更自由更自己可以率性為之。小說家有意識(shí)地征用“散文”篡改“小說”貪的就是散文的解放感,是一種小說形式,結(jié)構(gòu)意義上刻意的別調(diào)。所謂“云無心以出岫”,心里其實(shí)已經(jīng)預(yù)存了歡喜與厭棄。“小說的散文化”作為現(xiàn)代文學(xué)的潛流和隱脈,當(dāng)然因?yàn)椤靶≌f的不散文化”的滔滔大河在焉。周作人說廢名的小說,“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約總是向東朝宗于海,它流過的地方,凡有什么汊港灣曲,總得瀠洄一番,有什么巖石水草,總要被拂撫弄一下子才再往前去,這都不是它行程的主腦,但除去這些也別無行程了。”(周作人《<莫須有先生傳>序》)因此,如廢名、沈從文、汪曾祺的“小說的散文化”,“散文”是做了他們“反抗”小說形式嚴(yán)整的武器。現(xiàn)代中國文學(xué)端的是外來的和尚好念經(jīng),扯上異邦的大牌,汪曾祺則更是把“小說的散文化”說得理直氣壯:“契訶夫開創(chuàng)了短篇小說的新紀(jì)元。他在世界范圍內(nèi)使‘小說觀’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從重情節(jié)、編故事發(fā)展為寫生活,按照生活的樣子寫生活。從戲劇化的結(jié)構(gòu)發(fā)展為散文化的結(jié)構(gòu)。于是才有了真正的短篇小說,現(xiàn)代的短篇小說。托爾斯泰最初看不慣契訶夫的小說。他說契訶夫是一個(gè)很怪的作家,他好像把文字隨便地丟來丟去,就成了一篇小說了。托爾斯泰的話說得非常好。隨便地把文字丟來丟去,這正是現(xiàn)代小說的特點(diǎn)。……(阿左林)是一個(gè)沉思的、回憶的、靜觀的作家。他特別擅長于描寫安靜,描寫在安靜的回憶中的人物的心理的潛微的變化。他的小說的戲劇化是覺察不出來的戲劇性。他的‘意識(shí)流’是明澈的,覆蓋著清涼的陰影,不是蕪雜的、紛亂的。”(汪曾祺:《談風(fēng)格》)在汪曾祺的眼里,“小說的散文化”有來頭,而且很“現(xiàn)代”。應(yīng)該說,在這種意義上,周作人和汪曾祺確實(shí)讓現(xiàn)代中國文學(xué)別開生面。但如果再往下走呢?當(dāng)汪曾祺借“小說的散文化”把“小說”往“細(xì)小”“柔軟”處做,如他說:“散文化的小說一般不寫重大題材。在散文化小說作者的眼里,題材無所謂大小。他們所關(guān)注的往往是小事,生活的一角落,一片段。即使有重大題材,他們也會(huì)把它大事化小。散文化的小說不大能容納過于嚴(yán)肅的、嚴(yán)峻的思想。這一類小說的作者大都是性情溫和的人。他們不想對(duì)這個(gè)世界做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拷問和卡夫卡式的陰冷的懷疑。許多嚴(yán)酷的現(xiàn)實(shí),經(jīng)過散文化的處理,就會(huì)失去原有的硬度。”(汪曾祺:《小說的散文化》)對(duì)于斯說,是不是有可以商量之處?“小說的散文化” 的篡改和瓦解的是“做”出來的“不散文化”的小說。“散文化”歸根結(jié)底為的是掙脫精神的桎梏和情節(jié)的牢籠,如果卻做了堅(jiān)硬嚴(yán)酷生活的軟化劑,往逼仄處走是自然而然的結(jié)果,也有違“散文化”解放的初衷。
再看當(dāng)下小說,有幾股力量推動(dòng)“散文化”成為一種時(shí)風(fēng)。一是,寫作立場和寫作策略的考慮。“繼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運(yùn)動(dòng),新時(shí)期文學(xué)發(fā)軔與發(fā)展,肯定與發(fā)揚(yáng)個(gè)人價(jià)值之后,難免走入褊狹,到了七十年代生人開始寫作,文學(xué)中的個(gè)體性常被當(dāng)成一種私人化的概念,于是對(duì)自身以外他人的生活漸趨淡漠,從某種方面來說,這樣簡單的自我書寫,也規(guī)避了想象力不足的缺陷。”(王安憶:《東邊日出西邊雨》)一是,時(shí)代的精神癥候。“由于這個(gè)時(shí)代人們的精神普遍處于一種漂流狀態(tài),作為記錄真實(shí)感受和思想的散文也顯得輕盈而零亂。又由于這個(gè)時(shí)代注重個(gè)性,人們?cè)谏⑽膭?chuàng)作中紛紛選擇自己的服飾、道具和配音設(shè)備。”(蘇童:《蘇童散文·自序》)再有是,消閑文學(xué)的盛行。“現(xiàn)代好多作家小說的結(jié)構(gòu)意識(shí)不強(qiáng),那些為有閑階級(jí)、有錢階層服務(wù)的消閑文學(xué)更沒有結(jié)構(gòu)意識(shí)。”(莫言:《莫言王堯?qū)υ掍洝罚┢鋵?shí),不只是“七十年代生人”,比他們或老或少的人,小說都有著“散文化”的時(shí)代風(fēng),比如李洱的《遺忘》、韓少功的《馬橋詞典》《暗示》、胡昉的《購物烏托邦》、安妮寶貝的《二三事》、衛(wèi)慧的《我的禪》、東君的《樹巢》、林白的《婦女閑聊錄》、刁斗的《小說》、何小竹的《女巫詞典》、廖一梅的《悲觀主義的花朵》、韓寒的《1988我想和你談?wù)劇贰ⅠT唐的《萬物生長》以及《最小說》《鯉》《獨(dú)唱團(tuán)》這些主題書中的所謂“小說”明顯出入紀(jì)錄、論文、雜著、札記、隨筆等等散文文類之間。文體實(shí)驗(yàn)和時(shí)尚寫作都不約而同地祭起“散文化”的大旗。文類的混搭瓦解了結(jié)構(gòu)巍峨的小說的文體樣態(tài)。當(dāng)下小說和散文在“輕盈而零亂”之上握手言歡。在此之上,散文予小說的很多時(shí)候不再是一種自由精神的追求,而是一種松懈和倦怠結(jié)構(gòu)的偷懶和漫不經(jīng)心。“小說的散文化”走到這一步已經(jīng)完全失去了它革命和前衛(wèi)的本意,而成為小說不思進(jìn)取不求上進(jìn)的遁詞和掩體。一部小說,尤其是一部長篇小說,如果沒有一種自覺的結(jié)構(gòu)意識(shí),沒有生氣灌注的小說“情節(jié)”,有的只是一點(diǎn)點(diǎn)散文“輕盈而零亂”的“情緒”;散文和小說之間不是旗鼓相當(dāng)彼此對(duì)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占領(lǐng)和篡改,而是小說單方面向散文的投降和臣服。這對(duì)小說固然不是幸事,對(duì)散文也不值得額手稱慶。
其實(shí),小說在許多方面也應(yīng)該是散文的榜樣。就像小說家畢飛宇說周作人的散文《初戀》中的“小說”:
我讀過他的《初戀》。這篇不到一千字的短文被數(shù)不清的散文集、小品集、隨筆集收錄過。只是在“小說集”里頭我還沒有看到過一回。可是,在我的眼光里,《初戀》是一篇出色的短篇,盡管它一千個(gè)字都不到。
《初戀》的故事簡單極了,“我”,害了一場單相思,愛著一個(gè)不知道年紀(jì)、名字,沒有說過一句話,不敢正視的女孩子,而最大的波瀾僅僅是宋姨太的一句詛咒:這個(gè)排行第三的“小東西”也“不是好貨”,“將來總要流落到拱辰橋去做婊子的” 。拱辰橋在哪兒,不知道;婊子是什么,不知道,能肯定的是,數(shù)月之后男仆帶回了一個(gè)壞消息,“楊家三姑娘患霍亂死了” 。
我不知道我為什么如此喜愛這則“短篇”,其實(shí)“短篇”里頭并沒有什么,只有“我”的一點(diǎn)枉然的努力,“我”的一點(diǎn)喜悅,一點(diǎn)不快,不快過后無力回天的一點(diǎn)平靜。如斯罷了。實(shí)在是沒有故事的故事。周作人只是從故事的周圍繞了一圈,給了作品一種氛圍,或籠罩,這籠罩便“罩”在了我們的某個(gè)痛處,而痛便彌漫了。無聲無息。你找不到傷口在哪兒。故事完了。
可是“故事”又復(fù)雜極了。它涉及到了八個(gè)人物,連同一只叫“三花”的貓,“故事”糾集了相當(dāng)復(fù)雜的世故縱深,人物內(nèi)心的底色、背景,“故事”的起因、過程、跌宕、結(jié)局以及情緒的大幅度飄動(dòng)。盡管它只有一千個(gè)字。
它不僅是迂回、氛圍、籠罩,還有“干貨”,有實(shí)實(shí)在在的細(xì)節(jié)和最性格的人物言語,也許還有最“前衛(wèi)”的心理分析,雖然它一千個(gè)字都不到。(畢飛宇:《“硬”說周作人的“小說”》)
散文向小說學(xué)習(xí)什么?按小說家畢飛宇說“‘故事’又復(fù)雜極了”說細(xì)節(jié)說人物言語說心理分析。這些還只是“技術(shù)”層面的。散文也是“文”,是“散”的“文”。因此,從小說,豐富散文技術(shù)的武庫,肯定是有所裨益的。像李娟的《我的阿拉泰》、塞壬的《下落不明的生活》、高暉的《康家村紀(jì)事》這些“散文”骨子里都“化”入了“小說”。散文向小說學(xué)習(xí)還不止于技術(shù)的征用。我們可以看看小說家怎么寫散文的。小說家的散文固然有寫小說剩下的邊邊角角,但許多小說家會(huì)在適當(dāng)?shù)臅r(shí)候去經(jīng)營一塊“整料”而不是邊邊角角“下腳料”的散文。《我與地壇》太有名,我們且不去說。我隨手翻了幾本雜志,看到小說家的散文真的不算少。揀靠近的說,像賈平凹的《一塊土地》、蘇瓷瓷的《一望無際的憂傷》、閻連科的《我與父輩》、王安憶的《東邊日出西邊雨》等就可以拿來做例子。在“非虛構(gòu)”“原生態(tài)”“生活流”等旗幟下,散文養(yǎng)成了對(duì)“獨(dú)異”某個(gè)“角落”某個(gè)“行當(dāng)”某個(gè)“階層”某個(gè)“時(shí)代”生活實(shí)錄的過度依賴癥。而我要說的散文扎根于日常生活,這沒錯(cuò)。還是一個(gè)小說家莫言說過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原則是“我是唯一一個(gè)報(bào)信人”,正因?yàn)椤啊沂俏ㄒ坏膱?bào)信人’,所以,我的聲音,我的話,對(duì)于保存事物的真相,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義。”(莫言:《我是唯一一個(gè)報(bào)信人》)但過于依賴日常生活,黏著于日常生活,不能穿越和超逸于日常生活的寫作是危險(xiǎn)的。文學(xué),當(dāng)然包括散文,需要有重構(gòu)日常生活的能力。它可以像《一塊土地》那樣大開大合的做減法,可以像《一望無際的憂傷》在一個(gè)點(diǎn)上蜿蜒盤旋,可以像《我與父輩》以思想穿越化解事件,可以像《東邊日出西邊雨》閃爍隱約晦暗幽深……所以莫言又說“想怎么說就怎么說,我是唯一的報(bào)信者,我說是黑的就是黑的,我說是白的就是白的。”當(dāng)下散文少見這種小說的大氣魄和大氣象。因此,散文從小說引進(jìn)一些小說專屬的技術(sh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對(duì)于散文這種“近日常生活”的文類,尤其要思考從生活跨入文學(xué)“我”的創(chuàng)造性和想象性重構(gòu)。我們的散文需要地理大發(fā)現(xiàn)、行業(yè)揭秘、階層互窺、時(shí)代翻案等等這些“非虛構(gòu)”“原生態(tài)”的生活之“真實(shí)”,但從生活到文學(xué)不是簡單的“復(fù)制”和“還原”。在“我”的創(chuàng)造性和想象性重構(gòu)方面,小說已經(jīng)走得很遠(yuǎn),散文還可以走得比現(xiàn)在更遠(yuǎn)。直接地說吧,“想象力不足的缺陷”,在當(dāng)下散文和小說中都存在,而散文尤甚。
對(duì)于一個(gè)有進(jìn)取心的寫作者,寫的是散文,還是小說?很多時(shí)候確實(shí)不是一個(gè)問題。再抄畢飛宇幾句。
我不是學(xué)者,絕對(duì)沒有比較魯迅和周作人的意思,那是我的學(xué)養(yǎng)力所不能逮的。而且明明是說小說,怎么又扯到雜文和隨筆上去了,實(shí)在是跑了題目了。其實(shí)我只是想說,在魯迅小說的“底子”上頭,依舊有一種雜文的“作法”,隱含了一種直面與“吶喊”的戰(zhàn)士氣質(zhì),這種氣質(zhì)使先生區(qū)別于一般,使他最終成為現(xiàn)代白話文小說史上最偉大的短篇大師,使他的短篇最終成為現(xiàn)代白話小說中最杰出的范本。然而,我又有些固執(zhí)地以為,周作人的一小部分隨筆里頭,似乎潛伏了“另一種小說”的“小說法”。比如說《初戀》。至少,作為前期的周作人,即使他不能或不愿“吶喊”,“彷徨”的可能似乎還是有的(這句話并不代表鄙人對(duì)《吶喊》與《彷徨》的藝術(shù)評(píng)判——宇注)。倘如此,在魯迅這座短篇大師的高峰一側(cè),周作人或許會(huì)有另一種風(fēng)光的。(畢飛宇:《“硬”說周作人的“小說”》)
如果散文和小說都抱定“我想和你談?wù)劇钡拈_放態(tài)度,把各自的城門敞開,亮出各自的家底,看看各自的貨色,有合用者但管拿來。至于,拿來之后,是丟了河山,還是拓了疆界?看的是寫作者的造化和修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