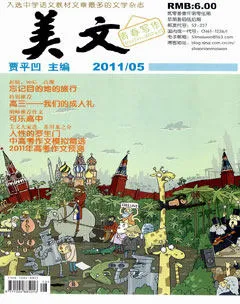北大會商學
“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魯迅先生曾這樣評價北大。的確,曾經有太多思想光澤,讓北大成為中國人的一種精神符號。然而,隨著時間流逝,令人內心激蕩的北大傳統,現在已經籠罩上沉厚的暗影,讓這片天地原本充滿自由與個性的空氣越發稀薄。
這樣的空洞與壓抑,現在就聚焦于“北大將對思想偏激學生進行會商”這件事上。北大學工部副部長查晶表示,主要因為有一些學生經常夸大學校工作的一些細微漏洞,“比如動不動因為食堂飯菜漲兩毛錢就批評學校”。作為一個專業術語,“會商”透露的“調整、統一、控制”意味不言自明。
“北大,已經不是以往的北大。”這是網友發出的沉痛嘆息。其實,這些年有關北大傳統淪陷、精神不斷矮化的事情層出不斷,也一次次激起有關北大精神坍塌的討論。特別是一次次高居大學排行榜之首,讓北大越發傲慢與偏見,離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傳統越來越遠。
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北大會商“思想偏激”的學生也就根本不值得奇怪了。盡管北大此舉引發巨大爭議,多數學生并不認同,但也有北大學生如此表示支持——“有些學生太囂張,經常因為一點小事就詆毀北大,應該將他們送到瘋人院去”。如果北大從上至下真的都走到不能接受批評意見的地步,毫不諱言地說,北大傳統必將徹底坍塌。
關于北大傳統,蔡元培、胡適、蔣夢麟、傅斯年這些北大校長們曾經做過太多表述。“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僅僅以蔡元培這句眾所周知的名言,就把自由主義是北大傳統說清透了。不過,我更喜歡的還是同為北大校長胡適對學生發出的那句激情吁請——— “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吾人若視教育為增進文明之方法,則當自尊重個人始”。這是北大校長蔣夢麟說過的話。他還描述過北大當年的情形,“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短長。背后拖著長辮,心里眷戀帝制的老先生與思想激進的新人物并坐討論,同席笑謔。教室里,座談會上,社教場合里,到處討論著知識、文化、家庭、社會關系和政治制度等等問題”。面對這樣生動的場景,真的不知道現在北大那些要把偏激學生 “送到瘋人院”的干部與學生,會不會一臉羞慚。
北大對“思想偏激”的學生進行會商,說到底,XYBRDN+7++/Z5uPTrUNgWw==就是扼殺個性自由,戕害獨立人格。在北大學工部那位副部長看來,“食堂飯菜漲兩毛錢就批評學校”就可以被界定為“思想偏激”。這一次,我真的被這種官場思維與數字邏輯震驚了,難道說“兩毛”就屬于偏激,到“五毛”就屬于不偏激嗎?嗚呼,我實在無話可說。這里我只想向北大師生,特別是那些表示要把思想偏激的同學“送到瘋人院”的學生推薦兩部老電影———《飛越瘋人院》與《肖申克的救贖》。
寬泛地講,這兩部電影里都是在說逃離掙脫去追求自由人性的故事。不論是被飛越的瘋人院,還是肖申克逃脫的監獄,都曾被賦予太多體制秩序的隱喻。《時代》周刊對《飛越瘋人院》的評價“向體面階級社會的陳規以及支持這些陳規的看不見的統治者發出的憤怒抗議”;而《肖申克的救贖》里被錯判入獄的安迪沒有去像獄友那樣“適應”看似絕望的生活,他相信“有一種鳥是關不住的,因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閃著自由的光輝”。
北大會商學生,我們會商北大。如果現在北大還要會商,不妨就去會商一下自己如何“飛越瘋人院”吧。就像電影《飛越瘋人院》的主題歌唱的那樣:“你是否需要力量抵抗這瘋人院/和我一起飛越這瘋人院……”學者劉軍寧曾說:“沒有自由的時候,北大的使命是爭取自由;有了自由的時候,北大的使命是捍衛自由。”悲哀的是,曾經為別人爭取自由的北大,現在竟然淪落到要別人為它爭取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