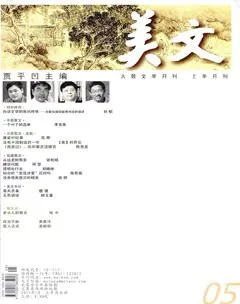老頭兒的散文
何平
生于上個世紀60年代末,現執教于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90年代后期開始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和當代文化批評。做規矩的學術論文,也做不規矩的文藝評論和媒體書評。近年在《當代作家評論》《上海文學》等發表文學批評四十余篇,曾獲《當代作家評論》獎。
新陳代謝,人都是要老的,如花零草凋,合的是節令。歷朝歷代,老而能文者甚多,但這二三十年更是挨挨擠擠,蔚為壯觀。這當然不是什么可歌可泣的正途大道。蓋因為流年多舛,文人遭難,恰在知天命古來稀的年景,逢到一個陽春好天氣。于是,那些早在1949年前就成名了,后來倒了霉運的文學角兒們重新拾起荒疏的把式,老夫聊發少年狂般紛紛著文寫字。以至于一時竟然成就了個“老年寫作”的大景兒。話說文學史上說的“新時期”,朦朧詩也好,傷痕文學也罷,好像都是青壯年們打下的江山。這是小說詩歌在新文學中做大了種下的因果。任何一本現代文學史都把散文當作小擺設小點綴。而事實卻是,就所謂的“新時期”來說,不只是寫《隨想錄》的老頭兒巴金,一幫老頭兒(自然也包括幾個老太太,以下行文中老頭兒包括老太太)的散文是為我們文學迷途復返做下大貢獻的。因此,冀望文學史的專家學者對老頭兒們在這二三十年的文學寫作史也搶救性的“還原”一下。
依稀記得沈昌文先生幾年前的小書《書商的舊夢》好像有些事關“老年”的議論。重新找來翻,發現這個自稱“老漢”(《舊時月色》)的“老頭兒”果然說過許多有意思的話。比如《于無意中得之》中說,“我只是出版界的退休老職工,既無學識,更非什么‘大佬’。”比如《七十二·五十五·三》中說:“於梨華與我同齡,都已七十二歲,可謂垂垂老矣。她的散文集,有老年作家的特點:嫻于懷舊。”“人都老了。我看著於梨華那仍然歡樂、暢然的笑臉,不知怎的,又想起她散文中對自己母親晚年‘眼里沒有認知,臉上沒有喜悅’的描述。下次見面,我們這些老人會不會這樣呢?但無論如何,我更相信於梨華小弟弟的一席話:‘母親沒有老人癡呆癥,只是她已回到三歲孩童時期,世事不知,何嘗不是幸福’。”“從七十二歲退回五十五年,可以敘說當年的往事,是一種幸福。如果能再退到‘三歲孩童時期’,那一定更幸福了”。比如《老年時期》說關于張中行先生的一個傳說,“張中行老先生近來已經不能行動,有記者采訪他,老人神智清楚,到哪無法以言詞應對,只在紙上寫了這么一句話:想不到老年時期這么過去了(大意)”。“老年人集會,容易聽到的話是:老了,不中用了。現在張老這話指出,人還有一個‘老年時期’,還能做事”。恰乎有個“老年時期”,且“嫻于懷舊”,沈“老頭兒”的這些議論為老頭兒的散文畫出了大致的一個道。
自定下寫這個題目,這一個月扎圖書館專找老頭兒老太太的散文往家搬。只是時間催得緊,也只才半新讀半溫習了汪曾祺、張中行、黃永玉、吳冠中、王世襄、楊絳、劉紹銘、木心、沈昌文、臺靜農、吳冠中、孫犁、黃裳、季羨林、聶紺弩等可數的幾家。可就看這幾家,就看他們的“懷舊”,已經是可觀得很。這二三十年寫散文的老頭兒大都是在歷史的大風浪中顛過簸過。他們所經歷的人事即使織不起歷史的經絡,也當是歷史的血肉。劉紹銘在其《黃永玉書畫人生》中說:
Kathleen Norris為二○○一年《美國最佳散文》(The Best American Essays,二○○一)作序,說到收入這集子的作家,有一特色,那就是:心有所感,發覺非筆之于紙公諸于世不可(this story must be told)。
你說對了,此說卑之無甚高論。可圈可點是下面這句話:I am the person who must tell it的承擔。要說此故事,普天之下,除了區區,還有誰可勝任此重任?
像郁達夫夜訪沈從文這類故事,也只有黃永玉最適合講。他記紺弩、林風眠、李可染和張樂平等人的文字,都顯露了I am the person who must tell it的承擔。
黃永玉的師友篇,就是這種‘舍我其誰’的信念和‘當仁不讓’的精神驅使出來的成果。文字粗獷,散發著U6eNCvZBDREH9DFVL5fLq8yZorW50OHc4YtuxgvQ9cM=一股‘蒸不爛、煮不熟、錘不扁、炒不爆’的頑強生命力。這正是黃永玉文字別具一格的地方。
不只是黃永玉,“I am the person who must tell it的承擔”幾乎所有這二三十年寫散文老頭兒的“格”。或者說是“風骨”。這種“承擔”的“立此存照”的見證意義,所涉及有的還不只是個人之“私”,它關涉到我們對一些“大人物”“大事件”的判斷。比如楊絳在《我們仨》中關于錢鍾書在學部七樓的陋室翻譯毛澤東詩詞的一段:
袁水拍同志幾次想改善工作環境,可是我和鍾書很頑固。他先說,屋子太小了,得換個房子。我和鍾書異口同聲:一個說“這里很舒服”;一個說“這里很方便”。我們說明借書如何方便,如何有人照顧等等,反正就是表示堅定不搬。袁辭去后,我和鍾書咧著嘴做鬼臉說:“我們要江青給房子!”然后傳來江青的話:“鍾書同志可以住到釣魚臺去,楊絳同志也可以去住著,照顧鍾書同志。”我不客氣說:“我不會照顧人,我還要阿姨照顧呢。”過一天,江青又傳話:“楊絳同志可以帶著阿姨去住釣魚臺。”我們兩個沒有心理準備,兩人都呆著臉,一言不發。我不知道袁水拍是怎么回話的。
比如吳冠中的《我負丹青!丹青負我!》寫到的江豐和中國當代美術的是是非非:
他依舊是美術界掌握方向性的領導,觀點較反右前開明,但對抽象派則深惡痛絕,毫無商討余地,大家經常說“探索探索”,他很反感?似乎探索中隱藏著對現實主義的殺機。我發表過《關于抽象美》的文章,江豐對此大為不滿,在多次講演中批評了我,并罵馬蒂斯和畢加索是沒有什么可學習的。我們顯然還是不投機,見面時彼此很冷淡。在一次全國美協的理事會上,江豐講演攻擊抽象派,他顯得激動,真正非常激動,突然暈倒,大家七手八腳找硝酸甘油,送醫院急救,幸而救醒了。但此后不太久的常務理事會上(可能是在華僑飯店),江豐講話又觸及抽象派,他不能自控地又暴怒,立即又昏倒,遺憾這回沒有救回來,他是為保衛現實主義、搏擊抽象派而犧牲的,他全心全意為信念,并無私念。(吳冠中:《我負丹青!丹青負我!》)
類似老頭兒的“懷舊”很多,比如黃永玉《這些憂郁的碎屑》說沈從文;比如臺靜農《酒旗風暖少年狂》談陳獨秀;比如楊絳《回憶我的姑母》述楊蔭榆;比如梅志《“愛”的悲劇》談蕭紅……這種“懷舊”的“舊”,和歷史學家的“舊”不同,他們有自己的一己之“私”和“思”澆灌其中。也就是有自己的心眼,而不拘泥定見和陳規。比如楊絳眼里的胡適:
他又是我爸爸和我家親友的熟人。他們曾談到一位倒霉的女士經常受丈夫虐待。那丈夫也稱得蘇州一位名人,愛拈花惹草。胡適聽到這位女士的遭遇,深抱不平,氣憤說:“離婚!趁豐采,再找個好的。”我爸爸認為這話太孩子氣。那女士我見過多次,她壓根兒沒什么“豐采”可言,而且她已經是個發福的中年婦人了。
……
我記得胡適一手拿著帽子,走近門口又折回來,走到擺著幾盤點心的桌子旁,帶幾分頑皮,用手指把一盤芝麻燒餅戳了一下,用地道的上海話說:“‘蟹殼黃’也拿出來了。”說完,笑嘻嘻地一溜煙跑往門口,……(楊絳:《懷念陳衡哲》)
從這種意義上,我們有理由相信,即使不從文學審美的角度,老頭兒的“懷舊”也應該是我們民族精神財富的一部分。甚至可以極端地說,對于他們所經歷的歷史,那些流逝的時光,如果他們保持緘默,我們將兩手空空。但他們都會更老了,他們將離我們而去。我的研究生吳晨一直在做這方面的資料。我看了她整理出來涉及老頭兒生卒的部分就唏噓不已。從上個世紀80年代,幾乎沒有一年沒有老頭離世的哀痛為我們所遭逢。
我知道,以文學論衡,我們談論老頭兒的散文不只能定位在掌故、稗史、野聞上。文學考量上的老頭兒散文,往往“歸于平淡”,不似少壯之年的“新一點,怪一點,朦朧一點,荒誕一點,狂妄一點”;(汪曾祺:《七十抒懷》)“可以在斜陽照射的籬下說說”;(張中行:《趙麗雅》)這種“平淡”和“說說”不是“寡淡”和“絮絮叨叨”,可以看看汪曾祺先生寫他的小學教師:
……這張會議桌平常不開會,有一個名叫夏普天的教員在桌上畫炭畫像。這夏普天(不知道為什么,學生背后都不稱他為“夏先生”,徑稱之為“夏普天”,有輕視之意)在教員中有其特別處。一是他穿西服(小學教員穿西服者甚少);二是他在教小學之外還有一個副業:畫像。用一個刻有方格的有四只腳的放大鏡,放在一張照片上,在大張的畫紙上畫了經緯方格、看著放大鏡,勾出鉛筆細線條,然后用剪禿了的羊毫筆,蘸碳粉,涂出深淺濃淡。說是“涂”不大準確,應該說是“蹭”。我在小學時就知道這不叫藝術,但是有人家請他畫,給錢。夏普天的畫像真正是謀生之術。夏家原是大族,后來敗落了。夏普天畫像,實非不得已。過了好多年,我才知道夏普天是我們縣的最早的共產黨員之一!夏普天給我的印象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汪曾祺:《我的小學》)
筆下驚雷,而能張弛有致。也許只有老頭兒才有這種拿捏的心手。黃永玉寫看鋼琴家霍洛維茲演奏的紀錄片說“這老頭不管奏出什么聲音,神色都從容安詳”。(黃永玉:《這些憂郁的碎屑》)說的就是這等境界。老頭兒為文有瘦枯之弊,從用情觀之,“從容安詳”,而能做到“情深若是,發人哀思”的腴潤((黃永玉:《大家張伯駒先生印象》)又是另一層境界。這里可以舉黃永玉寫晚年的張伯駒先生:
四害伏法,伯駒先生及碌碌眾生得活。月入八十元與潘素夫人相依為命。某日余偕妻兒赴西郊莫斯科餐廳作牙祭,忽見伯駒先生蹣跚而來,孤寂素寞,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紅菜湯一盆,面包四片,果醬小碟,黃油兩小塊。先生緩慢從容品味。紅菜湯畢,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手巾一方,將抹上果醬及黃油之四片面包細心裹就,提小包自人叢中緩緩隱去。余目送此莊嚴背影,不忍他移。……余曾對小兒女云:張先生一生喜愛人間美好事物,嘗盡世上甜酸苦辣,富不驕,貧能安,臨危不懼,見辱不驚,居然喝此蹩腳紅菜湯,真大忍人也。……夫人國畫家音樂家潘素系余同行。老人手中之面包,即為帶回者。(黃永玉:《大家張伯駒先生印象》)
所以,劉紹銘品評黃永玉的散文:“以文字‘言志’的作品,有不少是記懷舊交游的。在他筆下出現過的近代中國畫壇祭酒級的人物,計有齊白石、林風眠、李可染等,還有漫畫家張樂平。這些記述文字,有時淡淡幾筆,卻載動許多愁。”“載動許多愁”固然是老頭兒散文的一端;另一端卻是“謔”與“幽默”。黃永玉畫作一大特色是“謔人和自謔”。而這恰恰也是許多老頭兒散文的特色。劉紹銘對黃永玉的理解是老頭兒對老頭兒的心解。汪曾祺以為這種“謔”,或者說幽默是有來頭的:“人生多苦難。中國人、中國的知識分子生經憂患,接連不斷的運動,真是把人‘整慘了’。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卻能把一切都忍受下來,在說起挨整的經過時并不是捶胸頓足,涕泗橫流,倒常用一種調侃詼諧的態度對待之,說得挺‘逗’,好像這是什么有趣的事。這種幽默出自于痛苦。唯痛苦乃能產生真幽默。唯有幽默,才能對萬事平心靜氣。平心靜氣,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缺點,也是優點。”(汪曾祺:《平心靜氣》)沒有“許多愁”的底子,“謔”與“幽默”容易流于輕浮、淺薄;而只有“許多愁”,不“謔”與“幽默”出之,則文字漸次滯澀、呆板。我們可以不舉黃永玉、汪曾祺這些以“謔”聞世的老頭兒的例子。看看王世襄這個老頭兒怎么寫的。京劇演員朱家縉不料由于一技之長,竟招致誤導訛傳,認為他有飛檐走壁之能。“三反”中引來一場周密計劃,興師動眾,如臨大敵,步步為營,捉拿朱家縉的可笑鬧劇。二三十人編了隊,開了三輛吉普車來。特工人員從炒豆胡同進入,每進一道門就留兩個人把守。越過兩層院子,進入中院,正房和兩廂房頂上早有人持槍守候。王世襄寫到:
季黃說:“那天傍晚,我剛洗完澡,坐在床上,尚未穿好衣服,兩腳也未伸入鞋中。忽聽見院中有人聲,破門沖進兩人,立即把我銬上手銬,并叫我跟他們走。我因兩手不能下伸,提不了鞋,忽然想起林沖在某出戲中(戲名可惜我忘記了)的兩個動作,可以采用。我立在床前,像踢毽子似的,先抬右腿,以鞋幫手,伸手把鞋提上。再抬左腿,重復上述動作,把左腳的鞋提上。”做兩個動作時,口中發出“答、答”兩聲,是用舌抵上膛繃出來的,代替文場的家伙點兒,缺了似乎就不夠味兒。兩個動作完后,季黃問大家:“你看帥不帥?邊式不邊式?”……(王世襄:《沒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
再在《錦灰堆》里挑一段:
不意垂老之年,來到長江以南的瀕湖地區——咸寧。我被安排住在圍湖造田的工棚里,放了兩年牛。勞動之余,躺在堤坡上小憩,聽到大自然中的白靈,妙音來自天際。極目層云,只見遙星一點,飄忽閃爍,運行無礙,鳴聲卻清晰而不間隙,總是一句重復上百十次,然后換一句又重復上百十次。如此半晌時刻,驀地一抿翅,像流星一般下墜千百仞,直落草叢中。這時我也好像從九天韶音中醒來,回到了人間,發現自己還是躺在草坡上,不禁嗒然若失。這片刻可以說是當時的享受,把什么抓“五·一六”等大字報上的烏七八糟語言忘個一干二凈,真是快哉快哉!(王世襄:《百靈》)
“謔”與“幽默”不是外加麻油樣的做出來的。能“謔”者,往往都有熱愛生活的好性情。對于生活,年輕人很難做到“性情”,老頭兒卻能。“‘瓶花妥帖爐香穩,覓我童心四十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人到上了歲數了,最可貴的是能保持新鮮活潑的、碧綠的童心”。(汪曾祺:《平心靜氣》)阿城說:“當代的文學家汪曾祺常常將俗物寫得很精彩,比如咸菜、蘿卜、馬鈴薯。古家具專家王世襄亦是將鷹,狗,鴿子,蛐蛐兒寫得好。肯寫這些,靠的是好性情。”(阿城:《閑話閑說——中國世俗與中國小說》)
說到最后,稍微說幾句老頭兒散文的文體和文風。也算借不算遠的古來說說今。張中行先生說過:“我老了,同不少老年人一樣,不免有青壯年沒有甚至不理解的感觸。有感觸是‘情動于中’,照《毛詩序》的想法,隨之而來的還有‘而形于言’。言,偏于零碎的用口,偏于成套的用筆。古人云:‘言而無文,行之不遠’,化大道理為現前事,是寫下來,何時有興趣算舊賬,就可以一五一十重復一遍。”(張中行:《失落》)類似的說法,汪曾祺先生也說過:“人老了,對近事善忘,……但對多少年前的舊事卻記得真切。這是老人‘十悖’之一。我把這些往事記下來,就是一篇散文。”(汪曾祺:《祈難老》)黃宗羲《論文管見》稱:“古今來不必為文人始有至文,凡九流百家以其所明者,沛然隨地涌出,便是至文。”原來文章可以如許多寫手樣做出來,也可以“沛然隨地涌出”。當然,人猶未老,大可不必擺出一副老三老四的“老頭兒腔”唬人。“沛然隨地涌出”,你隨你的“地”,可矣。裝老裝嫩,不人不鬼,生出來只能是個四不像的怪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