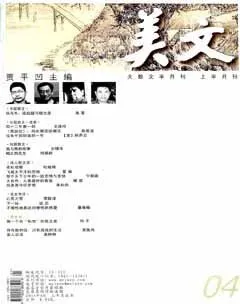風蕭蕭兮軒亭恨
朱和風
浙江紹興人,作家,發表小說、散文多種。現供職《寧波日報》。
七月盛夏的一個上午,我和女兒一起來到紹興古軒亭口的秋瑾紀念碑前,此時的街衢上人們行色匆匆,而漢白玉雕刻的秋瑾目光凝重。盡管我的身邊是滾滾的車輪和蒸騰的氣浪,但我卻感到寒冷如晨露沐過一樣。遙想百多年前的這天拂曉,黑暗籠罩的古軒亭口看不到晨曦,黎明前的幾塊烏云在空中低低地徘徊,偶爾落下幾顆雨滴,沉重地滴落在青石板鋪就的路上,聲音是單調的,也是無奈的。誰也沒有想到,已走到歷史盡頭的清政府,卻在古軒亭口磨刀霍霍,一起血腥的屠殺已經拉開序幕,一顆美麗的頭顱,瞬間駁離火熱的軀體。而古軒亭口周邊的河埠頭、青石板路上,神情麻木的會稽、山陰兩縣百姓,踏著細碎的腳步,前來觀看:秋瑾就義。
我小時候住在紹興的偏門街,這條蜿蜒的長街離魯迅小說《藥》中描寫華老栓“遠遠里看見一條丁字街”的古軒亭口并不太遠,與我家毗鄰還住著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她經常繪聲繪色地對我講起傷痕累累的秋瑾在軒亭口被砍頭的一幕,她是親眼目睹的。以至于小小的我去毗鄰軒亭口的紹興東湖照相館拍照時,總是心神不寧,臉上擠不出一絲的笑容,讓攝影師急得團團轉。后來,我讀書的學校是紹興一所著名的中學,叫稽山中學,離學校一箭之遙有條街叫和暢堂,并不叫和暢堂街。因為和這條街上有秋瑾的故居叫和暢堂,這條街就一直叫和暢堂。現在想來,這是紹興的黎民百姓對鑒湖女俠的深情緬懷和尊敬,把她家面前的那條街,以她的故居命名。那時,閑來無事的我,常去和暢堂玩,這里偏僻、安靜。街上的“和暢堂” 青磚白墻烏瓦,和暢堂的門楣上“秋瑾故居”的匾額出自何香凝的手書,筆力遒勁,情意內蘊。
我小時聽鄰居老人講秋瑾就義,到讀中學時與秋瑾故居為鄰,在屠刀下不屈的秋瑾形象和穿著日本式和服的秋瑾形象,從此雙雙進入了我的世界。
性格決定命運,我至今認為秋瑾的死既是歷史的悲劇也有她自身的因素。過去,常有人說秋瑾的婚姻是不幸的,她是父母包辦婚姻的犧牲品,丈夫王延鈞這個湖南的暴發戶之子,不學無術。近來讀秋瑾好友徐自華的《秋瑾軼事》后,我覺得憑著秋瑾的性格,她只能成為一個職業的革命家,而絕對不能成為一個好妻子和一個好母親。她和徐自華留學日本的某次游園小憩品茗時,突見一中國留學生挾一雛妓乘車,欲要當面諫之。有人勸她,她則說:“余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秋瑾口無遮攔之性格可見一斑。正如徐自華記載的那樣“女士擅辯才,口角不肯讓人。”還有,秋瑾又是一個飲酒甚爽甚好的人,徐自華稱她“女士雅量,雖一二十巨觥不醉,酒后縱談更豪”。我不知道這一二十巨觥是多少斤酒,想必不少于一二十杯酒吧,而能喝下這么多酒的一個女子,你能想象出她的剛烈如火一般的性格。
秋瑾確實是個性格非常鮮明的革命家,在日本留學的某日,正是明朝亡國之日,她獨自飲泣。同學們問她思家乎,回答無家可思;問她思親乎,回答母雖老嫂甚賢。她的憂國之心躍然而出。在徐自華所著的《秋瑾軼事》中,還有許多有關秋瑾的豪爽潑辣的生動細節。
從上面的一些記載和近來翻閱秋瑾的詩詞,我覺得她早年寫過如“一灣流水無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紅”風花雪月范疇的詩,可以窺到那時她的婚姻還是和諧的。她與王廷鈞的婚姻雖不像宋朝才女李清照與趙明誠那樣琴瑟和鳴,但她與王廷鈞還是相親如賓的。歷史記載,王廷鈞靠金錢捐了個京城小官,但如果他們關系惡化,根據傳言王廷鈞是個“紈子”的說法,他完全可以不帶她進京,甚至還可以納妾換妻。然而,王廷鈞沒有這樣做。應該說,秋瑾的丈夫王廷鈞對秋瑾是極盡包容和寬容的。而且,王廷鈞還給秋瑾走上職業革命家的道路創造了難得的機會,送她東渡日本留學。
北京是當時清政府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最易感受到時代潮流這一跳動的脈搏,王廷鈞帶著秋瑾去北京赴任,對于秋瑾來說是非常幸運的,使她能在消息靈通的京城吸收全新的信息。更加幸運的是,她的家又恰好與一位頗負文名且思想進步的婦女吳芝瑛為鄰。吳芝瑛是清末著名的“桐城派”學者吳汝綸的侄女,丈夫廉泉也是個思想開明的人物。秋瑾與吳芝瑛情投意合,她們都對詩詞有著濃厚的愛好和很深的造詣,思想又都傾向革新,向往著當時傳入中國的種種新生事物,于是她們結拜為姐妹。通過吳芝瑛,秋瑾經常有機會看到當時出版的一些新書、新報,接觸一些新思想,她的眼界從此不斷擴大。當有人將譚嗣同在北京菜市口就義時從容不迫地喊出“各國的變法成功,都有獻出生命的;中國變法的失敗,就缺少敢于犧牲的人,要有,就從我譚嗣同開始”的聲音描述給她時,秋瑾找來譚嗣同寫的變法文章,邊讀邊抹眼淚。潛藏在她內心深處的那一份剛烈的俠義性情澎湃了起來。
明末的紹興先賢王思任在斥責弘光帝朱由崧朝時的奸佞之臣馬士英時說“吾越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污之區也”。魯迅先生也非常欣賞此話,多次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而秋瑾的血液中,正流淌著這道堅韌的古越文化。我讀過一本辛亥革命時期的詩歌,有孫中山、黃興和趙聲的,也有章太炎和鄒容的,也有秋瑾、徐錫麟、揚振鴻、陳更新和龍鳴劍等人的詩歌,有不少詩歌現在讀來,口語化、公式化的味道很重,很少能達到思想性與藝術性完美結合的佳作。但是,這些詩歌所折射出來的氣勢是強烈的、革命的和不怕流血的。秋瑾更甚,她的“拼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很明顯地歌頌了流血的暴力斗爭。
應該來說,秋瑾本來是不會死的。可是,作為革命黨人的秋瑾的對立面是紹興知府貴福。貴福與被徐錫麟刺殺身亡的恩銘均為滿人,還有沾親帶故的關系。而置恩銘與死亡的人是徐錫麟,他的同黨同鄉又是秋瑾,貴福就必欲置秋瑾于死地,也算是為自己的滿族同鄉親戚雪了仇。所以,當山陰縣令李鐘岳說:“供、證兩無,安能殺人?”貴福就向浙江巡撫張曾鰎謊報秋瑾已承認密謀革命,騙得張曾鰎處決秋瑾的手諭。我還有一種理解,秋瑾的身上流淌著古代巾幗的豪情與血性,當她已知紹興大通學堂的起事泄密,安徽方的徐錫麟已死,革命已經走向低潮時,她既不聽人勸說去上海的租界避難,也不跟著翻墻逃走的王金發一起去嵊州鄉下,而是充滿豪情地表示還要等各地的光復軍來聯絡,自己怎可一走了之。她這種以卵擊石的精神固然讓人敬佩,但紹興的革命種子卻被清廷走卒鏟除,讓人唏噓!秋瑾這種身先士卒的精神也讓李鐘岳敬重,在抓捕秋瑾過程中,他故意拖延時間,留給秋瑾出逃的機會。但是,崇尚武力和犧牲的秋瑾并不懼死,殺身成仁的個人英雄主義使她把自己送上了烈士的刑臺。
魯迅的《藥》中的癆病患者,饅頭竟蘸著以秋瑾為原型的烈士夏瑜的鮮血,治病。這是死前的秋瑾不曾想到過的。我想,秋瑾不懼死亡,她想以自己的死喚醒沉睡的國人。可是,那部分已經麻木的“看客”,他們并不一定在“看”,在這個看的過程中,他們成了參與的“共犯”,這是秋瑾所不想看到的國民劣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