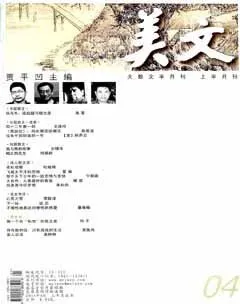做一個(gè)有“私想”的散文家
何平
生于上個(gè)世紀(jì)60年代末,現(xiàn)執(zhí)教于南京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1990年代后期開始從事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和當(dāng)代文化批評(píng)。做規(guī)矩的學(xué)術(shù)論文,也做不規(guī)矩的文藝評(píng)論和媒體書評(píng)。近年在《當(dāng)代作家評(píng)論》《上海文學(xué)》等發(fā)表文學(xué)批評(píng)四十余篇,曾獲《當(dāng)代作家評(píng)論》獎(jiǎng)。
題目本來是“源于生活,能夠高于生活?怎樣高于生活?”文章寫好了,題目卻換了。先把老題目的題意破解破解。“源于生活,能夠高于生活?怎樣高于生活?”其實(shí)是從“文學(xué)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那句著名的文學(xué)語錄翻出來的。這句文學(xué)語錄我們耳熟能詳。生活之于散文的源頭關(guān)系似乎也從來不證自明。但我們是不是真的把這句話都參透了呢?而且這句話本身存在不存在可以挑剔、可以質(zhì)疑的地方呢?說文學(xué)源于生活,我們姑且假定這個(gè)前提成立,那么當(dāng)我們開始捉筆為文的時(shí)候,我們想過,對(duì)于文學(xué)之源的生活,我們究竟知道多少?我們能夠說出多少?我們能夠沒有顧忌和禁忌說出多少?這些是不是問題呢?如果把這些損耗計(jì)算上,我們還能果斷地說,源于生活的文學(xué)就高于生活嗎?退一步講,即使沒有損耗,如當(dāng)今許多散文家所說寫的“原生態(tài)”“原生活”,文學(xué)又在什么方面“高于”生活了?當(dāng)然,我理解這句文學(xué)語錄的深得人心處,是相信文學(xué)對(duì)于生活有巨大的表現(xiàn)力、概括力、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因?yàn)樽骷姨焐蛻?yīng)該是想象和思想的動(dòng)物。因此,如果要得這句文學(xué)語錄成立,必須預(yù)先假定我們的作家心智是成熟的,是能夠識(shí)得生活的假象和真相的;假定我們的作家不躲不藏有反思批判勇氣的;假定他們的想象是飛翔著的,思想是獨(dú)異的如此等等。可索諸四海宇內(nèi),我們有多少作家能堪此任?
我盤算著,在處理文學(xué)和生活的關(guān)系之上,寫“真”生活而不是“偽”生活應(yīng)該是窺文學(xué)之門徑,而以獨(dú)異之思想想象性地穿越、反思生活則是達(dá)文學(xué)之高境界。且以前者觀諸當(dāng)下散文。不痛不癢不淡不咸可寫可不寫的生活差不多是我們散文的常態(tài)。當(dāng)然這些起居注交往志十八扯的“山海經(jīng)”可能是“真”生活,但這樣的“真”生活往往抓不住時(shí)代的“麻經(jīng)”,點(diǎn)不到時(shí)代的“穴道”。比如當(dāng)下作家寫了這么多的親人和自己,如果要他們像魯敏《以父之名》這樣直面一個(gè)給她少女時(shí)代帶來很多恥辱和傷害的父親,像塞壬的《匿名者》這樣不藏掖自己混亂不堪下落不明的生活,能不能坦蕩得起來?比如當(dāng)下散文寫了那么多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小人物”,可有多少像桑麻的《滏陽河邊的死亡》《一九九二年的暴力》那樣正視我們習(xí)焉不察的冷酷和暴力?20世紀(jì)80年代中后期,1960年代出生的作家曾經(jīng)和他的前一代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一起發(fā)動(dòng)了先鋒的嘩變。1990年代他們中間所謂的“晚生代”又和后一代的1970年代出生的作家用或妖嬈或粗糲的身體作本錢楔入時(shí)代,成為時(shí)代欲望化場(chǎng)景中的一部分。現(xiàn)在,這些叛逆者正在變得世故、圓滑,中產(chǎn)階級(jí)明哲保身的庸俗惡習(xí)正腐蝕著他們的心靈。他們避世、逃世,書寫著新時(shí)代的貴族文學(xué)和山林文學(xué)。他們對(duì)現(xiàn)實(shí)失語,甚至連身體也睡著了。因此,當(dāng)此時(shí),在生活面前,我們需要不躲閃,不世故,簡(jiǎn)潔而堅(jiān)硬地對(duì)現(xiàn)實(shí)亮出了鋒利的解剖刀,也對(duì)自己亮出了鋒利的解剖刀。唯其如此,也才能指望散文“源于生活”。
當(dāng)下散文在處理文學(xué)和生活關(guān)系之上的問題還不止是裝腔作勢(shì)躲躲閃閃。更大的更普遍的問題是“貼標(biāo)簽”。散文家罕見“異見領(lǐng)袖”和“私想家”,有的是大而化之的“標(biāo)簽黨”。比如寫到城與鄉(xiāng),言必“城”為人間地獄,“鄉(xiāng)”為田園牧歌;比如寫歷史,逢正必反,逢邪必扶,所謂歷史就是乾坤大挪移,文化散文玩成文化把戲;比如寫童年,必今不如昔,哪怕是前改革時(shí)代的中國(guó)鄉(xiāng)村,物質(zhì)匱乏得鳥去,也精神充盈得勃勃。可是我倒想,當(dāng)下中國(guó)鄉(xiāng)村固然一派頹敗到“廢”,但像林白的“神靈猶存的村莊”是不是也是一種“真”生活?林白說:
鄉(xiāng)下新蓋的房子還沒粉刷,我們就趕來住上了。
門口槐樹掛著一幅毛主席像,樹干因?yàn)榭偹┡#瑯淦げ涞袅艘粔K,是白的,主席像和這溜白樹干上下連成一體,早晚猛一看,十足像一個(gè)人站在樹下,讓你心里一凜。
聽鄉(xiāng)鄰說,在建屋工地上掛主席像可以辟邪。
……
太陽真的下山了,花生的葉子有些發(fā)潮,夜嵐在山野間鋪了薄薄的一層,各戶的炊煙升起來,是濃的,也是有草的氣味。
……
緊鄰有小學(xué)校,卻荒廢了,大鐵柵欄鎖著。站在門口看到荒草趕著操場(chǎng),眼看就快要長(zhǎng)滿所有的空地。學(xué)校蓋得很漂亮,是黃色琉璃瓦屋頂,像亭子似的六角形。但是沒有一個(gè)人,是一所空學(xué)校。孩子越來越少了,許多孩子跟父母在打工的城市上小學(xué),到讀初中的年齡才獨(dú)自回家鄉(xiāng)上中學(xué)。
路邊芭芒最高,鋒利的、瘋狂的,炸著長(zhǎng),我們走小路時(shí)要倒著走,以免芒葉劃傷。
人說現(xiàn)在的植被比六十年前要好,因?yàn)椴粺癫萘耍饕獰簹夂吞柲埽忠驗(yàn)榕I俣嗔耍蝗唬T缇涂泄饬耍睦镞€有這么高的草。
可見大自然也有生生不息的力量。我們對(duì)世界,其實(shí)所知甚少。
……
我問她:鬼在什么時(shí)候出來呢?
木珍肯定說,鬼是中午十二點(diǎn)出來,白天就到山凹里,晚上到家里來,天快亮?xí)r雞一叫鬼就跑了。麥子黃了鬼也要出來,叫“麥黃鬼”,鬼它也知道要收麥子了,它從墻上伸出手來要吃的。(林白:《新屋手記:神靈猶存的村莊》)
今天的散文寫鄉(xiāng)村都樂得簇?fù)淼筋j敗的“鄉(xiāng)村”,有多少人像林白這樣關(guān)切神靈猶存的村莊。村莊神靈猶在,但我們都忙著去趕其他的時(shí)髦場(chǎng)子去也。再比如奢批都市也是我們今天很大很正義的聲音。韓少功的《山南水北》也經(jīng)常把城市押上審判臺(tái):“所謂城市,無非是逃避上帝的地方,是沒有上帝召見和盤問的地方。”(《月夜》)“都市里的笑容已經(jīng)平均化了,具有某種近似性和趨同性。”(《笑臉》)“很多蟲聲和草聲也都從寂靜中升浮起來。一雙從城市喧囂中抽出來的耳朵,是一雙蘇醒的耳朵,再生的耳朵,失而復(fù)得的耳朵,突然發(fā)現(xiàn)了耳穴里的巨大空洞與遼闊,還有各種天籟之聲的纖細(xì)、脆弱、精致以及豐富”。(《耳醒之地》)“融入山水的生活,經(jīng)常流汗勞動(dòng)的生活,難道不是一種最自由和最清潔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難道不是一種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撲進(jìn)畫框》)這些議論我們今天的大小文人幾乎都能熟練地牢騷幾句,但有幾人像韓少功這樣身體力行地先讓自己成為了一個(gè)“勞動(dòng)的”“鄉(xiāng)下人”然后再議論風(fēng)生。因此,我們不能忘記韓少功非議城市的背景是:“坦白地說:我看不起不勞動(dòng)的人,那些在工地上剛干上三分鐘就鼻斜嘴歪屎尿橫流的小白臉。”“我對(duì)白領(lǐng)和金領(lǐng)不存偏見,對(duì)天才的大腦更是滿心崇拜,但一個(gè)脫離了體力勞動(dòng)的人,會(huì)不會(huì)有一種被連根拔起沒著沒落的心慌?會(huì)不會(huì)在物產(chǎn)供養(yǎng)鏈條的最末端一不小心就枯萎?會(huì)不會(huì)成為生命實(shí)踐的局外人和游離者?”“我要?jiǎng)趧?dòng)在從地圖上看不見的這一個(gè)山谷里,要直接生產(chǎn)土豆、玉米、向日葵、冬瓜、南瓜、蘿卜、白菜……我們要恢復(fù)手足的強(qiáng)健和靈巧,恢復(fù)手心中的繭皮和面頰上的鹽粉,恢復(fù)自己的大口喘氣渾身酸痛以及在陽光下目光迷離的能力”, “勞動(dòng)就成了一個(gè)火熱的詞,重新放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