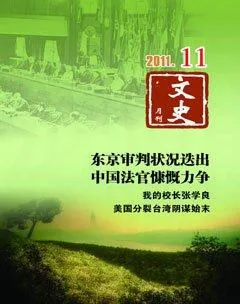大勢將去運難
1948年11月,杜聿明被蔣介石任命為徐州“剿匪”總司令兼前進指揮部主任,邱清泉為“剿匪”副總司令兼第二兵團中將司令官,二人同劉峙一道,指揮淮海地區(qū)80萬國民黨軍隊同人民解放軍進行大決戰(zhàn)。
12月4日,華東野戰(zhàn)軍在徐州西南130里處的青龍集、陳官莊地區(qū),將杜聿明集團重重包圍起來。
一、大戰(zhàn)臨頭,國民黨高官熱衷于測字,不知測字高手本是中共地下黨員
杜聿明的前線指揮部設在陳官莊農民陳瑞興家里。這是一座四合大院,南房住著邱清泉,北房住著中將副參謀長文強等高參,西房住著杜聿明。院子中間有一棵水桶粗的老槐樹,葉落枝禿,在寒風中發(fā)出嗚嗚的聲音。
1949年元旦后的第二天,杜聿明正在院子里理發(fā),沒有突圍出去的原十六兵團監(jiān)察官尹天晶來了,邱清泉旋即把尹天晶叫到了大院的南屋。
原來,邱清泉最迷信算命,去年蔣介石欲調他到河南鎮(zhèn)守商丘,邱清泉聽了面如土色。原來,早有高人給他指點迷津——遠離或避開“商丘”。為何?“商”與“傷”諧音,“丘”與“邱”同音同義也。這尹天晶平素善觀天象,深諳陰陽五行,更會江湖藝人的相面測字,不少國民黨高級將官請他預測未來兇吉,常常八九不離十的。如今,在紛飛戰(zhàn)火中請尹天晶測一測字,顯得尤為重要。
邱清泉寫了個“榮”字讓測,心想這“榮”字不論怎么想都吉利無風險。
尹天晶看了連連搖頭,不說話。
邱清泉說:“你我早已成生死之交,但說無妨!”
尹天晶道:“這‘榮’(繁體字寫作“榮”)字上面兩個火,象征一對蠟燭,中間部分‘冖’像墓臺,下面是‘木’字,代表棺木……”
邱清泉急忙打斷尹天晶的解說,掂一掂手中的鋼筆,眼神定在“筆”上,于是迅速寫了個“筆”字,要尹天晶測一測。
尹天晶還是搖頭:“這‘筆’(繁體字寫作“筆”)中‘聿’字乃‘建’破之象,‘建’無‘腳’,如何行走?倘若固守城池,必有一劫。”
此刻,旁邊圍觀的還有李彌、文強、孫元良等,眾人不解,認為尹天晶這樣讖析“聿”有牽強附會之嫌。緊張之余,眾人想放松一下,于是一起步入院子當中的槐樹下。
邱清泉意猶未盡,在槐樹下寫了個“古”字,尹天晶不予理睬,而是叫文強、李彌也寫個字試一試,邱清泉則不依不饒,非要尹天晶先測了“古”字再說。
尹天晶不得已道:“你在樹邊寫‘古’,合為‘枯’,你想,這枯字還有什么好測的?還是讓別人測一測吧!”
邱清泉道:“既然‘古’不好,那不測‘古’字,我在槐樹的邊加‘土’,使它有土不枯總可以吧……”
李彌聽了雙眼一瞪,連說:“不行不行。”邊說邊把頭往西屋方向的杜聿明點了點,眾人心領神會。是啊,這“樹木”邊加“土”不是“杜”么?
尹天晶看了看“杜”字,最后仰天長嘆:“不測了,說真的,這個院子不吉利啊!”
眾人疑惑不解。
“是這樣,”尹天晶比手劃腳,“這院子四院合圍,而中間卻是一棵大樹。樹也!即木也!諸位請看——”
尹天晶以右手食指在左手掌中劃了一個“口”,又在中間加了個“木”字,道:“這不是‘困’么?”說完又指了指剛才寫的“杜”字。
李彌心領神會,靈機一動:“各位不必驚慌,待我去組織人把樹砍掉!”
樹是砍了,可幾天了,圍卻還是未“解”。華東野戰(zhàn)軍還是把陳官莊方圓十里圍得水泄不通。
邱清泉又找來尹天晶問究竟。尹天晶掐指一算,細細打聽院中如今還住著多少人?答曰:“西屋住有杜聿明總司令及副官2人,南屋住有邱清泉副總司令、李彌等6人,北屋住有孫元良、文強等高參10人,共18人。”
尹天晶附在邱清泉耳邊悄聲道:“不好!原來是‘困’,砍去院中的槐樹沒有‘木’還剩‘口’,可院中三個屋子的‘人’有‘十八’,這‘十八’合起來還是‘木’,所以至今仍被‘困’住難以突圍!”
邱清泉趕緊把這個意思告訴杜聿明,走投無路的杜聿明撓了撓后腦勺吩咐道:“那就把部分參謀和副官另行安排住宿,院中人數(shù)不能是‘十八’!”
之后,邱清泉又問尹天晶,尹天晶道:“看來天意已定,院中人數(shù)雖不是‘十八’,但院中究竟還住有人,若有‘人’即為‘囚’。‘囚’也不是好兆頭啊!”
邱清泉知道大局已定,決定搞清楚自己的兇吉再說,旋即寫個“兵”字求測,剛寫完‘丘’字時,墨水不夠,于是隨便找了個破碗加了點墨水,續(xù)寫完“兵”字。
這一舉一動,被尹天晶觀個一清二楚,道:“‘破器偶然添硯水,切憂財耗人空虛’,你寫‘兵’字時只寫成‘丘’。說來話長,古人講究避諱,這避諱分為國諱、家諱、圣諱。‘丘’在古代指圣賢孔子,孔子名‘丘’,清朝時皇上規(guī)定,天下姓‘丘’的,要求加耳字旁改姓‘邱’,并且不許發(fā)音為‘邱’,要念成‘七’字。因此,這‘丘’屬避圣諱。以此而論,你大姓‘邱’,溯源實為‘丘’,你欲測‘兵’字卻少寫了下面的‘八’,這是少了能走會跑的‘腳’,不要再測了。恕我多嘴!”
邱清泉問:“那我們這個院子的李司令、文強高參……”
尹天晶道:“李彌司令的‘彌’,文強高參的‘強’是以‘弓’為旁,‘弓’似蛇,這蛇么?就要看他倆的造化了,‘溜’得如何。”
1949年元月20日淮海戰(zhàn)役結束后,有人對號入座尹天晶的讖語:杜聿明被俘,應驗了“建”破之象,還應驗了“十八人”,即使不是“困”,也為“囚”;而邱清泉在1949年元月10日率部分隨從騎馬突圍,結果先是坐騎被擊中“少”了逃跑的“腳”,隨后負隅頑抗被當場擊斃,應驗了“兵”無“腳”而亡之兆;元月10日這天,在十三兵團殘部最后向解放軍接洽投降事宜之際,李彌化裝成傷兵混出了包圍圈逃往濟南,而文強審時度勢放下武器,與杜聿明一起被俘后保住了性命,僥幸逃脫。
其實,這次測字,只是為了瓦解國民黨將官們的信心而已——這尹天晶何許人也?他表面上是十六兵團監(jiān)察官,其實是我軍安插在國民黨“剿匪”總司令部的一名中共地下黨員。
二、“命相缺水”的戴笠,死后在大雨中澆淋三日后才被找到
戴笠出生那一年的五月,其父不在家,正在參加關帝廟會,家中不知何故被人放火,大火延至堂屋,央及戴家香火。正巧此刻烏云驟起,狂風大作,很快便下了一場暴雨,才免于橫禍。于是戴笠的父親認為后代的命里不能缺水,便給兒子取名戴笠,以示避陽求水,號也為“雨農”。后來,戴笠的弟弟出生了,亦隨之取名叫“云霖”。
戴笠發(fā)跡后,為標榜自己的風雅,一次,他的美國顧問梅樂斯問其本名的出處,戴笠神秘地避而不談,取出一書《風土記》道:“此乃古人代取之!書中曰:卿乘車,吾戴笠,日后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君乘馬,他日相逢君當下……”
戴笠6歲喪父,母親藍氏含辛茹苦地拉扯他長大,后來戴笠離家出走,一去不歸,藍氏思兒心切,四處尋找。1922年一個風雪之夜,藍氏在關帝廟中尋找到失魂落魄的戴笠,帶回家中。戴笠后來在江山縣城邂逅文溪高等小學同學毛善余(即后來任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局長的毛人鳳),二人一商量,決定一起赴廣州黃埔投考。在廣州,戴笠投考了黃埔軍校第六期,被編入入伍生第一團。
戴笠一日在街上閑游,遇一算卦的盲人,他突然來了興致,便請這盲人算了一卦。盲人問了八字時辰,掐算了好一陣道:“你這先生八字不錯,命生貴,只是美中不足,命相中五行缺水,如果有了水,就是大富大貴之命。”
關于命里缺“水”之語,戴笠早已從母親口中聽過,如今聽了這瞎子之言,一時愣在那里,雙眼發(fā)直,不知如何是好,心想命中五行是前生注定的,無法改變。這時瞎子給他出主意,告訴他名字上用帶水的字,可補命中五行所缺之水。戴笠聽了很高興。
此后,戴笠在軍統(tǒng)本部用過許多“水汪汪”的化名,他所起用的化名有:江漢清、洪森、汪濤、徐清波、海濤源、沈沛霖、雷雨雯等。用得最多的化名是“沈沛霖”,因為自從取了此名后,他的老胃病很少發(fā)作,甚至罕有傷風頭痛,“天天如愿,事事順手”,軍統(tǒng)局的副業(yè)又一帆風順。因此,他認為吉利的名字應是含蓄寓言深刻的,不可粗心。
戴笠對化名極為認真,秘書幫忙擬好后,他都要由自己來修改,有時完全由自己來起。
1944年春節(jié)過后,戴笠手下的秘書英渠為討好主子,說“沈沛霖”這個名字用得太久了,外人都知道了,建議改為“洪森”,戴笠一聽,覺得此名確實比“沈沛霖”水分更足,不但立即采納,還獎賞了小秘書一支德國造的“小左輪”槍。
戴笠不僅對中國的迷信看得很重,對“洋”迷信也看得很重。歐美人最忌諱“十三”這個數(shù)字,戴笠一生中也極怕這個數(shù)字,認為這個數(shù)字會給他帶來不利。戴笠出生那年的那場火災,湊巧又是農歷五月十三日發(fā)生的(據(jù)傳農歷五月十三是關帝的生日),因而對“十三”這個數(shù)相當敏感,十分忌諱。
戴笠與胡宗南為莫逆之交。一次戴笠在西安與胡宗南打牌,打到第十二圈時,戴笠佯裝肚痛。胡宗南信以為真,找來軍醫(yī)診治,戴笠見到軍醫(yī)藥箱上印有“十三”的數(shù)字,連忙將他罵走。
在重慶時,歷任人事工作處處長的龔仙舫等人有次宴請戴笠,席間用的酒是“法國路易十三”,當戴笠得知杯中的酒是“路易十三”時,馬上傾灑于地毯上,憤憤拂袖離席而去。龔仙舫一幫陪客大惑不解,不知是誰得罪了戴上司,還好,老處長李尚自說出其中奧妙——戴老板喝什么酒都行,唯獨不沾“路易十三”!
西安事變以后,戴笠更是不可一世,他在西安霸占了楊虎城將軍的軍需處長王維之的一所花園別墅。
此別墅座落在西安楓橋13號。剛好美國海軍上校、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樂斯要來西安,戴笠指示將該院落進行修葺,手下人不敢怠慢,趕緊動工修整。修整好后,大家滿以為戴笠看后一定滿意,誰知他剛到門口,就一臉不高興,在院子里轉了一圈后,回到室內,命人立即將西安警察局局長肖紹興找來,劈頭蓋臉地將肖紹興臭罵一通:“誰定的門牌號碼?”肖紹興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怔怔地呆愣著,戴笠見肖紹興還楞著,一把將肖紹興抓到大門外,指著門牌道:“你們瞎了眼,將我的門牌定成這個號?”肖紹興顫抖抖地答道:“主任,您這房子確實應是玄楓橋13號啊!”戴笠厲聲道:“什么確實不確實?你給我馬上改為甲14號!”
盡管戴笠如此迷信數(shù)字和命相,然而軍統(tǒng)局秘書助理是位青年書生,接受了一些科學知識,不相信鬼神迷信和術數(shù)巫術,因而在替戴笠起工作化名時,故意不用水,而擬了一個缺水多山的化名——高崇岳。此刻戴笠正好不在局本部,去了天津,無法知道新名字的擬定,而毛人鳳此刻也稀里胡涂,沒有好好審查斟酌,竟也馬馬虎虎地批準使用。
1946年3月13日,戴笠去北平巡視后,準備飛往南京時,發(fā)覺當天是“13日”,不吉利,便借故牙痛難忍,將行期推到3月15日去天津。3月16日,戴笠飛往青島會見美國柯克將軍,不料柯克已去上海,3月17日,戴笠乘222號專機趕往上海。這天上午晴空萬里,下午13時6分,專機飛臨上海時,卻天昏地暗,雷雨交加。機場指揮不讓飛機著陸,只好改飛杭州,杭州也是雷電大雨,只好再改飛南京。
飛機飛抵南京上空時,正值滂沱大雨,雷電交錯,云層極低,222號專機與地面的電訊失去聯(lián)絡,一頭撞到了南京郊區(qū)江寧縣板橋鎮(zhèn)附近的岱山山腰上。三天后,這位命相缺水的軍統(tǒng)大員,在大雨中澆淋三天后才被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