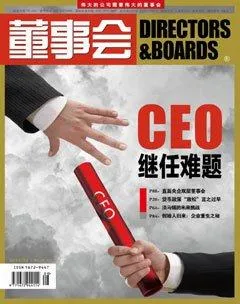科幻是一種精神
事實上,美國的科幻片即便發生在未來500年,它的主流價值觀仍然是美國當下的。如果說這種價值觀是停滯的,那么創造力卻是射線一般指向浩淼無際的未來
科幻片作為類型片,幾乎和電影同時誕生,以1902年的法國短片《月球之旅》為肇始。這是一部根據儒勒·凡爾納的《從地球到月球》和威爾斯的《第一個到達月球上的人》兩部科幻小說改編的電影。也就是說,科幻文學作品早已有之,電影只是新傳播技術對科學幻想的一個載體罷了。不過,直觀的視覺畫面對于科幻作品來說,是有突破性的。在此之前,科幻文字閱讀需要具備諸多苛刻的條件,比如科學素養和科技知識,比如基于此的個體想象力。換言之,人們終于可以“看到”外星球和未來的場景,而不是只能想象。
毋庸置疑的是,真正對科幻電影做出重大貢獻、成就最高的是好萊塢這個“夢工廠”。一百年來的探索和實踐,已使科幻電影在整個電影工業流程中同時細化到零件部分,并且產生眾多分支:超級英雄如《蜘蛛俠》、《蝙蝠俠》,滅頂之災如《后天》、《2012》,人獸大戰如《侏羅紀公園》、《金剛》,時空穿越如《猩球三部曲》、《回到中世紀》,天外來客如《ET》、《彗星撞地球》,太空遇險如《星河戰隊》、《火星任務》,人與機器如《機械公敵》、《變形金剛》……正所謂燦若繁星。
美國之所以能夠成為科幻大片不容質疑的最大供貨商,不外乎其是世界上尖端科技最發達的國家。沒有尖端科技上的軟實力,斥再大的巨資也難以實現科幻大片的拍攝工作。中國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積累了大量財富,但只能將資金投入到古代題材的權斗和戰爭方面,如張藝謀的《黃金甲》、《英雄》,以及吳宇森的《赤壁》等國產大片。比較之下,日本也是一個在尖端科技上領先世界的國家,它的科幻片雖不如美國那樣能覆蓋全球,但別有特點。哥拉斯和奧特曼雖然“低級”,但在中國的家喻戶曉已說明這個問題。不過,尖端科技雖為科幻片的基本條件,但并非決定性因素,包括投資也并非影片是否成功的關鍵。
最新美國科幻大片無疑是鄧肯·瓊斯的《源代碼》(2011)。這部電影在投資上并不小,涉及的也是一個關于穿越的話題。死者殘存的記憶、心理置換、反復輪回、拯救世界、更改時空……這些看點在好萊塢科幻片里都是日常的,并不為奇,好在全新的故事情節、流暢的電影敘述和精致的畫面語言使這部電影并不讓人失望。總之,電影的好看是毫無疑問的。不過,對比那部讓鄧肯·瓊斯名聲大噪的《月球》(2009),卻相對顯得平庸了許多。
《月球》故事發生在并不算遙遠的未來,人類在月球背面發現了一種巖石,它直接吸收太陽的能量,并在其中儲存為氣體氦3。為了開發新型資源,一家名為“月球巨人”的公司在月亮上建立了基地,從事礦石的挖掘工作。而山姆·貝爾是這個月球基地唯一一個員工,陪伴他的只有一名機器人戈蒂。在這孤獨而漫長的3年,山姆靠著憧憬退役后美滿的地球生活撐了下來。但當合同即將期滿之時,不尋常的事情發生了。一次事故中山姆救回了一個和自己長得一模一樣的“人”,他逐漸發現自己只是一個接二連三死掉之后被不斷復制的永恒勞工。關于復制或克隆,這部電影容易讓我們聯想到施瓦辛格的《第六感》和《逃出克隆島》,不過更讓人驚嘆之處是《月球》只有一位演員,只有靜止而閉塞的極其有限的兩個場景,耗資不超過500萬美元。這絕對是一個小成本電影。
《月球》起碼說明了一個基本問題:它有時并不用像《黑客帝國》那樣必須依托于最新的科技成果,投資和“大”更非決定性因素,它成功和動人的核心因素是創新和發現,也可以說和科技進步同屬一個過程。簡言之,就是探索精神和創造力。這不由得能讓我們聯系到西方文明和美國文化的特征,基于殖民主義的冒險和探索,無懼險境的騎士精神和牛仔精神。事實上,美國的科幻片即便發生在未來500年,它的主流價值觀仍然是美國當下的,關于倫理問題,關于環境問題,等等。如果說這種價值觀是停滯的,那么創造力卻是射線一般指向浩淼無際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