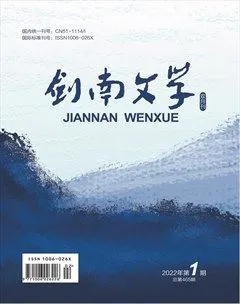綿州守藝(組詩)
□ 瓦 片
羌山口弦
流云,翠竹,飛瀑
皆可搓成,中空的清音
用麻繩,系住仰望,久遠
就系住了羌鄉密碼,與魂
上弦或下弦的月光,在唇尖憑欄
喊一聲是愛,喊兩聲是相思
羊角花開,開成花兒納吉
荷包繡進,阿妹的嬌羞
西窩羌寨的爾瑪,有雁南飛
白珠的羌紅,飄在春天里
古羌水磨漆
遠古刀法,能切出,精彩詞匯
為西漢或今朝,添一朵花
木質語言,專講有關木頭的故事
一章節一章節地講,百聽不厭
用上善的水,磨去所有戾氣,傲氣
就如李白,磨杵成針
在心扉上,鐫刻羊角花,民謠
飄飛的沙朗,悠悠羌笛
錦繡,數千年史冊
漆出,八百里河山
黃楊木梳
黃楊扁擔,一頭挑著土家民謠
一頭挑著,柳州三姐妹
在重華,最好的黃楊木,不做扁擔,
以百年時光,雕成梳子
梳少女的芳華,青絲,嬌羞
滿眼秋月,星辰
梳相濡以沫的,白發
夕陽西下的牽手,眷戀
梳田間小路,籬笆,炊煙
對某個昵稱,一生不變的,呼喚
李白詩意繡
詩仙云游去了,妹妹月圓在老家
為一壟壟竹,妝容
粉竹樓的心思,被愛詩的女子,讀懂
萬縷千絲的話語,束在指尖
以時光研墨,書寫丹青
李白的絕句律詩,歸隱于一根繡花針
繡個大月亮,掛在青蓮的山尖
李白嘞,你邀請嫦娥,還是鄉愁
繡出樵夫與耕者,出入畫屏
為盛唐詩歌,澆水,施肥,培土
聾派指畫
磨手為筆,自帶三千詩文
胸懷八百里溝壑,云水間謠曲
上善之水,在茶里,細語微瀾
聽禪音悠揚,指尖如蘭,清遠,虛無
一陽指獨步武林,相忘于江湖
寫山水,云朵上的星辰,鴻雁
二指禪歸隱祖訓,宣紙,田園
畫長短經文,春飛燕,高山天外天
在墨硯里迎風化雪,彈一曲琵琶行
用寂寥煮酒,醉成中國畫的,逍遙游
糧藝畫
麥穗在春天揚花,翻浪
稻子在秋天俯身,溢彩,飄香
這之后,紙上培土,布上澆水
把酒杯里的糧食喊回來,再活幾百年
寫部種子的萬國書,或傳奇
所有的方言膚色,在指尖,純粹
日子一粒粒挑出來,人生一粒粒貼上去
不潑墨寫意,也能參悟生命的寬厚
虛擬塵世斑斕,銘記豐谷,鄉愁
用雙手耕讀,堅守我們最本真的,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