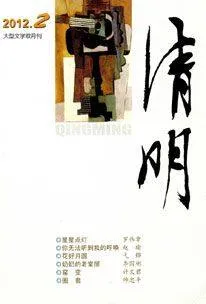四月
2012-01-01 00:00:00于繼勇
清明
2012年2期
四月了。太陽落得越來越晚。
我和羊橋坐在西老荒的土坡上,看一群羊啃草。太陽落得真快,像被大門縫夾著尾巴的豬,嗷的一聲,就掉下去了。
天紅得像殺豬血,潑灑在西邊村莊的上方。
肥
天黑透了,草雞還不上窩,一只只從樹梢子上飛下來,又飛上去,咯咯地叫。我和肥用竹竿搗樹上雞們的屁股,它們驚惶失措地飛下來,雞是雞宿眼,天一黑透就睜眼瞎,看不見路,不敢亂跑,很容易逮。
肥捉住一只,就遞給我,說:俺哥,給你一個。
她每逮住一只,就飛快地跑過來遞給我,說:俺哥,又一個。
肥是我妹子,五歲了。但她不是娘親生的,是娘在生產隊的棉花地里拾來的。肥當時裹著塊黑老粗布褂子,身上還有幾塊尿布。娘說,這孩子長得怪肥的。于是,“肥”就成了肥的名字。
娘拾肥的那天是處暑。趕集的劉瞎子拄著根細拐棍,篤篤地搗到我家,用棍子梆梆幾聲就搗開我家大門:大梁家的在屋里頭嗎?聽說你拾了個閨女,我掐指算了一下,這孩子你不能拾,你從哪兒拾的還得扔哪兒去,她是個禍害精。
娘兩手沾滿了面粉,從廚屋里探出頭,看了一眼劉瞎子,沒理他。劉瞎子對著大門板大聲說:這個閨女是個禍害。你不信我,以后吃苦的是你自己,你別怪我劉瞎子沒提醒你。
娘仍然沒吭聲,狠狠地朝地上吐了一口口水。呸。
屋里的肥,突然哇一聲大哭起來,嚇了我一跳。我正在剝豆子,嚇得我把剝好的豆子扔了一地。
這月子里的閨女,能聽懂人的話?娘盯著肥的臉,自言自語。
我不管,反正我得要個閨女,不管是自己生的還是拾來的,我都喜歡。……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