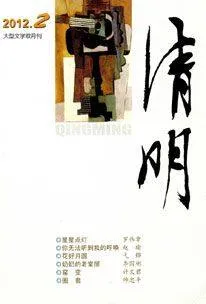放回原處
2012-01-01 00:00:00袁小平
清明
2012年2期
我叫方弟,出獄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一同出獄的還有一個叫王猛的獄友,是個毒販。
天氣晴朗,自由的陽光像燒紅的鐵水涌進發霉的胸腔,一陣劇烈的頭暈襲來,我蹲下身翻腸倒肚,把胃里漚爛的酸菜盡情地吐在監獄門外的地上。
一股酸水從鼻孔冒出來。自由的滋味真他媽難受!
后來知道那不是自由所致,而是西部某省發生了八級地震。這奇妙的偶合讓我啼笑皆非。我找到昔日的相好小梅,在她那里住了一天。三年沒碰女人,晚上睡在一起,動靜可想而知。小梅已經發酵,全身軟得不成形狀,但還是盡力推開我,說:“當心他拿刀剁你!這樣玩命,人都快死在你手里!”小梅收拾收拾,催促我走。
過去的都過去了。
路燈未滅,濃重的濕氣浮漾在灰藍的空氣中,東方已經泛白。一身空虛,沒處可去,我背著旅行包,漫無目的地沿著公路走。一輛環衛車停在路邊,正把垃圾桶吊上去,倒空渣滓,然后放下來。年老的環衛工人嘴里叼著一根煙灰很長的紙煙,向我做了一個避讓的手勢。我橫跨兩步,打算到盲道上去,不提防一輛載滿青菜的三輪車急馳而來,蹬車姑娘叫了一聲,龍頭急拐,車輪挺在路沿上,連人帶車翻了。老工人呆呆地“哎喲”一聲,紙煙掉在地上。
本能地,我想緊走幾步離開,這世界有點邪乎,我怕那女孩揪住我要醫藥費。回頭一看,姑娘滾了幾滾,坐起來啊啊地叫。原來是個啞巴。挺清瘦挺漂亮的一個女子。這讓我同情。老漢緊走幾步,過分熱絡地把女子扶起來。……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