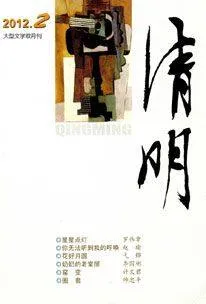我在北大的修煉
2012-01-01 00:00:00師力斌
清明
2012年2期
2008年6月下旬,我從北大暢春新園學生公寓搬出來,北大七年讀書生活結(jié)束了。說是讀書,實際上是讀書、聽課、辦刊、打工,四分天下。
我是拖家?guī)Э谏媳贝蟮摹?001年到2008年,我在北京換過十幾個住處。每當問起我的女兒,她總會說,暢春新園她最留戀,北大校園最好。
在2001年考入北大中文系讀碩士之前,每次出差到北京,總會抽空到北大來一趟。我有個同事在生物系讀研,住在靠小南門的40號樓,宿舍雖小,天地卻寬。我不止一次跟他說,你的現(xiàn)實就是我的夢想。我想死北大了。
考上北大之前,我曾狂妄地想,我比北大學生更像北大學生。發(fā)表過詩歌、散文,單位還資助我出過一個小集子。除了孔慶東、余杰,也沒有聽說中文系哪個學生寫過什么東西,天下也就那么三兩個人物。
然而,等進了中文系,開始上課后才發(fā)現(xiàn),自己是多么淺薄,多么狹隘。第一次受打擊,是在洪子誠先生的詩歌選讀課上。上課的學生濟濟一堂,很多人站著聽課,場面火爆,像是搶購。按說自己也是搞詩歌的,在這個課堂上卻像個門外漢。第一節(jié)課的發(fā)言就遭到了先我一步經(jīng)過嚴格北大訓(xùn)練的高材生們的批駁。洪先生的一名弟子有一句話刺激性非常大,大意是某某同學所秉持的仍是八十年代的知識儲備,言外之意是早已經(jīng)落伍了。當時,我還不太理解這句話的分量,還不明白是指一個人真正理解文學,特別是做當代文學研究,要經(jīng)過相當?shù)膶W術(shù)訓(xùn)練。因此,討論發(fā)言,寫論文,都是原來那一套隨感式,敢說敢寫。……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