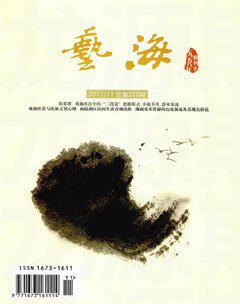不瘟不火 靜水深流
王強
一、 引言
京劇的形成自徽班進京以來已有兩百多年的歷史。毋庸置疑,京劇的發展首先是建立在其表演藝術的不斷精進之基礎上的。由此,許多專家、學者也指出了京劇發展過程中,其忽視文學性和戲劇性的“一大弊病”。甚至某些學者還曾直言:京劇藝術中根本就沒有文學性和戲劇性可言,京劇文學史更是無從談起。真的是這樣嗎?
乍一聽,這些觀點是有其一定道理的。
首先,縱觀京劇史我們會發現,所謂京劇名家,大多都是表演藝術家,其中既包括演員,也包括了樂師,但唯獨少見的就是編劇。雖然有齊如山、羅癭公等文化人參與,但他們所創作的劇本也大多是移植整理改編,無法與元雜劇、宋元南戲、明清傳奇中的戲劇文學相提并論。加之京劇劇目中有大量唱詞的確很“水”,甚至存在語法不通順的問題,無法與昆曲等劇種中那些行云流水的唱詞相媲美。如果僅從這兩個角度來判斷,似乎京劇藝術中,真的沒有什么文學性可言。
其次,由于京劇表演藝術的發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似乎使得我們完全可以拋棄文學性和戲劇性,而簡單地去欣賞京劇的表演藝術。京劇表演中強調的是“不瘟不火”,我們管看戲叫“聽戲”。京劇中某些劇目的確缺乏像地方劇種中那種激烈的戲劇沖突和鮮明的矛盾斗爭。某些“骨灰級”戲迷,去聽戲時經常遲到、早退。因為他們到劇場只是為了聽某折戲中的一兩段經典唱段。這種在欣賞過程中完全拋棄故事情節連貫性的做法,很容易讓人誤認為在京劇欣賞中,戲劇性已經幾乎可以被忽略了。
其三,自從王國維先生提出,戲曲“以歌舞演故事”的特性后,很多朋友便誤以為,戲曲重要的只是歌舞表演手段,而戲劇性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故事內容。因此,許多朋友在研究京劇的戲劇性時,也往往注重的是敘事性,或者以戲曲的敘事性來代替了戲劇性。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抱有弱化京劇文學性和戲劇性觀點的朋友不在少數,也似乎有一定道理。那么京劇中到底有沒有文學性可言?京劇中是否真的不需要戲劇性?京劇、文學性、戲劇性三者之間的關系到底如何呢?這也許都是我們直至今天,仍然可以探討和研究的問題!
二 、京劇與“文學性”
對于“文學性”一詞的定義和概念,無數的專家、學者都有自己的觀點和看法,應該說至今為止,仍然很難有一個定義能夠完全準確地表述這一概念。但是大家似乎又都有一個簡單的共識,即“文學性”首先是文學作品應該具有的本質特性。
而文學是指以語言文字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觀現實的藝術。因此既然文學性的傳播所依賴的載體首先是文學作品,那么她必然由文字組成,并且能夠伴隨文字而傳播。
顯然京劇并不能簡單地僅僅依賴于文字來傳播。美國戲劇家羅伯特?科恩曾經說過,“人們常常認為戲劇是一種文學形式,很多戲劇課程都是在文學系開設的。不但如此,很多劇作家都是詩人或小說家出身,或者身兼二職,既寫詩歌、小說,又寫戲劇。所以在很多人眼里,戲劇創作首先更像是一種文學活動。事實并非如此。”(《戲劇》簡明版第六版,【美】羅伯特?科恩 著,費春放 主譯,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頁)京劇也是這樣,雖然她有自己的劇本,但是最終的表現形式卻并非文字,而必須依賴表演、音樂、舞美等來共同完成。
2011年,京劇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而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曾明確提到,“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被各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其中包括:“1. 口頭傳統和表現形式,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2. 表演藝術;3. 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4. 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5. 傳統手工藝”。很顯然,文學并非“非物質文化遺產”,因此“文學性”也就必然不是京劇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的本質特性。
京劇是一種綜合藝術,她只有最終呈現在舞臺上,才是其完整的形態。如果說雜劇、傳奇中仍然能夠存在一些“案頭”之作,可以稱之為文學作品的話,那么京劇的劇本幾乎失去了這種被稱之為“案頭作品”的文學樣式。京劇劇本創作中的大量規律都是為了演出而制定的:唱詞的合轍押韻是為了演員更好地演唱;冷熱場的場次安排是為了觀眾更好地欣賞;大段唱腔的設置是為了更好地展現演員的唱功特點;人物男女性別的搭配是為了行當的齊全;臺詞的節奏感和韻白的韻律感是為了增強演員念白的感染力。總之京劇的所有劇本皆是為場上而作,為演出而作,為演員而作。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文學性僅僅是京劇藝術所具有的眾多特性中的一個。或者說,在京劇中存在的已經不再是文學性,而是“文學因素”。因為文學性已經不是京劇的本質特性,而僅僅是其眾多的組成部分之一。
如果是這樣,那么我們還何必糾纏于京劇是否具有“文學性”?因為答案不論是肯定還是否定,都絲毫不會減損京劇的藝術價值。
三 、京劇中的“文學性”與“戲劇性”
其實很多朋友在強調京劇中的文學性的時候,常常是把“戲劇性”也納入“文學性”的范疇當中,甚至認為具有“戲劇性”就意味著具備了“文學性”。因為張庚先生就曾經將戲曲稱為“劇詩”,黑格爾也曾經將話劇稱為“戲劇體詩”。
事實上“戲劇性”與“文學性”是有著很大差別的。張庚先生所說的“劇詩”是從戲曲美學的角度來描述戲曲表演所具有的獨特的韻律美,這與“文學性”的差別仍然是很大的。
人們之所以會將“戲劇性”與“文學性”混為一談,主要是因為大量敘事文學和戲劇一樣,都有連貫的情節,強調對于人物性格的塑造。可是從事戲劇創作的朋友都能夠感受到,其實在話劇或戲曲劇本創作的過程中,我們主要要做的就是壓縮敘事成分(如過場戲),而強調戲劇性成分(如重場戲)。戲曲不是講故事,其核心仍然是通過展現戲劇沖突來表現人物。雖然戲曲作品中也有大量敘事成分,但我們是通過簡單交待來完成的。
如京劇《霸王別姬》首演長達八個小時。可是到現在,我們看到舞臺上經常上演的,卻是“別姬”那一段戲劇性最強的折子戲。而這其中的劍舞則是重中之重。此時的虞姬已經決定以死來成全自己心中的英雄——霸王。可是,虞姬無法將自己的想法告訴霸王,于是要求為霸王表演一段劍舞。這段劍舞正是虞姬與霸王的生死訣別。如果按照“文學”的慣例,我們應該大量描述虞姬的內心,應該盡情表達虞姬內心的痛苦。可是此時的虞姬卻不能將內心的一切告訴霸王,因為她知道,霸王絕不會接受為了偷生而放棄自己心愛的女人這一結果。于是作者用“戲劇”的手法,來展現虞姬此時豐富的內心感受——一段純粹的劍舞。
讓我們看看虞姬的唱詞:“勸君王飲酒聽虞歌,解君憂悶舞婆娑。嬴秦無道把江山破,英雄四路起干戈。自古常言不欺我,成敗興亡一剎那……”此時虞姬所說的都是勸霸王重振雄風,絲毫沒有談到她對于霸王的訣別之情。可是我們可以想象,虞姬的劍舞不是處處都在表現自己對于霸王的愛戀與不舍嗎?她多想再多看一眼自己的愛人!她多么希望自己的死能夠換來霸王的東山再起!她即將與自己的愛人生離死別卻不能透露半點心聲!她的內心是多么的糾結與苦楚!所有這些情感,都蘊含于一段經典的劍舞當中。這段劍舞所承載的情感絕不遜色于一萬字的抒情散文!而在戲曲舞臺上,只要有這一段劍舞就足夠了!
這就是京劇中的“戲劇性”!她絕不用依賴于文學而存在。
當然,也可能有朋友會說,虞姬豐富的內心情感,不就是各種情節的發展所致嗎?豐富的情節本身就是“文學性”。這種觀點其實是以無限擴大“文學性”這一概念的外延的方式來包含了京劇中的“戲劇性”。筆者認為,如果將“文學性”這一概念的外延無限延伸,那其概念本身就失去了意義。
四 、京劇與“戲劇性”
也有朋友認為:“中國戲曲在其文學的階段就并不追求‘戲劇性,很少達到‘戲劇性的高度”(呂效平《戲劇本質論》,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8頁)。這種觀點,筆者實在不敢茍同。若真是如此,我們又何必將元曲分為“散曲”和“劇曲”呢?難道僅僅是以是否存在故事情節為區分?更何況,很多朋友對京劇中的“文學性”提出了質疑,如果我們再拋棄“戲劇性”的話,那京劇又還能剩下些什么呢?
呂效平先生在《戲劇本質論》中,用“劇場性”代替了戲曲中的“戲劇性”,認為“這個‘劇場性也不是‘戲劇性。當莊周之妻欲火中燒,在倫理與情欲之間痛苦徘徊時,當楊延輝與母親、發妻戀戀不舍,相擁而泣,而催行的更鼓一遍遍敲響時,這才是‘戲劇性。” (《戲劇本質論》第8頁)呂效平先生認為只有激烈的情感沖突和復雜的內心糾葛才是具有“戲劇性”的,而“《拾玉鐲》所表演的孫玉姣的天真、活潑和嬌羞,丑角媒婆對孫玉姣的天真、活潑和嬌羞的滑稽摹仿,雖然詩意盎然、趣意盎然,但并不屬于‘戲劇性。”(《戲劇本質論》第8頁)
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朋友也會像呂效平先生一樣,將京劇舞臺上那些看似平淡,沒有激烈的內在或外在矛盾沖突的場面,都歸結為沒有“戲劇性”的場面,并由此認定,戲曲表演中很多時候并不需要“戲劇性”。
在此我先舉一個例子,來與大家分享。
京劇《貴妃醉酒》是梅派的代表作,大家都耳熟能詳。我們看到,舞臺上的楊貴妃雍容華貴,沒有表現出任何劇烈的內在或外在的矛盾沖突。從舞臺上看,楊貴妃聽到皇上已經轉駕西宮的消息后,并沒有失態,也沒有表現出強烈的內心沖突,而是看似隨意地說了一句:“呀,昨日圣上命我百花廳設宴。哎,怎么今日駕轉西宮?哦,諒必是這賤人之意!咳,由他去罷!嚇,高、裴二卿看宴,待你娘娘自飲!” 隨后,楊貴妃由自斟自飲,繼而發展到讓高、裴二人敬酒,最后被高、裴二人誆走,全劇結束。
按照常理看,此劇根本沒有強烈的“戲劇性”。可事實上呢?當我們深入到楊玉環的內心當中之后,我們感受到的卻是極其豐富的人物情感。楊玉環受皇上之命,來百花廳擺酒侍君。結果,皇上卻去了西宮。這意味著楊玉環的失寵。但是楊玉環卻對皇上此舉敢怒不敢言。她雖滿心怨氣,卻無法發泄,唯有借酒澆愁。在百花廳中飲酒的楊玉環,借酒澆愁愁更愁。她空有一副絕世容顏,在這后宮之中卻沒有人欣賞,于是她開始挑逗高、裴兩個太監。此時雖然唱詞中和舞臺動作上沒有任何表現楊玉環怒火中燒、內心郁結的內容,可是當觀眾看到中國歷史上的四大美女之一,只能挑逗太監的時候,難道感受不到她內心的凄涼與痛苦?當觀眾看到楊玉環在太監面前下腰含杯、臥魚聞花的時候,難道感受不到這個女人生命中的最大不幸?如果說這出戲是并不具備“戲劇性”的,只具有“劇場性”的演出,那我真的就不知道,世界上是否還有真正的戲劇了!
同理,《拾玉鐲》中,孫玉姣那段表現其“天真、活潑和嬌羞”的表演,其實正是旨在將這樣一個“天真、活潑和嬌羞”的孫玉姣展現在觀眾面前。如果沒有這段表演,那么孫玉姣這個人物就是空洞、蒼白的,那么《拾玉鐲》后面的所有劇情都將失去人物性格的支撐,也必將失去其原有的“戲劇性”本質。正是這段表演,才將后面的情節納入了戲劇的范疇,擺脫了簡單地講述故事的非戲劇模式!
如果退一萬步說,我們忽視京劇中的“文學性”,筆者還能屏住呼吸忍痛接受的話,那么否定京劇中的“戲劇性”,則是筆者所無法接受的。
五 、結語
其實,戲劇中所有展現人性本真的內容都是具有“戲劇性”的。不論場面是火爆還是平淡,只要刻畫的是豐富、生動、真實的人物形象,觀眾就能感受到其中強烈的“戲劇性”所在。之所以很多朋友誤以為京劇中的“戲劇性”在很多時候可以忽略,那是因為京劇本身經歷了皇室文化的洗禮,因此在某些人物塑造上,更加強調“不瘟不火”,經常容易讓人誤以為這種表演本身缺乏“戲劇性”。事實上這種“不瘟不火”的獨特表演的背后卻是“靜水深流”的豐富情感,于平淡中卻蘊含著強大的戲劇動力。這正是所謂的“不瘟不火亦有戲,靜水深流也是情!”
(作者單位:中國戲曲學院。本文為北京市教委“中青年骨干人才培養計劃”成果,項目編號:PHR201008169)
責任編輯:尹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