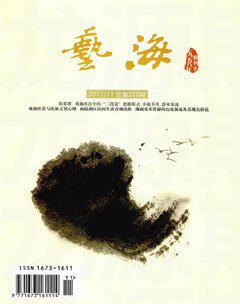清朝題材歷史電視劇視覺符碼讀解
王小娥 何靜
當前,作為敘事藝術和視聽綜合藝術的電視劇,其生產與消費均呈現出一派興盛的局面,而作為電視劇種之一的清朝題材歷史電視劇(以下簡稱“清史劇”)尤為如此。從《末代皇帝》(1988)到《末代皇妃》(2004)再到《太祖秘史》(2005),從《雍正王朝》(1999)到《康熙王朝》(2001),從《孝莊秘史》(2002)到“格格”系列,從《康熙微服私訪記》(1997)到《宰相劉羅鍋》(2001)、《鐵齒銅牙紀曉嵐》(2001),從《太平天國》(2000)到《走向共和》(2003)等等,帝王將相、王公貴族、公主格格之類曾在歷史上顯赫一時的權貴人物你方唱罷我登場,為中國電視劇史譜寫下重彩華章,不僅提供可供識別的時空信息,還致力于挖掘凸顯其獨有視聽敘事魅力的圖解符碼。本文擬從人物符碼與權力符碼等方面對“清史劇”的視覺圖解符碼予以讀解,以期挖掘“清史劇”塑造人物、表現權力抑或突出疆場廝殺宏大場面時蘊藏符碼間的特定內涵。
一、“清史劇”人物符碼讀解
電視劇中的人物符碼即指活躍于熒屏的人物的一種視覺符號能指,是人物外在造型的另一種展示,更是人物類型化模式化的別樣展現。“清史劇”中的人物符碼也不例外,它似乎總有自己的固定模式,人物符碼似乎永遠處在類型化的過程中。
首先,“清史劇” 的帝王符碼不僅體現出類型化模式,而且在“不變中求變”。作為至高無上的帝王,其視覺形象往往是高大、強壯、儀表端莊,如《康熙王朝》中由陳道明飾演的康熙皇帝、《雍正王朝》中由焦晃飾演的康熙皇帝及由唐國強飾演的雍正皇帝、《乾隆王朝》中由焦晃飾演的乾隆皇帝。而幼年登基的少年皇帝,其視覺形象往往是清秀、柔弱、少年氣盛、貪玩,如《康熙王朝》中的幼主康熙帝、《大清風云》中的順治帝、《欽差大臣》中的康熙帝。但隨著幼主年齡的增長,政權的回歸,這些帝王的視覺形象又變得高大、強壯、足智多謀。這里,帝王符碼隨著帝王年齡的變化而變化,凸顯了少年皇帝從幼稚走向成熟的成長過程。
其次,“清史劇”中的主要人物多數都有自己固定的明星類型。比如,斯琴高娃、李保田、王剛、張鐵林、張國立等,其中號稱“鐵三角”的王剛、張國立、張鐵林三人尤為典型。王剛分別在《鐵齒銅牙紀曉嵐》、《宰相劉羅鍋》、《少年嘉慶》中飾演了趨炎附勢的貪官形象和珅,使得觀眾一度將王剛與和珅等同一人。張鐵林則一度在《滿漢全席》、《鐵齒銅牙紀曉嵐》兩部劇中獨占帝王的寶座,飾演了康熙、乾隆兩位性格迥然不同的帝王角色。最為甚者可能要數張國立了,他曾一度在《康熙微服私訪記》、《少年寶親王》、《宰相劉羅鍋》中飾演了“康乾盛世”的三代君王——康熙、雍正、乾隆,并在《鐵齒銅牙紀曉嵐》一劇中出演紀曉嵐這一角色。“清史劇”中固定明星陣容的出現,無不預示著劇作人物類型化模式化的愈趨成熟。
二、“清史劇”權力符碼讀解
“權力”,在詞典上被詮釋為“政治上的強制力量”,《辭源》則釋為“權勢和威力”。總之,是執掌權柄,掌權、當權者也。在封建社會,帝王執掌著最高的權力,國家即朕,朕即國家。黎民百姓只配當統治者的牛馬和奴隸。而“權力符碼”,它并不是權力與符號的簡單相加,而是通過特定視覺符碼的設置來彰顯權力。
在“清史劇”中,最顯著的權力符碼當屬服飾符碼了。作為一種符碼,服飾關涉能指和所指,它往往是權力和價值的最直接體現。“清史劇”中,除了高高在上的帝王身穿黃色的龍袍上朝外,但凡官員上朝都得穿補服,而補服又是區分官職品級、權利大小的重要標志。權利的大小主要通過補子的圖案、補服的色彩及腰帶的色彩來體現。比如,《乾隆王朝》中一品大員紀昀每每上朝都身著繡有仙鶴的紫色補服,腰系藍色腰帶。較之紀昀的服飾符碼,和珅的服飾符碼在劇中經歷了幾次變化,比如當他以阿桂軍中書辦身份飛馬給乾隆帝送來六百里加急之時,他的服飾符碼是最為普通的朝服。當他因查處貪官王亶望而獲五品實缺在戶部任職之時,他的朝服“搖身一變”變成了白鷴補服。隨著他官職品級的不斷晉升,最終紫色仙鶴補服取代了他的白鷴補服。從和珅服飾符碼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出和珅權力的不斷擴大。此類服飾符碼在“清史劇”中比比皆是,鑒于篇幅有限,在此不一一例舉。
“清史劇”中的官員可以通過服飾符碼來凸顯自己的權力,“清史劇”的女性同樣可以通過自己的服飾、裝束來體現自己的權貴。不管是《雍正王朝》還是《乾隆王朝》,但凡“清史劇”中的尊貴女性往往身穿秀美的旗袍,頭梳高高的發髻,腳穿“花盆底”旗鞋;宮女的服裝也是根據她們職務的不同而設計的,往往職務越高,權力越大者服裝也就越華貴,越往下者服裝色彩就越暗淡,甚至呈石青色。比如,《康熙王朝》中,容妃受寵之時其服飾便明顯體現出她的雍容華貴,而當她被貶去刷馬桶之時,她身上所穿的是白底藍花的單衣,抑或是臨死前的純黑單衣,一律的“平民色”。這里,服飾符碼在編碼與解碼中的裂變彰顯出容妃權力的逐漸被剝奪。
可以說,服飾是反映權力的重要符碼,卻不是唯一符碼,“清史劇”中的馬車、轎子等代步工具的不同也可以區別權力的大小。一般說來,一品大員乘坐的是綠呢大轎,其馬車也只能駕兩匹馬,因為駕三匹馬是皇上的“專利”。并且,綠呢大轎也好,駕兩匹馬的馬車也罷,這樣的殊榮只屬于一品大員本人,其他人即使是家人也不能逾越。《乾隆王朝》第二十四、二十五兩集便運用聲畫蒙太奇這一影視語言講述了李矩璨火燒和珅綠呢大轎的故事。故事是這樣展開的,和珅舉薦普道昭入仕且親筆題寫“廉”字相送以提醒普道昭為官要清正廉明;湖北中丞李矩璨得知此消息后,向和珅求“廉”字遭拒,因報復心理作祟,當他無意間發現和珅的管家劉全非法乘坐和珅所擁有的綠呢大轎時,便借機火燒和珅的綠呢大轎并抓捕了劉全。同樣是火燒和珅的綠呢大轎,《鐵齒銅牙紀曉嵐》則以另一種方式予以展示,燒車中丞李矩璨被紀曉嵐的部下海升取而代之,所謂的報復心理在此卻成了“純粹的看不慣”。不管是《乾隆王朝》中李矩璨因報復心理作祟而火燒和珅的綠呢大轎還是《鐵齒銅牙紀曉嵐》中海升因看不慣而燒和珅的綠呢大轎,無形中都達到了一個殊途同歸的效果——以綠呢大轎這一符碼象征和珅的權高位重,并突出了綠呢大轎這一符碼與權力之間的對應關系。
“清史劇”中,除了服飾、馬車、轎子等系列符碼被常用于彰顯權力外,頂戴花翎也是這眾多權力符碼中的一種。賞三眼花翎,摘去頂戴等敘事情節在“清史劇”中比比皆是。編導往往運用聲畫藝術將朝廷官員的晉升與貶庶等情節再現觀眾眼簾,以此凸顯頂戴花翎在權力表現中的符碼作用。另外,黃馬褂也是“清史劇”中彰顯權力的重要符碼。“清史劇”也就是在這一系列符碼的編碼與解碼過程中完成對權力的彰顯的。
“清史劇”中,除了類型化的人物符碼及以服飾、轎子、馬車為代表的權力符碼外,還有諸如“建筑”、大炮、馬匹等較為明顯的視覺形象。幽深的宮苑、宏偉的大殿、獨具特色的四合院、矗立街旁的古玩小店及官道上隨處可見的驛站、客棧構成了“清史劇”建筑符碼的一大特色,并飽含豐富的人文內涵。比如,“清史劇”中,建筑群落宏偉壯觀的外觀及精心雕刻的裝飾,既體現出北方建筑的雄偉,又凸顯了江南水鄉的秀美,體現了南北大融合、滿漢一家的民族大一統思想。而飛奔的馬匹,有著雄健之美,在一定程度上象征了男性的威嚴和中心話語地位的堅不可摧。在“清史劇”中,長矛、大炮是沙場士兵用來御敵、保家衛國的主要工具,因而也就輕而易舉地被讀解為男性生殖器的象征。“長矛、大炮”成為性別癥候的同時,也是沙場將士實現自我抱負的主要工具,將士一旦被俘抑或是被撤職,“長矛、大炮”便成為他失勢的一種隱喻。總之,符碼作為一種能指和所指,它在“清史劇”中無所不在,符碼在不斷的編碼和解碼中,更好地以視覺圖碼的形式完成“清史劇”的敘事。
(作者單位:南昌大學影視藝術研究中心)
責任編輯:翁婷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