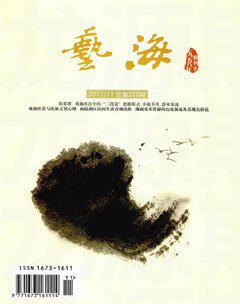論音樂學教育專業學生知識體系的建構
延劭楠

摘要:本文通過對《骷髏之舞》這首交響詩所涉及的音樂體裁形式、作品中服務于音樂情境傳達的配器手法,以及與《骷髏之舞》選取的題材內容關聯的音樂情境與文化淵源等三個方面的分析解構,將這首作品作為眾多知識的結點,所體現出的知識點、知識脈絡,乃至最終建構成知識體系的方方面面梳理清晰,目的在于提請執教者以此為思路進行教學改革,以更好地把握音樂學教師教育專業教學的特殊性與綜合性。
關鍵詞:骷髏之舞音樂情境文化淵源知識體系
《骷髏之舞》(Danse macabre,又名《死神之舞》)是一部以小提琴為主奏樂器的管弦樂交響詩,它是法國作曲家圣桑(Camille Saint-Saens,1835-1921)四首交響詩中最著名的一首,也是他的作品中流傳最廣的一首。在目前的音樂欣賞課程教學中也是較常使用、影響范圍較廣的一部作品。
樂曲圍繞著一個古老的神話展開:西方國家的人們在每年的11月1日要過萬圣節(又稱鬼節)。據說,在這天的午夜時分,地下所有鬼魂都要聚在一起狂歌亂舞。于是樂曲伊始,豎琴在弦樂器持續和弦的襯托下,準確撥出十二聲,宣告了午夜12時——“魔鬼時刻”的到來。墓地石門緩緩打開,眾鬼魂紛紛從自己的墓穴中爬出,為首的一個現出骷髏形象的就是死神,他手里拿著一把小提琴,鄭重其事地調著弦(按照作曲家的要求,小提琴將E弦降低半音,與A弦形成減五度,營造了一種古怪的、與現實相隔離的音響效果),而后“瀟灑”地演奏起一支節奏刻板、粗魯的圓舞曲。這時小提琴的下行音調伴著長笛的旋律,使音樂顯得更加陰森和慘淡。之后出現了一支與前面的旋律形成鮮明對比的新主題,它的旋律流暢而連貫,并帶著一種嘲諷式的熱情。這兩支旋律不斷變化反復,同時穿插著由木琴敲擊聲所代表的骨頭相碰的音響和用來贊頌死神的天主教古老旋律的變奏。音樂就這樣不斷走向高潮,象征著眾鬼魂的舞蹈越來越熱烈。突然,狂亂的舞蹈終止了,圓號的和弦暗示了黎明的微曦,雙簧管模仿著雄雞的啼叫,這時的眾鬼魂競相逃入墓穴,只有死神的小提琴勉強發出幾聲有氣無力的哀鳴,隨即也慢慢隱去……天亮了。
《骷髏之舞》作品本身音樂意境的傳達,貌似僅僅具有傳神的描繪性,似乎可以歸入通俗性的管弦作品之流。而究其外延與內涵、從形式到內容、從創作技巧到文化淵源,卻極有挖掘的余地。
一、《骷髏之舞》涉及的音樂體裁形式
《骷髏之舞》涉及的音樂體裁形式通常是作為音樂欣賞課程最基本傳授的知識點。作品可以從兩種體裁入手進行講解:第一,交響詩;第二,圓舞曲。
交響詩體裁是興起于19世紀中葉的一種單樂章的,具有描寫或敘事性、抒情性或戲劇性質的標題管弦樂曲。從這個層面分析,《骷髏之舞》的確是具有敘事性過程的標題管弦樂曲。而圓舞曲體裁的體現,在于作品使用了符合圓舞曲的、以“強、弱、弱”為基本節拍特征的3/4拍,同時,作品中“死神”的形象也分別呈現了“操琴——調弦——演奏圓舞曲”的過程。
二、《骷髏之舞》中服務于音樂情境傳達的配器手法
《骷髏之舞》為了更好地傳達作品特殊情境,使用了變調定弦、木琴的特殊音色等配器手法。
變調定弦在廣義的古典音樂作品中是不常使用的手法,而在《骷髏之舞》中由于變調定弦手法的運用,使得這首圓舞曲顯得十分怪誕,但這正契合了“鬼節——深夜——鬼怪妖魔之舞”的敘事性情節的應有氛圍,是對作品情境的最恰如其分的描繪。同時,變調定弦形成的減五度(減五度中世紀宗教音樂中是被禁止使用“魔鬼三全音”)的不協和感恰恰可以體現對于中世紀宗教音樂穩重、均衡的一種挑戰(相對于第三部分——文化淵源而言)。
木琴在作品中的戲份并不很多,但它的運用的確達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枯骨相碰的音色特質。
三、與《骷髏之舞》選取的題材內容關聯的音樂情境與文化淵源
“神鬼情結”似乎是古今中外各民族、各地獄、各文化系統中共通的文化現象,單就好萊塢出產的電影目錄中就有枚不勝舉的例子,例如,《木乃伊》就被港臺譯名為《神鬼傳奇》。如果僅舉一例來說明與《骷髏之舞》音樂情境相似的作品,應該非俄羅斯民族樂派作曲家穆索爾斯基(M?Mussorgsky ,1839-1881)的《荒山之夜》(A Night on the Bare Mountain)莫屬了。
“黑夜降臨,地下傳出亂哄哄、陰慘慘的聲音,妖魔們紛紛出現在黑暗中,魔王由眾妖魔簇擁著上場,舉行了祭奠儀式。之后是喧鬧的“圣宴”與狂歡。在狂歡進行到最高潮時,教堂的鐘聲響起,眾妖魔立即四散消失,因為東方現出黎明的光輝,太陽就要升起來了。”
同為交響詩體裁,同樣展現了“神鬼情結”。而我們如果以此進一步分析兩部作品所滲透出的文化符號,恐怕依然有文化淵源值得去探究。
我們仍以《骷髏之舞》為例,樂曲中段曾引用中世紀天主教安魂彌撒中著名的“末日經”旋律(見譜例)作為素材,進行了戲謔化的變奏。如何進行變奏?本文在此不做分析,重點在于“末日經”的歷史文化背景與影響值得擴展分析。
“末日經”片段
末日經,拉丁文為Dies Irae,意為“震怒之日”(Day of Wrath),是天主教“安魂彌撒”(亦譯為“追思彌撒”)十二段經文中的第五段,內容描寫世界末日到來時,號角聲四起,已過世的人都將從墳墓中復活起來,聽候最后的審判。
從西方音樂史的廣闊范圍中進行研究,與“末日經”有關系、甚至與《骷髏之舞》相似,直接應用“末日經”旋律或進行變奏的作品為數不少,筆者在此做了不完全的統計(宗教聲樂作品中為數眾多,在此不作涉及):
圣桑:交響詩《骷髏之舞》中,引用“末日經”。李斯特:《死之舞》, 以“末日經”為主題創作的鋼琴與管弦樂隊的變奏曲,與《骷髏之舞》同一題材,描繪中世紀傳奇的意境。柏遼茲:《幻想交響曲》第五樂章“女巫夜會安息日之夢”中,引用“末日經”旋律。帕格尼尼:第24首隨想曲,引用“末日經”。伊薩依:第二小提琴無伴奏組曲,四個樂章均使用“末日經”旋律進行音樂的發展。
拉赫瑪尼諾夫有眾多作品使用“末日經”素材——《死之島》,《帕格尼尼主題狂想曲》op.43,第7、10、24變奏 ,《a小調第三交響曲》op.44,《交響舞曲》op.45。為何有這么多作曲家醉心于這個題材內容,并通過各自創作展現其深邃悠遠的歷史文化積淀,已非本文的主題。但透過《骷髏之舞》這一知識結點所引申出的龐大的知識體系,的確需要由教育的引領者逐點、逐線、逐面、乃至立體的呈現給學生們。
針對《骷髏之舞》這部作品,也許作曲家創作之初并未思考過將如此多的內涵賦予其中,但通過后人的欣賞、品鑒,的確解讀出其豐富的內涵。如果每個學習者抱有如此探究的慧眼,將知識體系化整為零、統零為整,或許只是簡單的過程而已。而解讀眾多內涵的思路,恰恰印證了由點串線、并線成面、面面層疊,最終建構立體知識體系的過程。這一點,對于強調綜合能力實現的音樂學教師教育專業學生而言尤為重要,同時,也應該引起執教者對于教學思路、教學手段、教學過程等方面問題進行思考、調整、更新的關注。
參考書目:
1.《世界名曲欣賞》(歐美部分),楊民望,上海音樂出版社
2.《外國音樂欣賞》(第二版),錢仁康,高等教育出版社
3.《歐洲音樂簡史》(第二版),錢仁康,高等教育出版社
4.《西方音樂史》(修訂版),黃騰鵬,敦煌文藝出版社
(作者單位:蘭州城市學院音樂學院,此文為“優化課程培養體系,提高教師教育專業學生素質”系列論文)
責任編輯: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