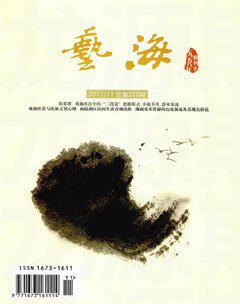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董世忠
摘要:許多百年照片已成為歷史變遷的見證,它們作為文化的傳承者、守護者和傳播者,超越了影像本身,具備了深刻的社會文化意義,是一種最直觀的記史方式。從三寸金蓮到長辮馬褂,從老房老街到各種交通工具,從小攤小販到老字號招牌,涵蓋了攝影所要表現的內容。可見,這些具有文化學、社會學內涵的影像,既是珍貴的歷史史料,又有獨特的中西文化傳播藝術的價值。
關鍵詞:湯姆遜影像傳播
19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歷史是段屈辱的歷史,主權喪失,處處挨打,經濟、政治、文化受到了西方列強的沖擊。當資本主義列強向中國傾銷商品并大量掠奪原材料的時侯,西方一些先進的科學技術也隨之傳入中國,西方攝影師就是在這一時期同鴉片和槍炮傳入中國的。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英國的大炮破壞了中國皇帝的權威,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攝影師作為中外文化交流的媒介出現在清政府的外交活動中,而作為中國時代特征的國內攝影師們在這個特殊的年代并沒能完成其歷史使命,在那段激蕩的歲月他們并沒有為后世留下讓人印象深刻的攝影作品,他們也沒有廣泛深入到當時的社會生活中去拍攝。但這又是必然的,因為中國攝影是在滯后的政治經濟條件與新舊文化沖突的夾縫中生存發展的。清末真正廣泛深入的涉及到中國社會生活的攝影師要數約翰?湯姆遜。約翰?湯姆遜1837年生于英國愛丁堡,1862年,湯姆遜首次游歷亞洲,并開辦了一家專業照相館。湯姆遜深深地被當地文化所感染,于1868年再次返回,后遷居香港,并在1868年至1872年間游歷了廣東、福建、北京以及華東和華北地區,然后南下長江下游,行程近8000公里,用鏡頭拍攝了晚清中國的大量圖像。1872年,湯姆遜回到英國后,開始積極地向公眾宣傳中國。他的攝影作品使得19世紀歐洲對亞洲的認識大為改觀,填補了東西方之間的視覺空白,他也獲得了“中國通”的美譽。雖然他不是最早到中國攝影的西方人,但確實是第一個最廣泛拍攝和傳播中國的西方攝影家”。
現在能看到的中國清末人像攝影原作,能留存于世的已不多見,特別是中國早期一些反映平民百姓生活內容的照片,多為當時外國游客或傳教士所攝,大部分已留傳于國外,其中約翰?湯姆遜的關于香港和北京兩地攝影實踐的記錄為我們研究中國早期攝影史提供了十分寶貴的資料。早期在中國拍攝西方攝影師大多都抱有一種獵奇的心態,對中國人充滿了敵意和曲解。因此,小腳女人、乞丐等社會的陰暗面成為攝影師拍攝的主題,拍攝的人物大都神情木訥、呆板。但當我審視湯姆遜拍攝的中國照片時,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的中國人輕松、自然的笑臉。湯姆遜來到中國時,雖然他也深感清政府的腐敗,覺得“改革應當是政府本身的改革”而對中國人民,湯姆遜用切身體會說道:“我在中國的感受是:中國人相當誠懇、好客。我相信任何一個能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思想及能使對方理解的外國人,在中國的大部分旅途中不會遇到什么敵意的對待”。可以看出,湯姆森對中國人民的態度是友善的,對中國人民是有同情心的,這種思想感情也表現在他的許多作品中。在這些照片中,我們看到了小姐的自然、丫環的敦厚,孩童的天真無邪,新娘的憂郁、無奈……在今天看來,依然有著強烈藝術的感染力。
湯姆遜攝影作品有意識地脫離了早期傳統的拍攝靜態人物的方式,拍攝了大量動態的肖像和群體照片。如,喊號的更夫,給小姐梳頭的丫鬟,磨刀的匠人等,這些照片,不像我們今天抓拍那么簡單,一個簡單的動態往往要花費很長時間來完成。攝影師為了讓被拍攝者保持某個姿態而需要耐心地和他們溝通。雖然湯姆遜有中國的助手和翻譯,但在當時封建的中國,尤其是在內陸地區,需要攝影師在一個盡可能短的時間內說服被拍攝者配合,需要極大的耐心和真誠的溝通。中國人喜歡全身照,喜歡左右對稱,不喜歡臉上有陰影。受到西方正統教育的湯姆遜,對中國人的攝影審美雖然能夠理解,但他在攝影創作中,并沒有象很多當地的外國攝影師那樣單純地迎合本地市場需求,仍然堅持以自己的藝術理念拍攝了大量中國人的肖像,為我們從另外的一個視角保存了一份早期的歷史遺存。他在新加坡和香港拍攝了大量中國人的側面肖像,半身照片或頭部特寫,作為一個商業攝影師,這是要冒風險的,因為很多中國客戶并不喜歡這樣的作品。當然在旅行拍攝中,湯姆遜也保持了他的一貫藝術創作風格,有意識地攝制了大量的特寫肖像。從照片人物的服飾、化妝及所配道具上,我們仍可以看出當時市民所追求的生活方式與時尚。從沿海的香港、廈門、福州到內地北京,從客家農婦到滿清格格,這些珍貴的照片對我們研究清末女子頭飾和服飾演變提供了珍貴的參考。
湯姆遜的攝影,是早期西方攝影術與中國傳統文化有機結合的產物,他的肖像攝影風格一直在影響著現代港臺婚紗攝影的化妝風格。
參考文獻:
1.廣東僑網http://www.gdoverseaschn.com.cn
2.約翰?湯姆遜. 鏡頭前的舊中國[M]. 中國攝影出版社,2001年7月
(作者單位:西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
責任編輯:劉小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