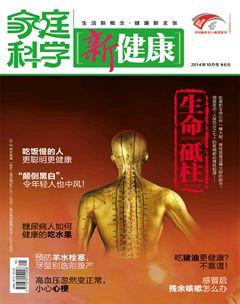吸氧并非越多越好
張昕
很多人認為,吸氧是越多越好。其實,高濃度氧療很可能會導致氧中毒,甚至抑制呼吸。吸氧一定要遵從醫(yī)囑,不可盲從。
遼寧省名中醫(yī)張艷說:“家庭氧保健如今正被越來越多的患者所接受。它不僅是緊急情況下救心救腦的必要措施,在日常生活中患有心、肺慢性疾病的患者也可以通過低流量吸氧,緩解癥狀、控制病情發(fā)展,從而改善長期的預后。我在臨床中,常常建議有心腦血管疾病的人,尤其是年齡偏大的,家中最好備用氧氣袋和氧氣瓶,根據(jù)自身情況每天吸氧2小時左右。”
很多患者認為,吸氧是越多越好。事實上,高濃度氧療可導致氧中毒,反而抑制呼吸,出現(xiàn)胸骨后不適及疼痛,吸氣時加重,咳嗽、呼吸困難等。
因此,家庭氧療一定要遵醫(yī)囑進行,在操作時還應該注意以下五點:1.密切觀察氧療效果,如呼吸困難等癥狀減輕或緩解,心跳正常或接近正常,則表明氧療有效。否則應尋找原因,及時進行處理。2.高濃度氧療不宜時間過長,一般認為吸氧濃度>60%,持續(xù)24小時以上,則可能發(fā)生氧中毒。3.對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加重患者給予高濃度吸氧可能導致呼吸抑制使病情惡化,一般應給予控制性(即低濃度持續(xù))吸氧為妥。4.氧療注意加溫和濕化,呼吸道內保持37℃溫度和95%—100%濕度是黏液纖毛系統(tǒng)正常清除功能的必要條件,因此,吸入氧應通過濕化瓶和必要的加溫裝置,以防止吸入干冷的氧氣刺激損傷氣道黏膜,致痰干結和影響纖毛的“清道夫”功能。5.防止污染和導管堵塞,對鼻塞、輸氧導管、濕化加溫裝置、呼吸及管道系統(tǒng)等應經(jīng)常定時更換和清洗消毒,以防止交叉感染。吸氧導管、鼻塞應隨時注意檢查有無分泌物堵塞,應及時更換,以保證有效和安全的氧療。
張艷最后特別提示,經(jīng)常有中高考的學生家長咨詢是否應該給孩子吸氧以提高考試成績。其實,吸氧和提高智商沒有任何關系。吸氧僅是營養(yǎng)物質糖在氧化代謝時的“助燃劑”。腦是機體中耗氧量最高的器官。高強度腦力勞動時,腦氧量會有所增加,但很有限,通過自主調節(jié)增加血液即可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