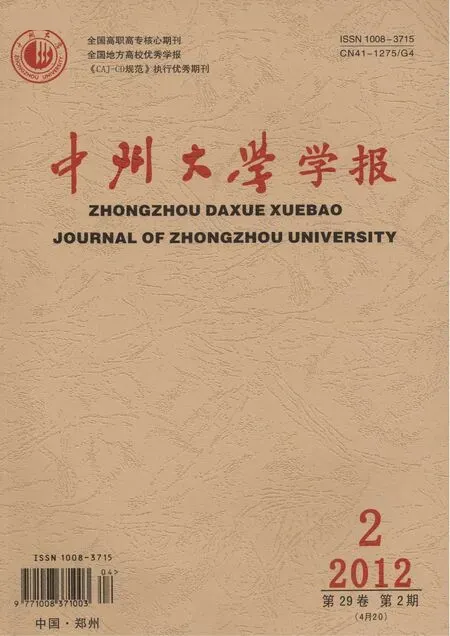中國現代小說鄉土語言的產生及發展
劉 恪
(河南大學文學院,河南 開封475001)
一
討論鄉土語言,我們采用地方性生產一詞是最合適的。語言長于泥土會有無限的生命活力,語言離不開地方環境,從特定的水土里長出來,這使語言具有成長的概念,有一種內在的活力與能量,大地與人成為語言的直接源頭,這種語言會有一種天然的質地,我們可以從中梳理出一種鄉土精神與氣韻。“每一個大洲都有它自己的偉大的鄉土精神。每個民族都被凝聚在叫做故鄉、故土的某個特定地區。鄉土精神是個偉大的現實……”[1]230我們是否可把它的秩序如此理順一下:鄉土——鄉土人——鄉土語言——鄉土精神。這種鄉土精神是世界性的,歐洲自塞萬提斯起,勞倫斯、巴爾扎克、莫泊桑、左拉、維爾加、哈代、屠格涅夫、契訶夫、托爾斯泰等人都有偉大的鄉土小說。在美國,魯尼思有關紐約的故事,凱布爾的南部風情,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塌法等,被稱為地方小說或地方色彩。它的含義指“強調背景,人物對話和某一特定地區的社會結構和習俗,不僅有地方色彩,而且影響人物的氣質、思維方式和感情。”[2]221這個解釋,幾乎可以視為鄉土小說的經典定義。
中國是鄉土小說的大國。其一,中國是歷史悠久的農業大國,農耕文化決定大部分人都依靠土地而生存,中國的民居不是以聚集方式,而是散落在山灣水邊,這是一種由大地而決定的生活方式。其二,20世紀以來的現代小說家幾乎90%是農民出生,或者和土地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中國小說家作為鄉土小說的代表似乎也是極為自然的。其三,中國現代小說的發源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產生在鄉土文學之上,魯迅被推為現代小說創作的第一人,后來現代小說無論涌現出多少分支,均會追溯到魯迅所開創的局面上來討論。
在這樣一個鄉土大國產生的鄉土小說,我們如何道出它的總體特征呢?因為中國地大物博,南北形勝與氣候很不一樣,東西部習俗差異巨大,鄉土在各地方均有自身特色,如何總體稱謂,最典型的恐怕是鄉俗土語特征。鄉俗也許是在人群之間,或人與環境關系里產生的。土語是各地特征與人的性情的自我表達。在鄉土文學里,地域不是一個整體概念,而是一個分割概念,南方多水多山,人們分割在一些很小的局部里,形成了所謂的“十里三音”,百里之外的人群相遇,語言是無法交流的,許多土語無法聽懂。廣闊的北方,語言流通好多了,但每個郡縣的語言也依然不一樣,風俗也彼此有別。特定地域產生的鄉俗土語正好讓彼此的地域區別開來,形成各自的特點。因而在全球范圍內或中國的土地上,并不會有統一的鄉土文學。有了這個理解前提,鄉土小說的特質也就好把握了。這里不是討論鄉土的類型小說,而僅指它的語言。鄉土語言一定是依地域而生成的,其次才是因人的秉性不同產生表述方式的特點,語言的地方特色是本體,語言個人風格的相異則可能是血型、氣質、愛好、脾性、修養等導致的,因此我們可以說語調、語感是個人的,語象和語式則是地方的。當然腔調也會有濃厚的地方因素,但腔調的話語態度、速度、強弱、輕重則又是個人的。丁帆在討論鄉土小說時把它的特征歸納為:三畫四彩,即風景畫,風俗畫,風情畫。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悲情色彩。[3]24這雖是一個過于歸整教條的總結,但它基本上是準確的。這似乎很難概括那種社會批評和問題解剖性的鄉土小說,還有那些反諷幽默的略帶荒誕的鄉土小說。如果僅討論鄉土語言用這個三畫四彩概括極少數小說倒可以,更多的小說我們必須找到融合點。例如說我們從句子中找到口語和方言在形式特征上融洽的程度,用詞和造句中的地方性美學趣味,現代性語言在鄉俗土語中如何構成新的風格特征,還有語言細部的表現功能如何極致地發揮。
二
我們首先來談以魯迅為核心的鄉土問題小說的語言。魯迅的小說幾乎全部是鄉土小說,包括《故事新編》也采用了地方性較強的描寫語言。從語言上看,魯迅的小說一方面是指向社會問題分析批判的,以一種尖銳潑辣、幽默反諷的語言方式,這類以《阿Q正傳》、《藥》、《祝福》為代表;另一面采用詩畫抒情方式,但卻有濃厚的懷舊與悲情意識,這類以《社戲》、《故鄉》為代表。總體上看,魯迅采用了一種主觀抒情語言,突出了對鄉土社會的反思,有一股熱血激情在語言的深部流淌運行,其語言是瘦勁尖銳、潑辣有力型的。
從年代來看,魯迅的語言是20世紀20年代最初幾年里發生的。這時候,葉圣陶、冰心、郁達夫、廢名、許欽文、高世華、潘訓、王統照、許地山、廬隱等人都有小說問世。從舊時的信息傳遞緩慢來看,很難說他們這時所寫的鄉土小說互相有什么語言上的影響,應該是各自創造其鄉土語言的特色。
急迫的櫓聲起在右面的河面,使我一切思考都暫停,直奔對面的水埠,跨下石級,站定在齊海面的一級上。向右望去,黑影似的一條船,依稀可以辨認了。斜方體的燈光從船側窗框子里射出來,映在水里,給一枝櫓攪得蓮花似地零亂。河水動蕩的聲音,合一種短促的警示;櫓偶然觸著河底的石頭,發出重濁聲……一會兒,船身模糊了,不可辨了;燈光微弱了,沒有了;櫓聲呢,先是漸漸地輕微,終于聽不見了。
——葉圣陶《恐怖的夜》(1921年1月)
葉圣陶從視覺和聽覺兩個方面描繪鄉村河流上的行船,在這里鄉村風景便是鄉土語言,每個分句都從視覺再到聲音,從長句再到短句,使長短成為一種句子節奏。葉圣陶的用語習慣以短句見長,句子與句子緊湊連接,有一種口語的韻調。鄉土語言貼近鄉民土地的事情而寫,《曉行》是鄉土語言的典型,河水、泥土、水車、農舍、池塘、農具、秧田這些農事都充滿了深情,鄉人把這種田里種的東西視為生命,“就好比我們的性命更為堅固而長久”。把鄉土視為生命和生命成長,這正是鄉土語言的核心所在。
一個黃而瘦弱,目眶下陷,蓬著頭發的小孩子……忍著饑餓,去聽鳥朋友與水邊的蛙的言語。時而去聽聽葦中的風聲,所響出的自然的音樂。但是父親是個伺候偷吸鴉片的小伙役。母親呢,且是后母;是為了生活,去做最苦不過的出賣肉體的事。惟有星光送他到家中去。明日呵,又是同樣的一天!
——王統照《湖畔兒語》(1922年8月)
王統照采用直接用口語述說人物,口語的描寫,凸現客觀人物肖像時,卻表現作者的主觀抒情。把客觀描寫與直接抒情性語言結合起來,這是一種不同于魯迅、葉圣陶的語言方式。王統照的這種語言方式在《沉船》里發揮得極明確,往往在人物描寫和抒情描寫之后都有這樣的直接抒情語言。只是這種抒情有時是作者語言,有時是人物議論語言。
上述是于20年代初的兩三年之中做的鄉土語言的抽樣,他們的鄉土語言是不可以相互替代的,這標明了個人風格。于是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鄉土語言是每一個作家自己的心靈與生命的言說。中國鄉土小說也許有流派,可鄉土語言卻不可派別化。我們現在可以討論一下鄉土語言發生的一些特質與表現形式。
第一,可以從鄉村地理學斷言鄉村語言是鄉土地理特征的復現與模仿,因而有寫實性,這種寫實與作家的鄉土概念有關,魯迅、葉圣陶、許欽文、王統照、彭家煌、葉紫、廢名、沈從文均寫的是家鄉土地上發生的故事與人物。雖然可以創造一個未莊、史家莊、魯鎮,但家鄉的地理特征如行船、馬車、宗廟、村寨等山川地理,一定都可以和親歷暗合。這種寫實性會帶來如下特點:地方風俗的精細描寫,地方人情、血緣、鄉鄰都具有宗法性質的聯系,故鄉的現實性引起的反思與批判,因而形成社會問題的探討。因此,文本的語言必定符合地方性常識與風俗特征,也必然引入作者從童年起學會的方言土語及地方性思維習慣。這種語言在鄉土小說中會占絕對優勢的位置,其后百年小說發展也證明寫實性、描寫性的鄉土語言為鄉土小說的主流。
第二,鄉土語言蘊含著一個關于鄉土的人性、人生、人情的認知結構。鄉土語言是鄉土小說的一個痕跡,是一種地方性思維與記憶,但鄉土語言也影響地方性的人文風情,它構成鄉土文化的主要方面。任何鄉土語言都會灌注豐沛的鄉村經驗與生命意識,但并不是我們依葫蘆畫瓢就會有這種鄉村語言的文學性。中國有大量的鄉土小說是非文學性的,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訴說。這里涉及到審美現代性與價值估評問題。文學語言應該是這樣一種語言——語言成為“審美對象自身具有一定的價值,不為任何功利目的所奴役”。[4]26我們應該盡量開掘鄉土語言中豐富生動的表現力,鄉土語言中既明朗又暗示地帶有農民生存特點的語言效果。我們既有了鄉土語言的美學特征,又有了評估鄉土語言的各種標準,以此來檢索百年鄉土小說,從而給出一個正確評價,這應該不困難。但鄉土語言現象卻是多變而復雜的,多種派別、多種語言現象交織在一起。就魯迅而言,他既有鄉村問題小說的語言,也有鄉土抒情懷舊的語言,還有社會心理的、意識形態的語言。
我們大致可把自魯迅起的一批鄉土文學作家歸為一類,他們是葉圣陶、王統照、許地山、魯彥、許杰、許欽文、臺靜農、彭家煌、蹇先艾、葉紫。他們關注的是農村草民的生存問題,各自展開自己家鄉生活的嚴酷面貌,他們僅在鄉土材料上保持著一致性,語言還是發揮了各自的風格特點。魯彥的語言情緒豐沛熱烈,對事物、對人物模仿性地帶了個人主觀色彩的評判,他的觀念與情緒是融合的。我們看到的鄉土是他評判過了的鄉村土語。葉圣陶的語言精致,長短之間是選擇后的搭配,語言講究韻味,在陳述事物與人的過程中,力圖描繪客觀性,而主觀意念暗藏其中,哀婉略有反諷。許地山的早期鄉土語言里注重色彩、事物、器具的變化,句子有畫感,是一種豐富多彩的語言;后期沉淀下來,更多的是客觀陳述,細膩地表現語境中的情狀,把觀念含在事物之中。許杰的語言描繪性能很強,語言很出氛圍,善于鋪墊,往往把環境、人物、事件、心理交織起來,他和周文一樣很能渲染,使語言文字很出情緒與感覺,絕不會孤孤單單地使用觀念語言。王統照的語言長于風光描寫,寫出事物細致而微妙的變化,因而抒情性、風俗性強。當然,他也直接說出觀念,造成抒情直露的毛病。相比較,他喜歡用長句鋪墊,他的長篇更是如此,后期語言傾向復雜化,兼有象征隱喻、意象和心理分析等,早期語言地方性強,后期反而削弱了。臺靜農的語言貼近場景,人物均是鄉村對話,且凸現事物細部,而這些細部又是整體的有機部分,這樣有一種樸實親切的風格,容易產生地域風俗的意境,有濃濃的氛圍感。有些描寫句子是清靈的,但整體的情感狀態是凝重的。蹇先艾和師陀都是用鄉土語言復活鄉土生活本身,有一些像觀察日記,他以一個外來者的身份反觀自己的鄉土,力圖把鄉土的表象摹仿出來,倒也是本鄉本土的生活,似乎和故鄉的本質稍隔膜了一些,使那些生活表相掩蓋了鄉土人性更內在的真實。
上述作家都用鄉村土語寫作,也都是口語的散文化表述,從總體特征來說,他們都是用語言把故鄉的一切畫出來,畫成風景畫、風俗畫、風情畫。把他們歸于鄉土寫實派沒什么異議,因而從創作方法來看也是一樣的,由于創作的基礎理論是摹仿論,他們沒有完全相異的特征,所謂語言風格僅僅表現在他們的個性上,而且這種個性也只是細微的差別。許多東西在表層上是無法分辨的,只有細細地深入到內部,深入到句式,深入到語言組織的細節上,我們才能發現個人獨特的語言風貌,我們幾乎不能給他們貼什么語言標簽,只能是描寫性地揭示其語言特點。
三
鄉土小說的另一支脈是以廢名、沈從文、蕭乾、凌叔華、汪曾祺等人為代表,這類鄉土小說家有一種總體的風格。首先,他們有著鄉村田園牧歌式的溫情敦厚、恬淡雋永。其次,他們采用散淡活潑的口語,明麗清悠的話語特征,在用詞造句時既典雅精致,又古樸簡約,多用地方口語,又改造成文人氣,其句子短、跳躍,但又充分地復沓重疊產生回環之感。最后是他們把思想觀念隱含在文本之中,從不直接進行政治觀點的議論,讓現代性思想轉換為審美理想和情趣,往往體現為天人地三者合一的融洽思想。這些看起來統一的特征,具體到作者本人體現出來的風格語言也極為不同。例如,我們覺得廢名與沈從文的語言風格是一致的,但具體語言使用中又是極不一樣的。
抱村的小河,下游通到縣境內僅有的湖澤;濱湖的居民,逢著冬季水淺的時候,把長在湖底的水草,用竹篙卷起,堆在陸地上面……賣給上鄉人做肥料……這湖同麻一般長,好像扯細了的棕櫚樹葉子,我們拾了起來,系在線上,便用剪刀修成唱戲的胡子。這工作只有柚子做得頂好……
——廢名《柚子》(1923年4月)
廢名用口語散文的筆調描畫出鄉村牧歌式的圖景。鄉村事物中的童心玩鬧,獨顯的寧靜自然、悠遠韻致,這是一種恬淡詩意的追求。這種淡遠悠悠的炊煙,婀娜垂垂的柳葉在《竹林的故事》、《河上柳》、《凌蕩》等篇什中發揮到了極至,甚至把古典詩詞中的句子也化入他的詩畫描寫之中,直接有了“東方朔日暖”“柳下惠風和”的句子,還有“太陽正射屋頂,水上柳陰,隨波蕩漾。他在古典詩詞句子中嵌鑲入描寫狀態。廢名在鄉村自然的散淡中又插入一些古典遺韻和風雅,顯示了他鄉土語言的精致凝縮,他的語言確實淡遠了,幽雅了,可用詞與句型含有一些仿古,有一些像王維寫田園詩一樣,有些歸禪歸佛,皈依田園牧歌的生活。
廢名的語言簡略,沈從文的語言復沓;廢名的是說的風景畫,沈從文的是繪的風景畫;廢名的是凝練的意象,沈從文的是回環之美的意境。廢名精致的短散文,沒有故事與人物性格和命運,沈從文口語的散文筆法,人物在環境和時間長度里顯示出來,有一種沖淡的故事,也就是說人物是在情節邏輯上運動。沈從文的是風俗故事,廢名的是風俗情緒。沈從文特定的湘西地域和地方的語音語調,具有不可替代性。廢名的地域是南方,長江之南的風習,既便有一村一院仍是一種南方的共性,他的史家莊共存于南方的風物之中。
在京派小說中,蕭乾和凌叔華都出生于北京。蕭乾的鄉土話語制造的下層人群有很多想象的色彩,但他的語言精致,描景狀物又肯下功夫,從孩子視角寫鄉村情狀,即采用動物貓咪觸須探索事物的方法去觸動景物與孩子,細膩到氣息與毛發的顫動。凌叔華的鄉村景色是描寫性的,一句一句地鋪上去,從容不迫,她更下力的是寫這些人物可感可觸的細碎之事與心理。她的筆法婉委細密,有濃厚的情調特色。她表現母愛與人情,并不與政治思考糾結,而是人性的一種探索與生命意志的本能表現。
汪曾祺是沈從文的學生,從風格上更與沈從文接近。但汪有一些類如小品文的話本筆記體小說,還有一些現代派技巧的作品,汪曾祺的主要代表作仍是從沈從文一脈相承來的,如《受戒》,《大淖記事》,《雞鴨名家》等。汪曾祺愛在用詞造句時采用復沓手段,選擇疊音詞,在節奏感非常鮮明的環境描寫中,把風景畫與風俗畫融為一體。這一格調骨子里是獨得了沈從文的風韻。在這一點上,汪曾祺同何立偉一樣,把小說當作詩詞來寫,使小說的句子節拍化。沈從文后面的作家也努力將口語白話散文化,在口誦之中有輕緩抒情的節拍,或者口語的腔調,口語中鄉村方言俚語,口語的情狀與態度,簡言之,努力把鄉言土語說出詩化韻味來,這方面有獨特神韻的恐怕還只有汪曾祺與何立偉。
我們現在可以總結一下詩化鄉土語言發生的一些特質與表現形式。
鄉土是一個與大地、棲居、生命氣息、人情相諧的地方,每一個人有一方自己的水土、自己的天空,也就有了“棲居之詩意因素”。鄉人的農牧神在天空、在大地、在他活動的陽光雨露之中,鄉人因此而構筑神性的形象。這種形象是鄉土情節的形象,是詩意的形象,它必定“是別出一格的想像,不是單純的幻想和幻覺,而是構成形象。”[5]199如何真正理解形象呢?海德格爾說:“形象的本質乃是:讓人看物。”“真正的形象作為一種景象讓人看又不可見者,并因而使不可見者進入某個它所疏異的東西之中而構形。”[5]211海德格爾的精彩之處告訴你詩意的形象并不在一樹一村、一條河、一座山,因為這是一些具象的事物,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著。這些事物居于故鄉,它僅在于喚起你的想像,勾起你的情感,你用這一切而不拘形象,一種郁結而成的鄉戀形象,至于它是什么?均在每個人的心靈之中。因而現象一詞是在構成之中的象,構成的形象才表達出濃厚的詩意。可詩意在人與事物之間構成,然后語言才能意識。這時的鄉土語言是表現性的,是抒情意味的一種幻象之物。
鄉土語言的詩性不僅如此,它還是審美本體論的。“德國人為詩性推出一種定義,我們可以把詩性理解為產生美感的東西以及來自審美滿足的印象。”[6]392詩性也是一種行為,一種想像行為與語言行為。它提供給你的詩意是隱秘的、真實的、思想的,當然也是情感的,因而詩意避免直說,那會大煞風景,所以要采用暗示與象征的辦法。“詩的個性程度,地方色彩,現實性和獨特性愈強,便愈接近詩的核心。”[7]392鄉土語言最是這種詩性語言,為什么呢?鄉村首先應成為一個人的精神象征,但對故鄉的情懷愈是采用暗示隱喻便愈是有力量。“一切表達物體和抽象心靈的隱喻,都起源于村俗語言。”[8]200這也揭示了一個重大的語言秘密,我們所擁有的語言正好都來源于這鄉言土語。文本的所有詩性都是通過語言組織出來的,詩意不僅通過語言材料并且在語言組織過程中激發想像,在讀者看來,實現審美的功能仍是語言帶來的效果。審美語言一定會采用超常規的表意手段,這樣能指一定會過度膨脹與超重,當然像魯迅、廢名又采用減法,使能指更精彩凝煉,但目的是一樣的。這種多語或少語均以表達符碼自身的特質為重心組成詩性結構。于是,同樣的符號,處理方式不同,效果就不一樣。廢名與沈從文都是鄉土小說作家,可他們的鄉土語言區別卻很大,廢名用減法,沈從文卻是用加法。他們在兩個極端點上反常規地使用鄉土語言,因此我們可以判斷何立偉更接近廢名,而汪曾祺更接近沈從文。我們對鄉土語言的分類,更應分析文本中使語言偏移的技術手段,因為“布拉格學派肯定道,詩性言語通過打亂話語表現程序,在語言體系中發揮著突出作用。”[6]557要注意一點,要使鄉土語言充滿詩性表達,要緊靠符號語言的審美功能,重在語言的能指因素。而不是突出語義上的思想力度,這樣鄉土語言就會意識形態化。
對語言的這兩個方面的強化方式不同,觀念不同,導致了鄉土語言指向兩個方向:一是鄉土問題小說,一是鄉土詩化小說。百年鄉土小說的發展一直存在著這兩個維度的演進。鄉土語言的這兩個起點的風格派別特別重要,接下來數十年的鄉土小說都可以說是在他們之后類化出的。
四
從20世紀30年代起鄉土小說基本走上了一條向左傾向的線路,核心特征便是加進去了革命的元素。大量的意識形態話語涌入鄉土小說,這以后半個世紀的鄉土語言應該說是受一種觀念的支配,它們的脈絡大致可以這樣分出來。
一路是革命加戀愛的鄉土小說,社會剖析的鄉土小說,流亡的鄉土作家小說,七月派鄉土小說。這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以蔣光慈、陽翰笙、柔石、葉紫、丁玲、茅盾、吳組湘、沙汀、艾英、蕭紅、蕭軍、端木蕻良、駱賓基、舒群、羅烽、白朗、李輝英、路翎、丘東平、彭柏山、冀汸、曹白等人為代表。其鄉土語言被觀念化,他們寫鄉土中發生的事件、人物與環境,都是以革命、階級、社會為準則使用地方語言,因而他們的鄉土語言含有憤發式的革命激情,這也是一種烏托邦式的浪漫情懷。這四個派別分別有四種語調:第一種是激情性的。第二種是冷峻客觀的嚴厲批判。第三種是典型的懷戀鄉土,反觀追憶型的,悲愴凄涼的情緒中又包含著緬懷思念。第四種是表相與內心重疊的,混亂的現實社會特征與復雜變化的內心。因而,可以說它們屬于體驗型的鄉土小說。
另一路數是解放區的鄉土小說。一方是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山藥蛋派”,作者有馬烽、西戎、束為、孫謙、胡正等;一方是以孫犁為代表的“荷花淀派”,作者有劉紹棠、從維熙等人。此外還有不太好劃分派別的鄉土作家,如師陀和李劼人。
這是一個龐大的作家隊伍,表明了中國鄉土小說的發達,如何看待這批小說的價值與成就,也許今天還無法特別準確的評估,甚至連他們的成功與否都有待于我們重新去鑒定。從語言的角度值得注意的大概有如下一些作家和作品。
1.吳組湘。吳組湘的鄉村語言是客觀的,擅長描寫和鋪排,在家鄉口語中帶入一些方言。人物在環境里自然地活動,如實地畫出當時鄉村的實際狀況,作者本人不插入評論,讓觀點和傾向從人物與場景中流露出來。他的景物描寫使用長句,而且極注意層次,對話是純口語的,鄉俗落實在祠堂、儀禮、各種器物的名稱狀態中,是鄉里人看鄉土中的人與事件。
2.沙汀。沙汀的鄉土小說是典型的“川味”,四川人說話的幽默風趣在他的口語中有許多表現。俚語和普通話的調式不同,他的鄉土小說是本鄉本土的人物在對話、獨白,在場景中風俗性和人物的性格、語氣、韻調是融合在一起的,所以他絕不會用長句鋪張景物,他用語言說人、說事、說風俗,就算偶有描寫也轉化為風俗語言的說話。《淘金記》便是一種典型的鄉言土語。
3.艾蕪。艾蕪的語言主要的功力在描寫和詩意上,他主要是采用視覺觀察,色彩與情狀是形象生動的,然后才是納入聽覺、幻覺、感覺、味覺等五官感受的多種方式。他在南行的途中多呈現為一種異域風情,雖然有一種人文情懷貫注于語言之中,有著沉重的哀愁,但他的語言依然是表相的鋪陳,沒有扎根到人們的心靈與思想之中去,在風景與風俗人情中沒有融入當地人于大地血脈之中的生存方式。
4.蕭紅。蕭紅的風俗畫無疑是一種田園牧歌式的,家鄉風土的一切習俗構成了她對《呼蘭河》的言說方式。她的語言不能算是環境中人物的口語,而是經過她提煉了的一種描寫性的口語,句子異常短小,更多的分句是詞組性的,這使得她的語言有一種清靈的跳動感覺。她筆下的風俗浮在人群與事件之上,語言流動之中有一種歡快的浮嵐霧氣。
5.路翎。路翎的語言貢獻是把外部的描寫性語言轉化為內在的心理活動,把人物內心表現得細膩復雜,尤其重視行為過程中的心理變化,還善于抓住人物表情的復雜變化。某種意義上,路翎的心理描寫也采用了心理辯證法。當然,他也有直接表露思想觀念的議論,使之文風直白。
趙樹理和孫犁的鄉土語言走了兩個方向:一個是民俗大眾化的,一個是風景優雅浪漫化的。其實這兩種語言都是理想主義的。趙樹理想讓所有底層人群都能文學化,把草民情狀質樸地轉化為小說。孫犁卻把艱難困苦的現實風光化,追求自然美人性美風俗美。因此趙樹理的語言就是農民語言,包括俚語、俗話、民謠、歇后語等。農民語言與生活情狀絕對民間氣息化,直接展示鄉土生活的婚喪嫁娶、村居習慣、飲食節日心理,是那種地地道道的風俗畫,甚至大量采用民間文藝的方式,即板話評書的言說樣式。何謂語言的民間形式,趙樹理應該是一個典范,至于怎樣評價他作品里的革命觀念和意識形態,則是另一個問題了。孫犁的語言其實是追蹤廢名和沈從文的,讓鄉土語言雅化。他用細部描寫表現心靈與情感的細膩,語言細小的特征在人物對話中,他們的心靈與情致都是流動變化的。而敘述語言的主體則是作者的一種審美提煉,清新俊逸,淡泊明志,這與他的鄉土審美觀互為表里。他的鄉土語言里沒有粗俗蠻野的東西。這兩個人在北方各自有影響的傳人,就如沈從文的語言在南方一樣。在后繼者那兒,柳青、浩然、高曉聲走了趙樹理這條線索;劉紹棠、葉蔚林走的是孫犁的這條線索。貴州有兩個作家——何士學和李寬定,何士光是承趙樹理風格的,李寬定是承孫犁風格的。這僅僅是一些最粗淺的鄉土語言風格發展的脈絡,而他們之間是否真有其師承關系則又另當別論,但風格上的一致性是肯定的了。
五
當代鄉土小說呈現多元化,其鄉土思想內容的發展未必有多大的實績,但鄉土語言的表述卻是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鄉土小說,自問題小說、社會剖析小說、革命小說起,一直被政治觀念左右著,在當代也不例外。農村道路的小說、知青下鄉的小說、尋鄉土之根的小說、新寫實的小說、先鋒鄉土的小說,它們對土地、農民、鄉居、民俗、民間文化的表現,也沒超過他們的前輩。鄉村的各種因素處于被消解中,這對鄉土文學是一個巨大的打擊。但我國的鄉土小說產量卻仍然巨大,也許它們只是客觀模仿了鄉村的現實。在這些小說里,對鄉土有毀滅性的因素,如土地、環境、水資源、生態循環、農民地位和心理等均沒有創造性地表現出來。
知青鄉土我們可以找到梁曉聲、葉辛、王安憶、史鐵生、張承志、朱曉平、李銳、鄭義、孔捷生、阿城、陸天明等人。鄉土文化派有韓少功、李杭青、阿城、賈平凹、鄭萬隆、阿來、陳應松、林斤瀾、莫言等。新寫實的鄉土派有劉恒、劉震云、遲子建、楊爭光、李佩甫、張煒、畢飛宇、董立勃等。新生代鄉土派有須蘭、石舒清、紅柯、鬼子、東西、孫惠芬等。先鋒鄉土小說派有馬原、洪峰、呂新、蘇童、格非等。當然這是一個十分不完備的名單。要全面論述其語言又是另一部大論著,我們抽其有代表性的新鄉土語言來談。
張承志的語言里常有一股不可遏制的浪漫主義激情。一切自然皆著我主觀之色,其色彩、聲音、形體、感觸與味覺都被強烈的情緒籠罩著、牽動著。他的景物描寫,用了大量比喻、夸張、象征的手法。他對各種自然景物和場面都充滿了感覺體驗,往往是一連串的描寫長句,有很多象聲詞和各種色彩,形容詞也是重量級的,長句的綿延感和重復非常明顯,因而他的文本語言是過度使用的,總是膨脹的,有一種語言流動的相互覆蓋現象。這種放縱的語言也帶來了能指的超量,使所指簡單抽象。文本有大量的句子,但句型變化卻少,他的風景和風俗都是主觀描寫出來的,不是草原文化特點顯現出來的。雖然有其象征特色,而內涵卻缺少深厚沉穩。
莫言從語言本質上走的同張承志是一路,同樣被一種浪漫主義激情所控制,所不同的是莫言帶來的是一種負審美,表現鄉土中一些扭曲丑陋的、讓人恐怖惡心的事物。他的描寫句,少則數十,多則數百字,有時甚至上千字,一個句子一個意象從能指上無限夸大地延長,甚至在句群和語段內并置各種復合的意象,超量地使用比喻和夸張,每個單獨的描寫句都有繁殖能力,或者靜態地一句套一句地拉長,或者動態地使行為和聲音保持一種空中滑翔狀態,句子成了紡線不斷地抽出、拉長、循環、束結。他的語言流風景與風俗一反雅化,而是粗鄙化、原始化、欲望化,雖然在句子中保持了對話和獨白,但他的語言卻是不能上口念的,那是一種扯不斷的綿延。他讓語言有一種狂歡的表演,我們可以視之為一種暴力的感覺語言。
韓少功用的是一套冷靜邏輯的分析語言。他愛在詞語和句子中分析出語言在民俗傳說中的出處,類似于語言考古,他刻意尋找古汨羅江為代表的湘北語言源頭及其演變的歷史,把村俗俚語、民謠民歌放入一個具體的語境,揭示出不同時代和不同人群對語言使用所產生的意味。這是一種真正的語言自覺行為,讓小說回到語言自身,回到語言存在的一種生活方式。這里的鄉土語言既是作者的又是馬橋人物的,使用口語、俗語、土語交流,是一種典型的說語言。使語言成為小說實驗的自覺行為,真正體現了為語言而寫作。從中國小說語言發展而言,這是一個典型的范本。但也因為過于理性地分析語言,將語言其他的表現因素泯滅了,如語言的詩性、畫意,語言的風俗性是融入人群交流里有血有肉的個性痕跡,這里只有語言的情狀,而情緒與韻調的感染力便消失了。
賈平凹的語言似乎來源于兩個系統,他從趙樹理、柳青一派習來地方語言,直接把商州語言進入文本,俗語、俚語、諺語都整合在地域文化的表述之中,所有人物語言都通過篩子過濾了,而成為適合自己口語言說的方式,作者也運用本鄉本土的語言,這二者的融合度極高,幾乎不露痕跡。另一方面,他又從廢名、沈從文的方向吸取營養,所不同的是他吸取的是煉字造句的一種規范型方法,把所有句子都裁劃得整齊,然后又加進去白話及筆記體的說話方式,從從容容地說書,這使得賈平凹的語言特別流暢樸實,俊雅中兼有清朗平白。他的口語有一個隱含的敘述者,在整合人物與敘事者的語言,用一種娓娓道來的言說方式,這種言說籠罩文本,包括說風景、人物、事件、場景、風俗等,一切描寫與敘事都是說出的,因而與所有當代作家相比,他的語言最具話本的性質。
劉恒有一個語言流,無論鄉村還是城市,他都用北京土話去帶動,在這種語流中,他的語詞復沓、循環,如同一個漩渦不停地轉動帶著人物、事件往前涌動,他的對話可以是短句,但必須倒騰幾次,在前一句固定了語義之后,又極不放心地補一句二句,甚至連風景也是如此,人物肖像動態也是如此。這一點與老舍相似。劉恒的語調是連綿流動的,但還有一種以不斷結扣解扣的方式在演進,用北京話說就是“掰扯”,作者和人物掰扯,人物和人物掰扯,在掰扯過程中語言打磨得非常光滑,游走而流動,詞語加句子多得相互擁擠,但它們能在一個慣性和語流里行走,也許就是這樣的方式構成北京作家王蒙、王朔等的話癆。這種話癆構成了劉恒小說語言的日常生活之流,生活和語言同質。
我們剖析了五位有代表性的小說家的語言。第一,這種明顯有個人特征的語言是典型的人工語言,經過作者的主觀刻意發散出來的語言。第二,它是一種表現的語言,雖然他們在文本里盡量再現某種客觀性,但他們的語言卻是一種表現方式,就是每個人的語言均在表現他自身的創作個性。第三,他們的小說讓語言超過了它所表達的事物,從語言特征去分析,是語言看人群,看事物,看我們的鄉村,這里分別只能是張承志的草原,莫言的高密鄉,賈平凹的商州,韓少功的馬橋,劉恒的洪水峪。而最真實的客觀的鄉村土地我們是見不到的。第四,傳統的鄉土小說語言基本是模仿寫實性的,其語言功能是一種工具,一種媒介,語言自身的審美特征是看不見的,因此我們很難說傳統鄉土小說的語言有何種貢獻,因為語言的特征是鄉土自身的特征,我們最多能探詢到語言對事物和人的高度仿真能量。我們所言的語言準確、生動、形象,其實是事物和人自身形象性的表現,世界萬物自身具有這樣的表現性。
另一方面,新時期以來鄉土語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語言自身有其本體,有其現象。直白地說,鄉土語言在作家那兒成為一種語言表演,充分發揮了語言自身的魅力。傳統鄉土語言作為表現工具時,其功能是單一的,并不能發揮語言的多姿多彩性。每一個敘述者的個性和語言的特征相加時會產生拓撲學的變化,這就帶來先鋒小說家的語言試驗。我們將在另外章節專門討論先鋒小說帶來的新鄉土小說語言上新的可能性。
六
整個鄉土語言的發展狀態基本可描述為如下類型:一類是模仿的,又稱客觀的,是寫實性的,這是一種傳統的鄉土語言。二類是表現的,又稱主觀的,是理想情感性的,它有傳統鄉土語言的根基,例如廢名、沈從文、汪曾祺、何立偉等。但新時期以后,新鄉土語言呈現出異常主觀的表現型質地,如莫言、韓少功、張承志、劉恒、賈平凹等。三類是符號的,又稱為形式主義的,冷漠非情感化的。文本整體是象征化的,這基本指寫先鋒鄉土小說的呂新、格非、林白、韓東、行者等。筆者本人的碑基鎮、魚巷子系列小說也屬此類。近十年來的中國鄉土語言問題涉及面廣,類別復雜,無法一下談透。這涉及一些大問題,今后還有沒有鄉土地域性寫作?大眾語境下我們創作的民族性、民間立場應該是什么?鄉土語言基本屬于農業社會,如果社會高度工業化信息化了,我們如何重返鄉土社會語境?中國人的審美感受會出現什么局面?那可能是現代人真正丟失了靈魂的棲息地。
我們不能犧牲鄉土社會文化,以完成一個新都市化的大眾通俗文化。因為,地域概念是一個沒法取消的東西;文化特別是作為人與地方本性的文化,不可以被取消。文化特性是這樣一種東西,它是“代代相傳的固定不變的事物,又可以把它看作是區域性的事物——在這里,文化空間逐漸受到種族和民族觀點的影響,形成了一個強有力的‘血與土’聯合體。”[8]205民族國家的概念直接受到它的支撐,它是一種文化動力以此構成文化——區域——民族——國家的一個邏輯循環,有領土便會有鄉土,只有城市的國家很可能是一個孤島。沒有鄉土,不可能產生偉大的作品和偉大的作家。這里可能有更深層的原因,是語言發生學的原因,是什么決定了鄉土語言的發生和類型呢?一方面是地理、環境和種族,也包括特定的水土條件。另一方面是個人氣質的,它關系的是血緣、遺傳、情感、習得、審美、認知的思維方式,簡單地說,是一個人的素質和他的地理環境決定了鄉土語言的特征。在山地沙漠的人和在湖泊河流上的人,使用的語言和語言特征肯定是不一樣的。其實,知識也是由地方性決定的,人的知識和語言就像稻谷、玉米、麥子一樣從特定的土壤里長出來,不一樣的水土,糧食所含的元素也就不一樣,語言便是一個人的精神食糧。我們可以斷定每一種鄉土語言都是特定的地方長出來的,這既包括地方的物質痕跡,也包括地方的精神痕跡。無疑,鄉土小說也是地方上長出來的,從其根基來判斷,我們又大可不必擔心鄉土小說會從此滅絕了,因為地方性是不可以絕滅的。假定有一個樓蘭和亞特蘭斯蒂的地方消失了,但另一種地方又會出現的。
[1]戴維·洛奇.二十世紀文學評論[M].趙少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2]艾布拉姆斯.歐美文學學術詞典[M].朱金鵬,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3]丁帆.中國鄉土小說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4]馬克·昂熱諾.問題與觀點[M].史忠義,譯.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
[5]海德格爾.講演與論文集[M].孫周興,譯.北京:三聯書店,2005.
[6]讓·貝西埃.詩學史[M].史忠義,譯.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
[7]維科.新科學[M].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
[8]邁克·克朗.文化地理學[M].楊淑華,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