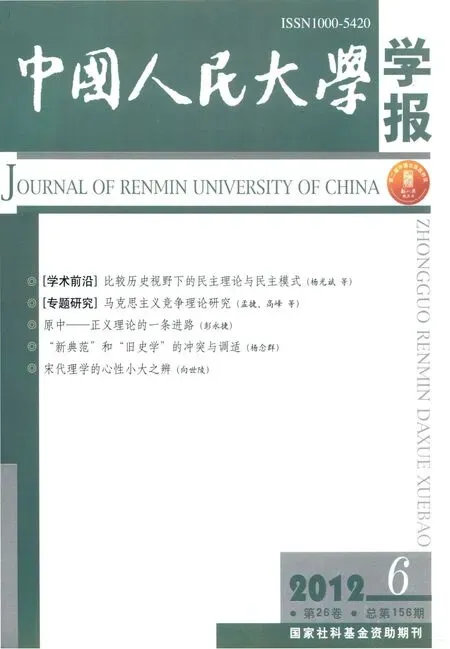俸米商業化與旗人身份的錯位:兼論商人與京城旗人的經濟關系
劉鳳云
在我國古代社會,俸米是由國家以實物形式發給統治階級的俸祿。清朝享有俸米者除貴族、官僚外,便是被編入八旗的滿蒙漢軍,他們被統稱為 “旗人”。這些俸米是通過運河以漕糧的方式被運送到京城后再發放到個人手中的,而京城不僅是貴族、官僚集中的城市,更是八旗旗人的聚居之地。本文將對運到京城的漕糧在變成旗人俸米之后的流通過程進行考察,探討旗人俸米如何從旗人手中到了商人手中、如何從其生活必需的食物變成經濟流通中的媒介、它在旗人生計中產生過怎樣的作用、對旗人社會又產生了哪些影響以及國家采取的措施等等。
一、旗人、俸米、商人:三者之間的經濟鏈
清朝視八旗為國基,自入關后,以優厚的俸祿作為八旗不農不工不商的保證,八旗自王公貴族至披甲兵丁例有俸米。諸如八旗兵餉,“京師前鋒、親軍、護軍、領催、弓匠長月給餉銀四兩,驍騎、銅匠、弓匠月給銀三兩,皆歲支米四十八斛,步軍領催月給餉銀二兩,步軍一兩五錢,鐵匠一兩至四兩,皆歲支米二十四斛,炮手月給銀二兩,歲支米三十六斛”。[1]在清朝每年運往京城的四百萬石漕糧中[2],八旗俸米的支給當是一個不小的數目,而對于個人而言,清廷規定的俸米額度也是豐腴的。所謂 “我朝自開國以來,額設八旗甲兵,按月支給銀米兩項,原使各兵丁關支銀兩可以制備衣甲,給領米石足以養贍身家,立法至為周備”。[3]
為了保證旗人的支領方便,俸米的發放之地分為兩處,一處在通州的中倉、西倉,另一處在京城的十一個糧倉。分倉的原則是按照官員的品級及爵位,貴族及高級官員在通州支領,下級官員及甲兵等在京城支取。這是考慮并照顧到普通旗人的支取成本問題,使之得以免除腳費的花銷,就近支領。
在時間上原定一年發放兩次,“辦理春季俸米自二月起,秋季俸米自八月起,旗員限二個月,漢員限四十日,按限放完”。[4]“上三旗包衣應放米石各隨本旗放米月份開放,由戶部按照城內祿米、南新、舊太、海運、北新、富新、興平等七倉分派二旗,城外太平、萬安、裕豐、儲濟等四倉分派一旗,挨定倉口次序,于每月初一日預定三倉挨陳定厫座,令該三旗分往關支,一旗甲米統在一倉承領。”[5]對于如何支領也有規定:“各旗應領甲米令本旗都統、副都統先期核明所屬各佐領管領下應領米數人數,造冊咨送戶部札倉,轉行倉場,俟開倉之日,令每月所放三旗之都統,將該旗應領米石無論滿洲、蒙古、漢軍、包衣共分作十五起陸續關支,每起約領十余個佐領,管領之米仍每起更番派撥,賢能章京一員、領催四名,并應食米兵丁內挑派三四名,令其跟同赴倉領米,限一月內放完,限外不完,將監放之都統及查倉御史并該倉監督均予議處。”同時實施 “米票”制度,就是以佐領為單位,每一佐領發一米票,具體是由 “該旗都統出給本旗總領交押旗參領等先赴該倉換票,該倉于該旗總領到時,即按照各佐領官員數目每員各換給米票一張,仍交該參領等領回,發交各該佐領散給應領俸米官員,令其遵照定限自行赴倉關支,不得擅交鋪戶領賣”。[6]
不難看出,清朝從俸米的額度到發放程序與方法,都是以對旗人最優為準則。但正是這優裕的制度給旗人帶來了潛在的隱患,這就是八旗俸米例有盈余。康熙時,“八旗兵丁每人所得四十斛之米,人口多者適足養贍,人口少者食之不盡必至售賣”。[7]大體上, “每放米之時,倉內所出官兵留食者約三四分,官局收買者約二三分,余俱在外流通。民間借以接濟。京師輦谷之下商民云集,每年所出倉粟不敷食用,尚賴各項雜糧添補”。所以,雖 “行戶囤積居奇實為民害,但官兵關領俸甲米石轉為售賣,亦勢所不免”。[8]
正是在八旗俸米 “常令充贏”的情況下,旗人為滿足城市生活不斷增加的日用開銷,往往將家中的多余米糧賣掉,以兌換銀兩。于是,一些買賣俸米的商人便應運而生。
這些經營米業的商人店鋪稱為 “米鋪”,又稱 “老米碓坊”。之所以有如此稱謂,是因為這種祿米是自南方經漕運而來,存在倉內,陳陳相因,所謂 “北京倉所貯之米,年深日久,其色紅暗,稱為老米”。[9](P245)最先發放的都是年深的老米。“厫座次序以所儲之米新陳為定,每月應放三色米石”。“萬安東西兩倉開放米石,先盡年份最陳之米發放,如次倉陳米足敷開放,不許再開彼倉,致滋弊竇。如一倉陳米不敷,必須在彼倉找放,仍照挨陳之例辦理,不得越次支放。”[10]又因發放的老米須加工后方能食用,于是就出現了承攬老米加工的 “老米碓坊”和經營米業買賣的米商、米鋪,又稱 “鋪戶”。
最初經營米業的多為山西人,在郭松義對山西商人的研究中,就提到了不少的米商。他說:“檔案記錄的八家糧鋪和三家碾房便是證明。像祁縣人郝良立等四人合伙所開糧店,至少在乾隆前期業已存在,當時郝還與同縣人郭大另外開了一家糧店……有名叫德勝成的碾房開設于乾隆年間,另一家天復昌碾房則開于道光年間,老板都是祁縣人;再有石大所開碾房則為徐溝人。道光二十四年 (1844),太原會館立 ‘糧行公立碑’,應是晉商參與北京糧食貿易的又一明證。”[11](P3-10)但是,隨著山東人的插足,山西人便失去了對糧食業的掌控,以致山東幫排擠掉山西幫,在糧食業中占了優勢。時人李光庭記載曰:“碓房多山東登州人。”[12](P107)
據官方統計,乾隆初期,“內外城碓房不下千余所”。[13](P189)乾隆五十二年 (1787)五月,乾隆帝因京城內外米價昂貴,為禁止商人囤積,下令步軍統領衙門會同五城官員等嚴查各鋪戶,“此次查封米麥共六萬余石,鋪戶共有數百家”。[14]另有數據顯示,嘉慶十五年 (1810),在“西直門內自新街口起至西直門,共有米鋪三十二座。各鋪共存之米自千余石至數百石數十石不等。西直門外共有米鋪二十座,各鋪共存之米自百余石至數十石不等,其余俱系陸續開設之鋪”。[15](P185)而以東市地近通州漕運碼頭,官倉多,故鋪戶亦多。至清末,幾乎所有的老米碓房、米鋪商人都集中在崇文門內的米市大街,米商皆于每日清晨聚此交易。外城除阜成門、右安門外皆有糧食市,前三門更是各糧業商號的交易之所。這種狀況直至光緒庚子前一直沒有改變。[16](P100)
上述記載說明,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乾嘉時期,米業不僅已經成為京城實力可觀的一個行業,且已經具有相當的規模。乾隆末年,僅一次查封的米鋪就達數百家,到嘉慶朝,米鋪所貯之米可以是 “自千余石至數百石數十石不等”,而且仍有 “陸續開設之鋪”。那么,米鋪及老米碓房的發展歷程又是怎樣的呢?
米的買賣之所以能夠吸引眾多的商人,主要在于米鋪及老米碓坊等并非僅僅是一般平民的購米店鋪,而是因為他們主要是做旗人俸米的生意。這在前面已經提到。接下來要強調的是,商人看到了市場供需中存在著巨大的利潤。據記載: “每年開倉放米之時,鋪戶賈人紛紛囤積,俟價昂時糶賣。”[17]“向來八旗甲米,俱按四季支放。放完后,去下屆放米尚遠,鋪戶乘機囤積,米價漸昂。”[18]也就是說,商人利用旗人俸米尚有盈余時以賤價買入,囤積之后待高價賣出。而旗人在進入城市之后,由于城市生活對貨幣的需求以及享樂和奢侈的誘惑,“往往耽于口腹,餉銀一經入手,不為度日之計,輒先市酒肉以供醉飽,不旋踵而貲用業已告竭,又支領官米,隨即賤價售與鋪家。祇顧目前得錢使用,不肯稍為儲蓄,而家中食米,轉零星用貴價向鋪戶糴買,此皆失算之甚者”。[19]
清政府雖然嚴禁八旗官兵將領得的祿米出售給鋪戶,但卻不得不 “聽其自行售賣”。究其原因,除了普通旗人需要利用所支祿米去換取生活必需品外,對于八旗富戶而言,祿米的轉賣可以調劑糧食品種。由于 “京師貴人家以紫色米為尚,無肯食白粳者”,所以旗人寧可將新入倉的米 “賤價售之米肆,而別糴肆米以給用”。[20](P68)說到底,旗人出賣俸米主要是受城市生活的經濟需求所支配,旗人、俸米、商人三者之間結成的是一條城市社會的經濟鏈。而內外城的米鋪及碓房卻靠俸米發展起來,他們雖然是俸米的寄生物,但旗人靠米商兌換銀錢,米商又是旗人依賴的對象。這種情況早在康熙朝就已經出現。
據嘉慶帝稱,曾閱康熙實錄,獲悉自 “康熙年間,因八旗兵丁多有將所得甲米私自賣給奸民,囤積販賣,及至該兵丁等食米不足,則又仍向鋪戶用貴價購買,奸民等因得抬價居奇,大妨八旗生計”。[21]嘉慶帝看到的這一記載應該是實錄中的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康熙帝諭曰:“今見八旗忽于生計,習為奢侈。”“八旗官兵以所支之米不運至家,惟圖微利,一時即行變賣。及至此銀費去,米價又貴,勢必請將八月之米于六七月間給發,且求將來年之米于今年豫支矣。”“自是以后,務將所支之米力加節省,必用至支米之時,庶不墮富商囤米術中。”尋大臣等覆奏,“嗣后八旗支米之時,請撥人監管,務令到家,不使鬻賣,至兵丁先期典賣米石亦應禁止,從之”。[22]
這條記載表明,早在清軍入關不久即康熙年間,米商即與旗人之間圍繞著俸米形成了這種特殊的關系。米商賺錢的基本伎倆就是先以賤價買回八旗官兵的餉米,再趁其下季餉米尚未發放、旗人無米下鍋之時以高價賣出,從中賺取差價。如果僅從商人的贏利方式角度思考的話,似也無可厚非,因為雖有巧取但不存在豪奪,且對雙方而言都有利。所以,康熙年間發生的這種情況在雍正朝已處于政府的半準許狀態。
雍正元年 (1723)五月,給事中巴圖奏請將商人買米、兵丁賣米之處概行禁止。經八旗都統等會議,認為 “鋪戶賈人雖買米積貯,而米仍在京師,且居民俱仰給于倉米,若概不準賣,恐價值反致昂貴,所請應毋庸議。嗣后遇青黃不接之時,米價騰貴,請限定價值,以杜掯勒。至兵丁米石實有贏余者,聽其糶賣,儻不計足食,盡行出糶,令該管官責懲示警”。[23]這表明,清廷準許俸米買賣還有借商人買米囤積以調劑市價的用意。也就是說,對于經營米業甚至是倒賣俸米的鋪戶,清廷是許可的,這應該屬于旗人與商人的正常買賣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旗人與商人之間還會建立起朋友關系。如松筠日記有曰:道光九年 (1829)冬月十二日,“東面米鋪趙掌柜探望,告曰,方自山東原籍返回”。兩天后冬月十四日,松筠 “至集成居米店探望趙大哥 (趙掌柜),久坐返家”。[24](P33)
可以說,俸米的收購賣出將旗人與商人系于同一經濟鏈條上,商人的財力及資本通過這一鏈條滲透到旗人社會,對旗人的生計產生了影響。盡管最初他們對旗人的經濟滲透力是有限的,而且商人的財富及資本的積累要受到政府相關政策的制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經濟鏈條將他們之間聯系得越來越緊,并導致了部分旗人的貧困化。
二、旗人與商人:債務與債權關系
旗人與商人之間因俸米所形成的經濟關系,隨著時間的推移,由最初的經濟互助,因旗人向商人預支銀兩、寅吃卯糧,逐漸演變成債權與債務的關系,而這種情況自乾隆朝就已普遍存在。
乾隆四年 (1739)八月,清廷為禁止旗丁之余米落入鋪戶手中,乾隆帝令直隸總督孫嘉淦“速行市買糧艘余米,以裕倉儲”,即采取 “官買旗丁余米”的措施。但孫嘉淦奏稱,“旗丁余米利于賣與民間”,“糧船北上時,多有向熟識鋪戶豫支銀兩,約于回空交米者,亦當聽其自便。是以官買米石,不能多得”。[25]也就是說,在漕米進京之前,已有八旗兵丁先預先支取鋪戶商人的銀兩,許以漕船回空之余米抵完鋪戶墊付,與商人形成較為固定的以賒貸為形式的債權和債務關系。而對普通旗人而言,賒買食物、布匹的現象在嘉慶年間越來越多。有御史蔣云寬 “請禁市儈盤剝八旗兵丁一折”,嘉慶帝批復曰:“旗人賒買食物布匹,事所恒有,及關領錢糧之時,安能禁鋪戶人等不向索取。”[26]
如此看來,當時旗人與鋪戶之間的這種賒貸關系很是普遍,旗人先以賒欠受制于還債之約,繼而以債臺高筑被鋪戶索取。滿人松筠在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道光九年七月,“早,豐昌號來人,告以前滿九爺為葬伊父母,請余向豐昌號借一百千文,至今未還。余難以推脫,只得陪小氣”。[27](P163-164)此種旗人欠債不還或無力償還的現象到了晚清更是司空見慣了。光緒時人夏仁虎記載了一則故事,形象地講述了旗人與商人之間的債務與債權關系。
他說:“昔居內城,鄰人某滿世爵也,起居闊綽如府第制。一日,余家人偶至街頭老米鋪,俄一少年至,視之,即鄰家之所謂某大爺者。見鋪掌執禮若子侄,而鋪掌叱之儼然尊長,始以罵,繼以詰,少年側立謹受。俟威霽始囁嚅言:‘今日又有不得已之酬應,仍乞老叔拯之。’鋪掌罵曰:‘吾安有錢填若無底壑?’少年曰:‘秋俸不將至乎?’鋪掌冷笑說:‘秋俸乎?汝家一侯二佐,領世職俸,養育孤寡,錢糧算盡尚不酬所貰也?’少年窘欲泣,鋪掌徐撿松江票四兩擲予之曰:‘姑持去,知汝需演探母也。’市井惡棍指逛窯也。少年感謝持去。家人歸述之……然則碓房握滿人財權說誠可信。”[28](P98)這是一個有關旗人吃喝嫖賭以敗家業不得不向米商借貸的故事。類似的記載也出現在現代作家老舍的書中。老舍記述其幼年時的經歷說:“在太平天國、英法聯軍、甲午海戰等等風波之后,不但高鼻子的洋人越來越狂妄,看不起皇帝與旗兵,連油鹽店的山東人和錢鋪的山西人也對旗籍主顧們越來越不客氣了,他們竟敢瞪著包子大的眼睛挖苦、笑罵吃了東西不還錢的旗人,而且威脅從此不再記賬,連塊凍豆腐都須現錢交易。”[29](P318)
然而,旗人生計的窘迫并非完全是商人所為,由于俸米在買賣過程中有利可圖,官僚、衙役以及上層旗人都加入到攫取利益的人群中。乾隆初年,和親王弘晝奏倉場事宜時稱,通州米局鋪戶多有賄囑倉役撞斛多量等弊。[30]除了在度量衡上作弊外,最常見的則有 “并票之弊”、“回漕之弊”等等,而這些弊癥都必須通過官商勾結方能完成。
所謂 “并票之弊”,是指旗人直接將米票擅自賣給商人。按照戶部則例,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并內務府官員應領俸米,需要該旗都統授權本旗總領及押旗參領等先赴糧倉換票,該糧倉于該旗總領到時,按照各官員數目每人換給米票一張,領回后散發給應領俸米官員,令其遵照定限自行赴倉支領。如果旗員并不持票領米而是將米票賣與鋪戶或擅交鋪戶領賣,就屬于 “并票”。[31](P174)“回漕之弊”則是指商人一旦在通州購得米票,往往會趁機將北上之漕米囤積起來,然后再沿運河水次南下售出。這些弊癥往往多發生于通州糧倉,即 “通州鋪戶買得官員米票,市儈奸胥,藉此勾連漁利,關支囤積,一俟重運將次抵通,正可潛赴水次售賣,是回漕之弊。”[32]換言之,通州糧倉相比京倉更便于鋪戶及相關人員串通作弊。以故,清廷申明“城內之米勿許出城,城外之米勿許出境”的禁令,并將此定例出示曉諭。[33]
但因利益所驅,在嘉慶十四年 (1809)竟發生了數位王爺、貝勒、貝子私自賣米賣票的事情。這些王公貴戚為 “節省車價,祇圖容易,將所領俸米即在通州賣去,甚至將米票在彼賣給奸民,以致米不入城,都市騰貴,而奸民乘機盜弄,冒領重支,囤積回漕”。對此,清廷規定,嗣后王爺貝勒、貝子等俸米,均責令運米入城,不得在城外售賣。如違,必當永革俸米。[34]
此外,覬覦俸米利益,與旗人形成債權與債務關系的還有錢鋪商人,而且他們對旗人施放的是高利借貸。
在雍正二年 (1724)三月,副都統覺羅佛掄的一份奏折中講了三類當鋪放債損害旗人的事例,俱發生在康熙年間。其一為 “小押”、 “小當”。“目今看得,有一名小當者,又名小押,處處開設,任意收取利息。其月息一兩銀可自四分至一錢,一千錢可自四十錢至一百錢。非但如此,凡人之典當物件,已過六個月,即不準贖”。其二為放債長短錢者。 “佐領領催伙同放債人,根據各佐領兵丁錢糧在此一月內所余情形,與放債人商量,在領取錢糧之前借貸,若借貸一兩銀錢,其利息可坐扣一百錢至二三百錢。領取錢糧之日,領催到部領回錢糧,而錢糧不到兵丁之手,即給予借貸人”。其三,賤價買、高價賣。“開倉前,不肖之徒 (鋪戶)伙同領催巧買兵丁米石。若一石米以時價折算應為一兩四五錢,但伊等兵丁領買米石之前,(鋪戶)只以五六錢銀買下一石米,若以七八錢銀買下一石米,則曰價昂貴。自閉倉后,賣米人 (旗人)無米時,即以一兩七八錢銀或以二兩銀買米而食之。若無銀買米時,又求領催,不論利息多貴,亦必借貸。”以上幾種手段, “皆暗中損害窮人以及愚昧兵丁”, “以致窮困潦倒者亦為頗多”。[35](P739-740)為此,清廷于康熙四十九年 (1710)正月,制定過一份有關借貸的章程,對借貸雙方進行制約。但是,后來的事實告訴我們,這份章程并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
雍正元年 (1723)八月,據鑲紅蒙古旗都統楊度奏稱:“或有兵丁遇有父母亡故等喜憂之事,向有錢人借貸,借七曰十,借二十曰三十,必立字據準以兵丁三季米為息,方才借給。名為放銀,實則暗中典押兵丁口米。倘不肖之人皆效仿而行,致使兵力日漸衰弱。”[36](P313)楊度的奏言引起了雍正帝的高度重視,隨后便由兵部尚書遜柱、大學士兼兵部尚書事務白潢等召集各旗都統、副都統50余人集議,議定 “嗣后以口米借貸銀兩之事永行禁止。倘仍有暗中借貸者,一旦查出或為旁人舉告,則將借貸雙方及其保人,并該參領、佐領、驍騎校、小領催一并交該部懲處,借出之銀概不償還”。并制定章程規定:“凡收典兵丁口米之人,食米四年,米還原主,不還借銀;食米三年,米還原主,銀還四分之一;食米二年,米還原主,銀還四分之一 (疑為銀還四分之二——作者注);食米一年以內,米還原主,銀還四分之三。此之償銀,皆視米主所得緩緩償還。”[37](P301-302)這份章程是在康熙四十九年章程基礎上修訂的,其條例有利于旗人借貸方。
雖然如此,但這種以放銀為名典押旗人俸米的行徑歷時已久,只因旗人迫于生計禁而不止,故雖有雍正元年的嚴禁,但其效果仍不容樂觀。到了嘉慶年間,竟有 “山東民人在八旗各衙門左近托開店鋪,潛身放債,名曰典錢糧”。[38](P11)
據嘉慶年間御史西瑯阿奏,所謂 “典錢糧”的具體做法就是: “以一月之期,取倍蓰之利。每月屆兵丁等支領錢糧,該民人即在該衙門首攔去扣算,該兵丁于本月養贍不敷,勢不能不將次月錢糧,逐月遞典,致被層層盤剝,受虧無窮,似此設計取利,較施放轉子、印子等錢尤為刁惡,于八旗兵丁生計大有關系。”[39]“典錢糧”又名 “轉子”、“印子”等,是鋪戶在向八旗兵丁施放 “轉子”、“印子”等錢時,以扣取八旗兵丁錢糧為前提,所以例禁綦嚴。
盡管如此,借貸雙方依然行之如故。據記載:“世族俸銀米悉抵押于老米碓房,侵漁逼勒久,遂握有全部之財權。因債權故,碓房掌柜之鄉親故舊稍識之無者,率薦入債家為教讀,遂握有滿族之教權。于是,旗籍人家無一不破產,并其子弟之知識亦無一不破產矣。”[40](P98)由清末人撰寫、民國初年刊行的 《燕市積弊》一書中也有類似的分析: “北京老米碓坊都是山東人所開,相沿已久,原不奉官。據理而斷,當初必是不準車騾裝載,每逢送米總是用人扛,無論多闊的碓坊也不敢使騾馬,假如硬改改樣,這就許犯私。山東人賦性樸實,原不會奸巧滑壞,惟獨這行偏有許多的毛病。內城叫做碓坊,又稱為 ‘山東百什戶’①山東百十戶,即山東撥什庫者。撥什庫為滿語,即隸屬于八旗佐領以下的低級小官。由于開設米碓坊的盡為山東人,且他們的高利貸生意是拿到旗人中的撥什庫等抵押的俸票和米票而付給銀兩,所以被稱作 “山東百十戶”。參見待余生:《燕市積弊》卷1,32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當初只準串米不準賣,故名 ‘碓坊’),名為賣米,其實把旗人收拾的可憐,只要一使他的錢,一輩子也逃不出他的手。”[41](P31)
不過,如果說是商人們預設之 “罟”導致了旗人的貧困甚或是滿人的衰敗的話,還是有嫌失之公平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商人憑借其經濟力量可以對有世爵的滿人大呼小叫,已形象地揭示出商人作為債權人與淪為債務人的旗人之間所發生的社會地位的轉變。
三、國家救助無果:旗人生計艱難
八旗乃清朝國力之根本,統治者無不以旗人生計為國家之首要問題,自入關伊始便關注旗人的利益,采取各種措施對貧困旗人進行救助。
一是順康時期國家向貧困旗人發放帑銀。順治年間,“上發帑銀四萬兩賞給八旗貧子”。[42]康熙帝自平定三藩后,“動支公帑數百萬,代清積逋”,“凡隨圍出征,雖給行月錢糧,官駝馬匹,猶恐用度不繼,設立八旗官庫以濟官兵”。康熙四十二年 (1703),又發帑金655萬貸給八旗兵丁。至康熙四十五年 (1706),將貸出而尚未扣完的395.66萬通行豁免[43],豁免之貸款達60%以上,這落實到每戶旗人,也可謂獲益甚豐。但遺憾的是,這些費用并未使旗人擺脫生計的困境,享受奢侈的城市生活已經成了旗人的習慣,而最令統治者感到頭疼的還是俸米不斷地從旗人手中流向市場。
二是以新的名目增加旗人的俸米,這主要發生在雍正初年。雍正元年 (1723)八月,雍正帝諭總理事務王大臣,令其參照外省副都統等酌給親丁坐糧的辦法,討論京城八旗 “將如何酌給伊等坐糧之處”。“尋議,京城滿洲都統親丁八名,蒙古、漢軍都統、領侍衛內大臣六名,前鋒統領、護軍統領、步軍統領五名,滿洲副都統三名,蒙古、漢軍副都統二名,步軍總尉一名,每月給銀三兩,每歲給米一十二石,每石折銀一兩。”[44]十一月,又有內閣侍讀學士三希保奏請給八旗窮困秀才糧米,擬實施“養育學生”之策,即于 “八旗舉人、秀才之內,凡為護軍披甲者俱令停差,照食糧米,以為讀書”。但仍有部分貧困無家業又無糧米之舉人、秀才,入護軍披甲不成,讀書亦不成,所以,三希保疏請將這部分人照停護軍披甲舉人、秀才之例,給其糧米。[45](P515)
三是創設雍乾時期的 “八旗米局”。八旗米局是政府干預俸米買賣的最直接舉措。所謂 “八旗米局原因鋪戶乘賤收買、居奇抬價有妨民食起見”。[46]早在20世紀70年代,日本學者細谷良夫就曾對八旗米局撰文研究,他指出,這是清政府為對抗米商、保障八旗俸餉經濟所采取的措施。[47](P181-208)但本文認 為,與 其說是清政府為對抗米商,毋寧說是想取代米商,由八旗自行解決其銀米兌換等問題。
從政府的角度看,導致旗人貧困的關鍵是米商對旗人的俸米買賤賣貴。“八旗官弁食余米必糶賣,商人囤米特為漁利壟斷,奸民彼此齊行,兵民兼受其累。”[48]“官員兵丁私賣米票,交鋪戶代領,及已滿花戶把持倉務,均干例禁。”[49]所以,清政府從國家的角度實施干預。
雍正六年 (1728)二月,正式設立八旗米局以取代鋪戶為旗人解決兌換錢糧的問題,兼及平抑糧價。對此,雍正帝在諭旨中是這樣表述的:“聞兵丁等于京通二倉支領米石時,每因腳價之費賣米充用,致有不計其米之接續,輒以賤價糶及,至缺乏又以貴價糴,此甚無益于兵丁者也。現今旗下俱有官房,或按八旗設立八局,或按滿洲蒙古漢軍分設立二十四旗,將兵丁欲賣之米以時價買貯,及其欲買則以平價賣給,如此似于兵丁大有裨益,著管理王大臣等公同詳議。”[50]尋議定八旗滿洲、蒙古、漢軍按旗設立米局二十四處,各領戶部銀五千兩,委官二員、領催四名辦理。通州于近倉之處分左右二翼設立米局二處,各領戶部銀八千兩,委官四員、領催八名辦理。[51]乾隆元年 (1637)二月,又定除滿洲、蒙古、漢軍、各旗設立米局二十四外,內務府三旗亦各立一局,共二十七處。乾隆三年 (1738)三月議準,每局各給銀二千五百兩作本,收買米石,并給米二千石平糶。[52]
八旗米局設立后,初期還是起到一定的引領市場米業、平抑米價的作用。雍正十一年(1733),廣東總督額彌達奏稱:“皇上降旨設立米局以來,歷年米價皆未昂貴,總由米局價平,故囤戶不能射利。”[53](P975)但官設米局很快便被鋪戶商人所利用:“八旗米局開倉時,鋪戶乘賤收買,居奇抬價。”乾隆帝認為這是管理不善所致:“現設二十四 (米)局,不能盡得妥協之人經理其事,以致辦理多有未善,或任聽奸民赴局私買,囤積漁利,轉滋弊竇。應將現在米局酌量裁并。”雖然八旗大臣遵照諭旨進行了討論,認為“從前辦理不善,原因在每局分隸一旗,經管多員,責成未專所致”,提出官米局坐落地方、需米多少,不必拘定原額,其八旗總理大臣請旨簡用等辦法。但是,以 “京師地廣民繁,官局米需多貯,一局地窄,收貯無幾,且糴米人眾擁擠,恐奸商混雜私販”。[54]從論及的問題仍可以看出他們對官設米局之作用存有疑慮。也正是由于八旗米局的作用有限,所以至乾隆十七年 (1757)二月,八旗米局在經歷了二十五個春秋之后便宣告停止。
四是調整俸米發放時間。由于俸米不斷流入市場并對京城米價產生影響,早在康熙時就引起統治者的關注了。五十五年 (1716),康熙帝因京畿地方雨水不足,莊稼干旱,擔心米價抬高后影響到八旗俸米的發放。他說:“八旗官兵糧米定例于八月內支放,今若候至八月,米價必愈加騰貴,著于五月初十日起即行支放,至京城米石若仍行減糶,甚為有益,著再發米三萬石交與原派賣米官員減價糶賣。”[55]
至乾隆時,針對商人囤積米石,乾隆皇帝實施了預借或提前發放八旗官米的措施。乾隆十七年 (1757)二月,著將王公滿漢大臣官員俸米,除本年二月應行支領外,并秋季及明年一年俸米預先借給,認為王公大臣等家有余糧,不與閭閻爭購,米價亦必漸次平減。 “至所有豫領米石,務宜撙節食用,不得任鋪戶乘機興販出境及囤積居奇,并應嚴禁燒鍋糜費。”[56]尋又行八旗甲米按月輪放之制。“查鑲黃、正黃、正白三旗并上三旗包衣應領米數較下五旗為多,請將鑲黃、正黃二旗于正月、四月、七月、十月支放;正白、正紅、鑲白三旗于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支放;鑲紅、正藍、鑲藍三旗于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支放。”[57]
五是在保護八旗利益的同時,對商人鋪戶予以限制。如規定,京師五城各鋪戶所存米麥雜糧等項,定例每種不得過八十石,儻逾數囤積,即照違制律治罪。嘉慶六年 (1801)冬,因 “潛訪得京城內外各處米局,所存米石自數百石至千余石不等,恐不無囤積居奇情事。若照定數祇準存貯八十石,違例罹法者必多”。[58]所以,又規定“五城鋪戶所存米麥雜糧,每種例不得過一百六十石”[59]等等。
但是,無論政府采取何種措施,旗人與商人之間所形成的經濟關系已經無法改變,商人的經濟力量滲透于俸米發放過程的各個關節。最重要的是,清朝在以俸餉確保旗人的衣食無憂的同時,也使旗人養成了 “不善謀生,惟恃錢糧度日,不知節儉,妄事奢靡”[60]的習慣,以至于旗人無法抗拒進入城市之后的種種誘惑。所以,在康熙時期,下層旗人的貧困化已經顯露出來。
據記載,康熙初年,旗人便在城市化過程中逐漸丟掉了在關外的樸實之風,所謂 “滿洲習于嬉戲,凡嫁娶喪祭過于糜費,不可勝言。蒙古惑于喇嘛,罄其家貲不知顧惜……近見以佐領爭訟者甚多,但知希圖榮貴,而愛養所屬之道,全然不知”。“賭博雖禁,猶然未止”,以至于 “滿洲貧而負債者甚多”。[61]康熙一朝,雖 “不惜數百萬帑金遍行賞賜”,然八旗人等非但不藉此務立生計,清償夙逋,反而 “惟知縱酒酣飲,鮮衣肥馬,過于費用,則不數日間仍如未沛恩澤時”。[62]至康熙末年,“見今八旗,得見舊日風景者已無其人,而能記憶祖父之遺訓者亦少,以致風俗日奢,人心不古”。[63]
雍正帝剛一登基,便有諭旨斥責旗人奢靡:“比見八旗官員兵丁內嗜飲沉湎,以致容貌改常,輕生破產,肆行妄為者甚眾。”[64]雍正皇帝所言并非危言聳聽,官員中也多有疏奏,稱八旗兵丁奢靡。雍正元年 (1723)三月,山東道監察御史尹達里在奏折中說,剛剛領到餉銀的 “八旗兵丁不守本分,三五人成群結伙入城外飯館酒肆食飲,一次耗費銀子二三兩,每月養家之銀一次即揮霍于盡,不顧妻子饑寒者甚眾”。[65](P47)四月,吏科掌印給事中崔致遠在給雍正帝的折子中,明確地談到他在京城看到的 “京城官民窮蹙日甚”的現象。他說:“臣向年初入京師之時,竊見城市之間甲第連云,裘馬耀日,人物之都立,百貨之翔集,游?之風華,街區之喧阓,何其盛也。數年以來,漸見凋零,人民猶是風景蕭然,近因歲欠窮乏益甚。在旗員之窮窮于無錢,漢官之窮更窮于無米。”以至于有 “鬻仆典衣變色黑米,日恐不繼,此官之窮也”。[66](P253)至雍正五年(1727),滿洲中竟然 “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賣房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肉,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多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貯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沽酒食肉恣用無余,以致合家匱乏,凍餒交迫,尚自夸張謂,我從前曾食美物服鮮衣,并不悔悟所以困窮者,乃以美食鮮衣之故也”。[67]
八旗的貧困化如同瘟疫一般蔓延迅速,就連八旗高級官員中如 “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內,頗有家計艱窘之人”。是年八月,福建巡撫黃國材也在折奏中談到這一點,認為其起因在于奢靡之風所致,而旗人所以奢侈乃效仿漢人所為。他說:“八旗之人初入關時,凡披甲每月不過給錢糧三兩,然而家家溫飽,絕無愁窮嘆苦之聲。雖日下人口漸次繁多,而皇恩高厚,又已添設甲兵,給予馬糧,又加增月支錢糧種種。豢養之恩愈深,八旗之窮愈甚,揆闕所由,皆因百姓風俗奢侈,旗人漸染效尤所致。”[68](P825-826)為此,他請旨禁奢侈并厘定京城官民服制。
在清朝,一方面是統治者不斷想方設法,以解決八旗的生計問題,另一方面,是旗人的奢侈揮霍,仰仗國家給俸給米,且不時救濟,而不事家計安排,致生計窘迫加劇。以雍正朝之嚴厲整飭,十余年后仍未奏效。雍正十二年 (1734),“乃近聞八旗人等仍有未改陋習,(多有)以夸多斗靡相尚者”。[69]可以看出,在雍正年間,旗人因追逐奢靡享樂而典賣錢糧,旗人生計的諸多問題已經凸顯無遺了。
乾嘉以后,旗人生計更是每況愈下。八旗“用度所以不足者,固由生齒日繁,物價昂貴,亦由平日不知撙節。若能將衣食二者隨時加意省嗇,即可免于匱乏”。然事與愿違,嘉慶帝曾感嘆道:“我滿洲淳樸舊風,衣服率多布素。近則狃于習俗,兵丁等競尚鮮華,多用?緞,以穿著不及他人為恥。試思旗人原以學習清語騎射為本,伊等技藝生疏何以不知愧恥,惟于衣飾欲圖體面耶!”[70]
奢侈的導向就是腐化。嘉慶年間,京城賭博成風,旗人開設賭局者不乏其人,參賭致傾家蕩產者也不乏其人。由于官員監管不力,成屢禁不止之勢。嘉慶帝斥責大學士兼任步軍統領祿康說:“專司緝捕,凡京城內有犯禁不法為匪滋事之人,皆當嚴拏凈絕,方使奸宄斂跡。輦轂肅清,乃平日一味寬厚,不加整頓,致涉懈弛。前月御史韓鼎晉奏內城賭風甚熾,系諸大臣之轎夫開局等語。”[71]這種社會風氣無疑是加速下層旗人貧困化的催化劑。
而對于大多數旗人而言,平時的無所事事,早已養成了游手好閑、奢華無度的習氣。松筠的日記再現了旗人周而復始的生活狀況。道光九年(1829)正月十三日,“早起,用餐畢,出,至石碑胡同尋常祥圃,同行出德勝門,至德盛園,聽景和春戲班唱戲,聽名角池才官 《蜈蚣嶺》,晚別去,入城,各自返家”。四月十八日, “餐畢出,至巡捕廳胡同富大爺家拜訪,久坐同出,至宮門口火神廟伊岳父家看房。出,富大爺請余至全珍館飲酒,食餃包子”。五月二十九日,“早餐畢,常祥圃來學堂,同出阜成門,至茂林居茶館旁林深陰涼處,鋪葦席而坐,竟日飲茶、喝酒、食餑餑。本日,余分文未帶,皆由祥圃付賬。晚入城,各自返家”。道光十年 (1830)五月初六日, “早,德惟一阿哥來,同行出正陽門,至天慶樓等候祥圃阿哥,祥圃來食水餃,于中和園聽景春和班唱戲,晚入宣武門雇車至四牌樓下,于至誠齋飲茶、食面,定于明日再會”。[72](P81、109、120、216)這幾天 不 過 是旗人生活的一個縮影,但卻可以說明,旗人大部分的活動空間都在飯館、茶館、戲園等宴飲娛樂之地,所做的也盡是吃喝玩樂之事,長此以往,已成積重難返之勢。
綜上所述,八旗的不農不工不商從屬于首崇滿洲制度,清朝統治者在為八旗及兵員提供保護的同時,也使旗人等陷入身份的制約,在“旗俸”成為旗人賴以生存的唯一經濟來源時,必然要面對城市化帶來的諸多無解難題。因此,旗人食俸制度在確保旗人的經濟特權的同時,也將入關后的八旗子弟締造成養尊處優、無所事事的社會庸人。這是導致八旗衰落的最重要原因。
[1]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獻通考》卷42,國用四,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
[2]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獻通考》卷43,國用考五,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
[3]《清仁宗實錄》卷250,嘉慶十六年十一月丁酉,臺北,華文書局,1969。
[4][5][6][10]《欽定戶部則例》卷15,倉庾一,同治四年本。
[7]《清圣祖實錄》卷241,臺北,華文書局,1969。
[8]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獻通考》卷37,市糴六,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
[9]石繼昌:《春明舊事》,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11]郭松義:《清代北京的山西商人——根據136宗個人樣本所作的分析》,載 《中國經濟史研究》,2008(1)。
[12]李光庭:《鄉言解頤》卷5,北京,中華書局,1982。
[13]王慶云:《石渠余紀》卷4,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
[14]《清高宗實錄》卷1280,乾隆五十二年五月辛巳;壬申;戊寅。
[15][31]《金吾事例》,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16]齊如山著、鮑瞰埠輯:《故都三百六十行》,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
[17][23]《清世宗實錄》卷7,雍正元年五月丙戌。
[18]《清高宗實錄》卷409,乾隆十七年二月戊申。
[19]《清仁宗實錄》卷100,嘉慶七年七月癸未。
[20]震鈞:《天咫偶聞》卷3,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21][34]《清仁宗實錄》卷214,嘉慶十四年六月乙卯。
[22]《清圣祖實錄》卷241,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庚寅。
[24][27][72]松筠:《閑窗夢錄譯編》,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1。
[25]《清高宗實錄》卷99,乾隆四年八月甲午。
[26]《清仁宗實錄》卷362,嘉慶二十四年九月戊寅。
[28][40]夏仁虎:《舊京瑣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
[29]舒濟、舒乙:《老舍小說全集》,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
[30]《清高宗實錄》卷87,乾隆四年二月甲辰。
[32]《清仁宗實錄》卷165,嘉慶十一年八月癸未。
[33]《清仁宗實錄》卷170,嘉慶十一年十一月丁巳。
[35][36][37][45][6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譯編:《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合肥,黃山書社,1998。
[38]光緒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1161,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印本,1976。
[39]《清仁宗實錄》卷225,嘉慶十五年二月壬辰。
[41]待余生:《燕市積弊》卷1,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
[42]《清世祖實錄》卷111,順治十四年八月丁酉。
[43]《清圣祖實錄》卷227,康熙四十五年十一月癸酉;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甲戌。
[44]《清世宗實錄》卷10,雍正元年八月丁卯。
[46]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獻通考》卷37,市糴六,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
[47]細谷良夫:《八旗米局考:關于清朝中期的八旗經濟》,載 《集刊東洋學》,1974(31)。
[48]《清高宗實錄》卷64,乾隆三年三月壬戌。
[49]《清仁宗實錄》卷331,嘉慶二十二年六月甲戌。
[50]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獻通考》卷35,市糴四,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
[51]《清世宗實錄》卷66,雍正六年二月甲午。
[52]《清高宗實錄》卷226,乾隆九年十月壬子。
[53]額彌達:《請官開米局疏》,載賀長齡、魏源等編:《清經世文編》卷40,北京,中華書局,1992。
[54]《清高宗實錄》卷397,乾隆十六年八月癸亥。
[55]《清圣祖實錄》卷268,康熙五十五年四月壬戌。
[56]《清高宗實錄》卷408,乾隆十七年二月辛丑。
[57]《清高宗實錄》卷409,乾隆十七年二月戊申。
[58]《清仁宗實錄》卷91,嘉慶六年十一月壬寅。
[59]《清仁宗實錄》卷270,嘉慶十八年六月壬寅。
[60][67]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獻通考》卷39,國用一,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
[61]《清圣祖實錄》卷44,康熙十二年十二月辛丑。
[62]《清圣祖實錄》卷212,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己亥。
[63]《清圣祖實錄》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乙亥。
[64]《清世宗實錄》卷2,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壬戌。
[66][6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1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69]《清世宗實錄》卷143,雍正十二年五月壬辰。
[70]《清仁宗實錄》卷100,嘉慶七年七月癸未。
[71]《清仁宗實錄》卷244,嘉慶十六年六月癸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