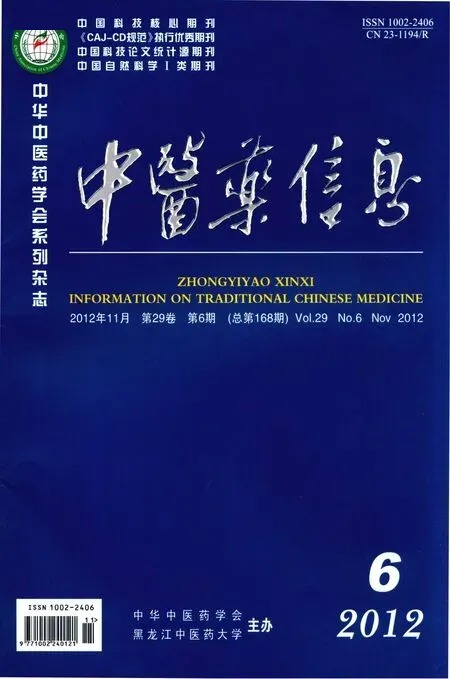腫瘤治療:扶正與解毒的平衡
陳賜慧,花寶金
(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北京 100053)
惡性腫瘤是嚴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常見多發病,近年來發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目前針對惡性腫瘤的治療,逐步向個體化治療、綜合治療和循證醫學的方向發展。而腫瘤的防治研究,也正從基于“病理學基礎”向“病理-生物學”基礎轉變,從殺滅腫瘤細胞向改變腫瘤微環境轉變[1]。近年來的研究發現,腫瘤的侵襲性的強弱在原發瘤階段即已存在,腫瘤的轉移復發是癌生物學特性最集中的表現,也是目前最難解決的問題。各種以“消滅腫瘤”為手段的療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腫瘤的療效,然而并未明顯影響總體生存率。因此,有人提出[2]“消滅腫瘤實際上加速癌抵抗和復發的出現,”并且爭論腫瘤的治療到底是完全消滅,還是讓其生存[3]。目前的觀點趨勢傾向于強調在最大限度消滅腫瘤的(手術、放療、化療、局部治療)的同時,重視對少量殘余腫瘤的調變及腫瘤宿主機體的改造(如生物治療、中醫中藥),爭取使腫瘤細胞改邪歸正,降低侵襲轉移潛能,使腫瘤宿主機體不適合腫瘤的生長。這一觀點與中醫學一直以來對腫瘤的防治觀點趨于一致,強調機體與腫瘤之間的矛盾平衡,也即扶正與解毒的平衡。
1 腫瘤的病因源自失衡
1.1 根本原因在于內虛
對于腫瘤病因的認識,中醫歷代醫家以“內虛”立論居多。《內經》提出“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百病皆生于氣”,并認為“精氣奪則虛。”其對腫瘤的記載相對比較簡單。漢唐時期,《諸病源候論》及《千金要方》對“積聚”的論述,表明腫瘤扶正培本學術思想的初步形成。至宋金元時期,腫瘤扶正培本學術思想逐步成熟。東軒居士在《衛濟寶書》中首次提出“癌”的名詞。明清時期,腫瘤扶正培本學術思想深入發展,如張景岳認為,“脾腎不足及虛弱失調之人,多有積聚之病…”。《醫宗必讀》更是直接指出“積之成者,正氣不足,而后邪氣踞之。”基于“內虛”理論,現代研究亦深入探討了“內虛”在腫瘤發生發展中的作用,并發現腫瘤病人的免疫功能(正氣)受到抑制,腫瘤的發生和發展及預后與帶瘤機體的細胞免疫狀態密切相關[4]。
1.2 癌毒是不可或缺的條件
腫瘤的發生,在正氣虧虛的條件下,癌毒是產生腫瘤的關鍵因素。對于癌毒的論述,古代醫家多有記載,然而均未明確提出“癌毒”的概念,而統稱之為“毒邪”。如《中藏經》認為:“癰瘍瘡腫之所作也,皆五臟六腑蓄毒之不流而生矣,非獨營衛壅塞而發者也。”隨著基礎和臨床研究的深入,“癌毒”的概念越來越受到認可,并且認為“癌毒”是惡性腫瘤發生、發展過程中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周仲英教授認為[5],癌毒是導致腫瘤發生的一種特異性致病因子,屬毒邪之一,是在內外多種因素作用下,人體臟腑功能失調基礎上產生的一種對人體有明顯傷害性的病邪,具有增生性、浸潤性、復發性、流注性等特性。凌昌全教授[6]則結合中西醫學對惡性腫瘤的認識,把癌毒定義為“已經形成和不斷新生的癌細胞或以癌細胞為主體形成的積塊”。并認為癌毒是惡性腫瘤產生的病機的核
基金項目:國家科技部“重大新藥創制”專項課題(2010ZX09102-216)
作者簡介:陳賜慧(1984-),男,北京中醫藥大學在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醫藥防治腫瘤復發轉移。
通訊作者:花寶金(1964-),男,主任醫師,主要研究方向:中醫藥防治腫瘤復發轉移。
收稿日期:2012-04-24
修回日期:2012-05-16
心,癌毒及其產生的病理性代謝產物通過血液、淋巴液的循環擴散到全身,致使整體功能失調,繼而耗傷正氣,并與氣、血、痰、熱等糾結在一起,進一步產生一系列的病理變化。癌毒一旦形成就具有迅速生長、擴散和流注等特性,必須及時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段,最大限度的消滅癌毒。
1.3 正氣與癌毒的失衡
目前腫瘤的發病越來越趨向于年輕化,這一現象無法單純運用內虛或者癌毒來進行解釋。從人體生命的正氣發展規律來看,中青年正處于“筋骨堅,發長極,身體盛壯”,或者“筋骨隆盛,肌肉壯滿”的條件下,即便“始衰”,亦不至于成積、成瘤。而癌毒的積聚亦需要一定的時間。因此可以認為,腫瘤的發生是正氣和癌毒二者之間的平衡被打破,正氣內虛為主或者癌毒過盛為主,最后均表現為癌毒占據優勢。這種失衡現象在現代研究中亦多有發現。如賈勇圣等[7]將癌基因分為陰陽,并以癌基因myc和抑癌基因p53為例說明其相關性,p53以促進細胞凋亡為主,故為陰,陰中之陰是抑制細胞生長促進細胞凋亡,而陰中之陽則是修復受損DNA,使細胞繼續存活。myc以促進細胞生長和增殖為主,故為陽,陽中之陽是促進細胞生長和增殖,而陽中之陰則是誘導細胞凋亡。這種陰陽的表現在腫瘤發展中為p53失活或myc激活者居多。另外在腫瘤的發生發展過程中,細胞信號傳遞網絡亦會發生失衡現象。如細胞生長、分裂和增殖相關的信號傳導通路多處于異常活躍的狀態,如生長因子及受體、G蛋白、細胞周期調控因子等,從而表現為增殖失控。與此相反,與機體清除異常、衰老細胞的重要機制以及細胞凋亡機制受到抑制,如TNF、Fas/FasL等,從而凋亡減少[8]。
2 腫瘤的治療在于平衡
2.1 治療法則
中醫學對于疾病的治療認識,可以概括為“實則攻之,虛則補之”。針對惡性腫瘤的治則,目前臨床常用的有益氣健脾、養陰生津、溫腎壯陽、活血化瘀、軟堅散結、清熱解毒、祛濕化痰、疏肝解郁等等。從腫瘤的發病機理,無外乎扶正及解毒二法。扶正又稱為扶正固本、扶正培本,是基于腫瘤的“內虛”理論而確立的一大治療法則[9]。其目的是通過對腫瘤患者的陰陽氣血的扶助與調節而改善其“虛證”狀態,提高機體自身的抗癌能力,達到祛除腫瘤的目的。解毒法則是針對癌毒的病機而確立的一大治療法則。在腫瘤的發生、發展及復發轉移過程中,除癌毒之外,還存在痰、瘀等病理產物,然而癌毒是其中最關鍵的一點,直接決定了惡性腫瘤的惡性程度,而不同于一般的氣滯、血瘀、痰凝等所致的慢性雜病。因此,扶正和解毒是腫瘤治療中的根本法則[10]。
2.2 分期論治
中醫學的兩大特點是“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現代醫學的個體化診療方案即是中醫“同病異治”、“異病同治”這一“辨證論治”的現代化闡釋。《素問·至真要大論》論述了“堅者削之”、“留者攻之”、“結者散之”、“客者除之”、“損者益之”的原則,體現了根據不同的疾病性質進行不同的治療。由于患者機體狀態、腫瘤分期及腫瘤生物學特性差異較大,臨床治療法則亦不同。從分期而言,在腫瘤早期,患者一般體質尚可,正氣充足,腫瘤處于生長期,癌毒亢盛,此時未形成明顯的腫瘤相關免疫抑制,即虛證不明顯,在治療上,應以祛邪解毒為主,積極采用手術、放療、化療、局部治療(冷凍、激光、射頻等)盡快去除腫瘤。這種攻邪祛毒的手段,在虛證不明顯的時候,中醫藥優勢并不明顯,因此中醫藥的應用主要在于各種治療的輔助治療,而且以扶正為主,使扶正與解毒達成一個平衡。在腫瘤中期,腫瘤增大,消耗增加,形成明顯的免疫抑制,人體正氣消耗明顯,這一時期,往往正邪力量勢均力敵,或正邪相當,或癌毒略減,或正氣稍強,在治療上常扶正與解毒并重,視其相互平衡消長而治。當腫瘤趨于晚期,癌毒熾盛,而正氣耗竭,無力抗邪,成邪盛正衰之勢。此時應“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急癥明顯,則以治標對癥為主,隨后以扶正治療為主,因晚期腫瘤治愈可能性較小,因此扶正應佐以解毒之法,使癌毒與正氣的力量逐漸趨于平衡,達到長期帶瘤生存。
2.3 遣方用藥
《素問·至真要大論》有言“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強調調整陰陽平衡。而清代張隱庵則指出“寒熱補瀉兼用,在邪正虛實中求之。”在扶正與解毒的平衡上,遣方用藥常表現為相反相成,矛盾統一,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2.3.1 攻補兼施
攻補兼施是腫瘤治療最主要的方式,使祛邪而不傷正,扶正而不留邪。臨床常用四君子湯或六君子湯加減扶助正氣,同時加用白花蛇舌草、白英、龍葵、石見穿、蜈蚣等抗癌解毒之品,扶正與解毒藥的權重和劑量視患者正氣與癌毒的關系而定,在不同的腫瘤、不同的分期、不同的體質狀態下,均需隨時調整處方,微調平衡,使失衡的狀態逐漸恢復平衡。
2.3.2 寒熱共用
腫瘤患者的臨床表現常錯綜復雜,中醫辨證多有寒熱錯雜的證候,因此處方常寒熱同調。如對于腫瘤化療引起的惡心、嘔吐、腹瀉等癥狀,臨床常用瀉心湯類加減,既用芩、連之苦寒降火除熱,又用姜、夏之辛溫開結散寒,恢復中焦脾胃的斡旋功能。解毒抗癌攻下的藥物常為寒涼之劑,容易耗傷脾腎陽氣,臨床多配以溫腎健脾之品,避免寒涼傷陽氣。
2.3.3 升降相因
《素問·六微旨大論》指出:“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腫瘤患者因情志、飲食及治療的影響,多存在氣機失調的病理狀態。調整氣機常升降相因,升浮藥與沉降藥同用,使氣機當升者升、當降者降,升降有序。如肺氣不降引起的大便干結,常以桔梗與枳殼為伍,前者宣肺氣,后者降腸氣,一升一降。心腎不交引起的失眠,常以交泰丸加減,黃連下心火,肉桂補腎水,亦屬一升一降的范疇。
2.3.4 動靜結合
因腫瘤治療中扶正治療占有很重要的比例。而補益之品多滋膩礙胃,反而影響脾胃功能。補益藥多屬“靜”,臨床常“動藥”與“靜藥”同用,使動、靜存乎于一而增療效。如應用溫中健脾之劑,常用生白術、茯苓、生薏苡仁等,多輔以醒脾化濕之品,以增加其運化能力,如廣藿香、紫蘇梗、荷梗、砂仁等。惡性胸水,應用葶藶大棗瀉肺湯、己椒藶黃丸等瀉肺逐水時,常加用桂枝溫運陽氣,增加其“動”性,以化氣行水。
總之,“陰平陽秘,精神乃治”,疾病的發生均由陰陽的失衡所致,腫瘤的發生發展也是這種陰陽平衡和正邪矛盾不斷被打破的過程,因此治療中應以扶正及解毒二法為總綱,不斷的調整人體內環境,使其重新趨于穩態,以達防治腫瘤的目的。
[1]湯釗猷.現代腫瘤學[M].3版.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9.
[2]Gatenby RA.A change of strategy in the war on cancer[J].Nature,2009,459(7246):508 -509.
[3]Andre N,Pasquier E.For cancer,seek and destroy or live and let live?[J].Nature,2009,460(7253):324.
[4]花寶金,樸炳奎.腫瘤虛癥及扶正培本的現代免疫機制研究[J].哈爾濱商業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1,17(1):5-7.
[5]葉麗紅,顧勤.周仲瑛教授的腫瘤觀[J].中國中醫藥信息雜志,2002,9(3):63 -64.
[6]凌昌全.“癌毒”是惡性腫瘤之根本[J].中西醫結合學報,2008,6(2):111-114.
[7]賈勇圣,鄭建全.癌基因和抑癌基因中的陰陽[J].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2009,29(1):72 -75.
[8]曾益新.腫瘤學[M].2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3:129-152.
[9]王愛紅,陳美霓,符兆英.誘導腫瘤細胞凋亡的天然藥物及其作用機制[J].中醫藥學報,2011,39(1):125 - -128.
[10]錢紅霞.論扶正法在腫瘤治療中的重要性[J].西部中醫藥,2011,24(8):4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