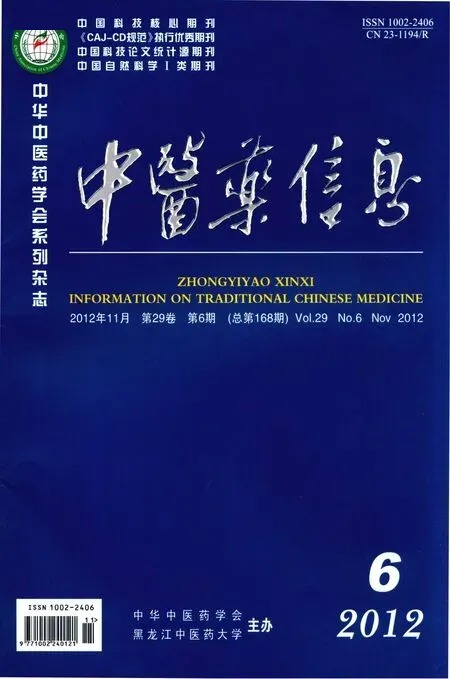中醫辨證論治研究進展述評(二)
楊徐杭,汶醫寧
(1.陜西中醫學院,陜西 咸陽 712046;2.陜西中醫學院附屬醫院,陜西 咸陽 712000)
1 病證結合研究取得新成果
西醫辨病與中醫辨證結合,可以使臨床優勢互補。王階[1]等主編的《病證結合中醫證候學》采用病證結合的形式,以常見疾病為章名,分述該病的證候分布、證候診斷、證候-方劑、證候臨床特征及證候療效評價等內容,既展示了中醫診療方法的獨特優勢,又對各病證候進行了深入研究。其中“冠心病心絞痛病證結合的診斷標準與療效評價標準”是王階主持的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項目的最新研究成果。柴劍波[2]等認為,病、證、方三者的有效結合是中醫辨證論治的核心。“方證相應”強調了方藥與病證之間的高度的對應性,“病證結合”強調了通過辨病與辨證的結合體現病變整體的縱橫聯系性。“方證相應”理論為“病證結合”動物模型創建提供了理論依據,為中醫“病-證”的本質研究提供了新途徑,并為通過“方”來探索已知疾病中醫“證”的病機研究提供了科學假說的可能,有助于闡明臨床上不同方劑針對相同疾病的不同作用機理,闡明現代醫學疾病的主要中醫證候病機。王天芳[3]提出病證結合診斷標準的建立,要在建立基于宏觀的證或證候要素診斷標準的基礎上,充分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和理論,不斷深入研究證或證候要素的本質,反過來再不斷充實、完善其診斷標準。
在病證結合臨床研究方面,陳可冀[4]主張病種選擇應側重在:1)適應當代國家/社會的需求,嚴重危害人民健康嚴重的常見病、多發病,如腫瘤、心腦血管病、糖尿病等;2)凸顯中醫藥療效優勢的病種,如功能性疾病、免疫性疾病、過敏性疾病、病毒性疾病、皮膚病、消化及泌尿系統病、情志病、骨關節病、小兒及老年性疾病、更年期綜合征等。病證結合臨床治療可以針對目標疾病、目標證候、目標癥狀或四者兼顧,或從整體調節入手,或從局部問題入手,解決其中某個問題。提倡多元模式臨床醫療的研究設計和療效評價,包括雙重的目標病種選擇,雙重的研究方法思考,雙重的評價標準的整體復合,以及進一步的循證醫學引入,建立增強式的病證結合、宏微觀和整體局部統一的循證醫學模式,解決可重復性的病證結合臨床實用的標準化范式或框架,傳承發展,提高自主創新的能力,進一步提高療效。陳可冀[5]用活血化瘀方藥干預冠心病介入治療后再狹窄,為活血化瘀中藥制劑預防冠心病介入治療后再狹窄形成和心絞痛復發、改善患者長期預后提供了有效的中藥治療途徑。錢桐蓀[6]認為,中西醫結合辨病辨證論治其療效既高于中又高于西。中西醫結合治病的方法論分為3類:1)按中西醫結合辨病辨證論治;2)按該病西醫的發病機制或其病理生理學為主,進行中西醫辨證論治;3)按該病西醫的病理形態學改變為主,進行中西醫辨證論治。趙玉梅[7]認為,中醫藥的辨證論治具有多向調節作用,在自身免疫病如多發性肌炎、甲狀腺亢進癥、原發性膽汁性肝硬變、干燥綜合征、系統性硬化病、類風濕關節炎、系統性紅斑狼瘡等具有獨特的優勢。劉薇[8]認為,PCI術后冠心病的病機特點主要為氣陰兩虛、痰瘀互結,屬本虛標實證。在治療過程中要正確處理補氣與祛瘀的關系,使補氣不留瘀,祛瘀而不傷正,臨床上以中醫辨證治療
基金項目:陜西省科技廳課題(2007C234)
作者簡介:楊徐杭(1958-),女,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證候規范化。
收稿日期:2012-03-22
修回日期:2012-04-17
與西醫綜合治療相結合的方法,為治療心肌梗死PCI術后再狹窄的最佳方案。陳丹萍
[9]
等認為,中藥復方調血脂膠囊(丹參500g,水蛭250g,山楂、草決明、何首烏各166g,三七7.5g)對血脂異常的氣血瘀滯型、痰濁中阻型、脾腎陽虛型、肝郁氣滯型療效有差別。通過監測患者治療前后的血脂指標,提出該配方適用各種類型的血脂異常患者,但對氣血瘀滯型和脾腎陽虛型患者治療效果更明顯。張燕軍
[10]
等用健脾滲濕基本方(茯苓、扁豆、山藥、薏苡仁、黃芪、黨參、白術等)結合辨證加減治療化療致難治性腹瀉,認為可起到扶正固本,標本兼治的功效,可快速緩解化療藥物毒性所致臨床癥狀和伴隨癥狀。趙治友
[11]
等將強直性脊柱炎患者治療組中醫辨證分型為寒濕痹阻型、濕熱壅滯型、瘀血阻絡型、腎虛失養型,分別給予干姜苓術湯加減、四妙丸加減、身痛逐瘀湯加減、左歸丸或右歸丸等治療,聯合應用改善病情藥柳氮磺胺吡啶片;對照組用柳氮磺胺吡啶片治療。認為辨證論治聯合慢作用藥治療強直性脊柱炎療效優于慢作用藥組,有增效減毒作用。
2 對“辨證論治”的認識深化
自提出“辨證論治”一詞后,一直未有統一的概念范圍,有不同的看法,也產生多種誤用情況。李宇銘[12]從文字的角度分析,認為“證”是指能夠反映疾病本質的“臨床表現”,而非現在一般所說的“某一階段的病理概括”;“辨證論治”則是按照辨別證候時所獲得依據,經過分析后作出治療方法的判斷,實際上即“辨證求因,審機論治”的縮寫。再從中醫理論的角度理解,“證”所強調的是“司外揣內”,亦即因“有諸內必形于外”而產生了“證”,證的產生是基于藏象學說,“辨證論治”實與“整體觀念”密不可分。認為產生誤用情況主要有五點:一是使用了病、癥和證的新定義,其實這三者本身含義基本相同,均是指“臨床表現”的意思,新定義使中醫教材變得混亂;二是關于辨證和辨病相結合,其中的“辨病”可分為“辨西醫的病與辨中醫的證相結合”,和“辨中醫的病與辨中醫的證相結合”兩大類,前者并非理論上的結合,而是臨床優勢互補,后者則是從根本處已經結合了,無需另提結合。三是關于“方證相對”而跳過了病機的問題,即是“對癥治療”,使中醫理論倒退;四是“方病相對”的分型論治,甚或“專病專方專藥”的趨勢,使中醫的診治簡單化,忽略了疾病的時間狀態;五是證本質的研究,實際上所研究的并非“證”,而是指“中醫病機的物質性研究”,由于微觀研究并非“辨證”,所以“宏觀辨證與微觀辨證相結合”的說法,從概念上不可能實現。
3 存在的問題
劉麗星[13]等指出,中醫證候的量化研究有諸多問題亟待解決。如量表的效用多大程度上代表中醫證候的診斷和療效評價?只包含問診及望舌內容的證候量表能否涵蓋望聞問切全部內容?目前的量表是否有為揉進中醫元素而揉進中醫元素的傾向?辨證量表更多是考慮辨證論治、整體觀;而療效評價量表削弱了辨證的色彩,更多是“天人相應”、“形神統一”、“五志七情”等中醫元素,那么體現這些中醫元素的癥狀會短時間改善嗎?是否會影響療效評價?哪些條目又是較為敏感的?認為辨證量表及證的療效評價量表并不能代表中醫診斷及療效評價的全部內容,其地位及應用場合還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張業[14]等從“方證相對”“方證相應”“方證對應”“方證相關”等方面研究了方證關系的科學內涵,認為中醫方證關系研究尚存在方、證研究相互分離;方、證研究角度固定;方、證研究方法單一等問題。
[1]王階,何慶勇.病證結合中醫證候學[M].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11.
[2]柴劍波,李冀,李勝志,等.“方證相應”理論在“病證結合”研究中的運用[J].世界中西醫結合雜志,2011,6(8):711 -713.
[3]王天芳.病證結合診斷標準的建立[J].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2011,31(8):1025 -1026.
[4]陳可冀.病證結合治療觀與臨床實踐[J].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2011,31(8):1016 -1017.
[5]史大卓.陳可冀院士冠心病病證結合治療方法學的創新和發展[J].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2011,31(8):1017 -1019.
[6]錢桐蓀.中西醫結合辨證論治的方法論[J].中國中西醫結合腎病雜志,2011,12(4):283 -285.
[7]趙玉梅.中醫藥的辨證論治在自身免疫病中的應用[J].牡丹江醫學院學報,2011,32(3):68 -70.
[8]劉薇.PCI術后再狹窄的中醫辨證論治探析[J].河南中醫,2011,31(11):1220-1221.
[9]陳丹萍,李爭紅.血脂異常的中醫辨證論治實驗室療效監測[J].當代醫學,2011,17(19):144.
[10]張燕軍,崔大江,雷寶霞,等.健脾滲濕為主結合辨證論治化療致難治性腹瀉36例[J].陜西中醫,2011,32(8):1001-1003.
[11]趙治友,鄔亞軍,王新昌.辨證論治對慢作用藥治療強直性脊柱炎的增效減毒作用研究[J].浙江中醫藥大學學報,2011,35(4):521-523.
[12]李宇銘.論“辨證論治”的本義[J].中醫藥通報,2011,10(2):38-40.
[13]劉麗星,張哲,杜蕊,等.中醫證候量表的研究現狀[J].遼寧中醫藥大學學報,2011,13(9):28 -30.
[14]張業,謝鳴.中醫方證關系研究的新思考[J].中醫雜志,2011,52(3):181-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