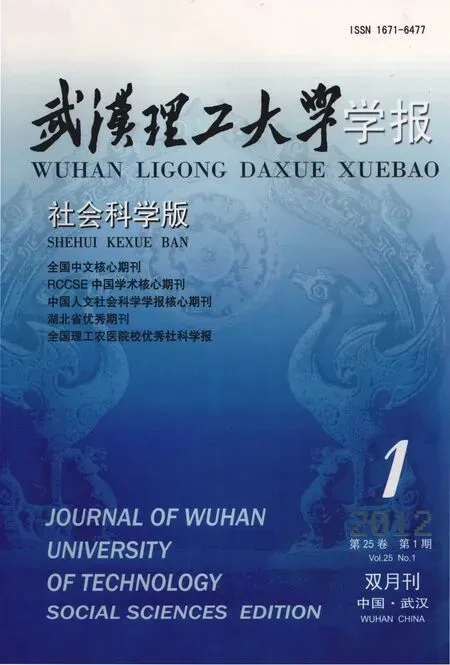中日雙邊服務貿易專業化程度及其影響因素*——基于產業內貿易視角
王恕立,劉 軍
(武漢理工大學經濟學院,湖北武漢430070)
進入21世紀以來,作為服務貿易大國的中日兩國服務貿易呈現出高速發展態勢,根據UN Service Trade Database公布的數據,2000年-2008年,中日兩國服務出口年均增長率分別達到了22.0%和10.5%,且WTO公布的《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9》顯示,2008年中日兩國服務出口分別位于第5和第6位,服務進口位于第5和第4位。同時,日本作為中國第4大服務貿易伙伴和進口來源地以及第3大服務逆差來源國,2000年-2008年,其對中國服務出口和進口分別以年均22.3%和10.8%的速度快速增長。可以看出,中日兩國服務貿易關系十分密切,再加上在地理、文化等方面的有利因素,使得兩國雙邊服務貿易存在極大的發展空間。深入分析中日雙邊服務貿易專業化程度及其影響因素,對兩國雙邊服務貿易的快速發展和中國服務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以及與日本服務貿易逆差局面的扭轉,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然而,目前國內外關于服務貿易專業化的相關研究文獻較少,Bobirca和Miclaus[1-2]在對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服務貿易競爭力進行研究時,采用貿易重疊指數(TO)分析了兩國與歐盟25國的服務貿易專業化結構。Grigorovic[2]運用Krugman專業化指數、Grubel-Lloyd指數及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CA)對羅馬尼亞與歐盟25國服務貿易專業化程度進行了分析。國內的相關研究則主要集中在中日服務業產業內貿易方面,比如崔日明和陳付愉[3],王濤和姜偉[4]及陳雙喜和王磊,都有論述[5]。而在服務貿易專業化方面,國內學者尚未涉足。鑒于此,本文采取UN Service Trade Database公布的相關數據,同時,考慮到多數服務企業在非完全競爭市場環境下運營而決定的,服務部門產業內貿易處于較高水平[6]的現實,本文在分析中日雙邊服務貿易現狀的基礎上,進一步基于產業內貿易視角對中日雙邊服務貿易專業化程度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一、測度方法及數據說明
(一)雙邊服務貿易現狀
1.服務市場融入程度。Marwah和Klein[7]提出了衡量一國在全球貿易中參與程度的貿易熵指數(trade entropy index,TEI),若一國擁有較高的貿易熵指數,則意味著該國貿易集中度較低,即世界貿易參與度較高;反之,則參與度較低。之后,貿易熵指數逐漸被應用于衡量一國通過貿易融入另一國市場的程度,如Simsek等的研究[8]。融入程度是深入分析兩國產業內或產業間貿易的基礎[9]。因此,本文將貿易熵指數進一步應用于雙邊服務貿易,對中日兩國通過雙邊服務貿易融入另一方服務市場的程度進行分析,其計算公式為:

2.服務業產業內貿易水平。Grubel-Lloyd指數是分析產業內貿易水平的一個常用指數,但該指數是對產業內貿易水平的靜態分析。Brülhart[10]提出了用于動態分析產業內貿易水平的Brülhart-B指數,該指數采取進出口增加額的方式來體現產業內貿易水平的動態變化。本文采取Brülhart-B指數來分析中日雙邊服務貿易各行業的產業內貿易水平,其計算公式為:

(二)雙邊服務貿易專業化程度
Finger和Rosa[11]提出了用于分析兩國貿易專業化程度的貿易重疊指數(trade overlap index,TOI),該指數是基于產業內貿易視角來衡量兩國的貿易專業化程度[1-3]。本文將運用貿易重疊指數來分析中日雙邊服務產業內貿易的專業化程度,其計算公式為:


(三)數據說明
本文分析所需相關數據的來源如下:中日雙邊服務貿易總體和各服務行業數據以及中日服務進出口總額數據均來自于UN Service Trade Database;人民幣兌日元匯率數據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2009》;中日服務業GDP數據、人均服務業GDP數據及人均國民總收入數據均來源于WB Database。其中,兩國人均服務業GDP數據采用各年服務業GDP除以當年人口得出;人口數據是按照WB Database公布的兩國各年GDP除以人均GDP得出。
二、雙邊服務貿易現狀及專業化程度
(一)雙邊服務貿易現狀
1.服務市場融入程度。采取貿易熵指數衡量的服務市場融入程度能夠較好地反映中日雙方對對方服務市場的滲透程度,是推進雙邊貿易快速發展的核心基礎。本文采取日本對中國各服務行業的進出口數據,得到日本對華服務出口和進口的熵指數,見表1。

表1 中日服務市場融入程度
可以看出,日本對華服務出口和進口熵指數呈現出截然不同的趨勢,其中,日本對華服務出口熵指數在2000年-2008年總體上呈現下降趨勢,說明日本通過服務出口對中國服務市場的融入程度逐漸減小;而日本對華服務進口熵指數在2001年達到最大值1.50后,在2002年-2004年間呈現下降趨勢,但自2004年觸底以來,直至2008年一直呈現上升趨勢。說明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服務出口對日本服務市場的融入程度呈現逐漸加深趨勢,為中國進一步擴大對日服務出口提供了較強的市場推動力。
2.服務業產業內貿易水平。已有的研究發現,產業內貿易是國際服務貿易的主要形式,因此,本文將進一步分析中日雙邊服務產業內貿易水平。表2給出了反映中日服務業產業內貿易水平的Brülhart-B指數。

表2 中日雙邊服務產業內貿易水平
可以看出,2000年-2008年間,中日雙邊服務貿易總體Brülhart-B指數為0.27,說明在長期中日服務業產業內貿易總體水平較高,雙邊服務貿易發展以產業內貿易為主。同時,從短期來看,除2000年-2001年Brülhart-B指數較大外,其他各年均較小,尤其是2004年-2005年,Brülhart-B指數只有0.09,說明短期內的中日雙邊服務貿易發展也以產業內貿易形式為主。
從服務業各行業來看,在長期上,運輸、旅游、其他商業服務及個人、文化及娛樂服務四個服務行業的貿易發展主要以產業內貿易形式為主,而其他服務行業的貿易發展主要以產業間貿易形式進行。但是,在短期內,除版權及許可費和政府服務的雙邊貿易呈現出較為明顯的產業間貿易特征外,其他服務行業的Brülhart-B指數波動較大,雙邊貿易發展形式表現的并不明顯。
從服務業各行業來看,在長期上,運輸、旅游、其他商業服務及個人、文化及娛樂服務四個服務行業的貿易發展主要以產業內貿易形式為主,而其他服務行業的貿易發展主要以產業間貿易形式進行。但是,在短期內,除版權及許可費和政府服務的雙邊貿易呈現出較為明顯的產業間貿易特征外,其他服務行業的Brülhart-B指數波動較大,雙邊貿易發展形式表現的并不明顯。
(二)雙邊服務貿易專業化程度
確定了產業內貿易是中日雙邊服務貿易的主要形式,本文進一步基于產業內貿易視角對中日雙邊服務貿易總體及各行業的貿易專業化程度進行分析,具體測算結果見表3。

表3 中日雙邊服務產業內貿易專業化程度
可以看出,總體服務業的TO指數在2002年出現微弱的下降現象,由2001年的0.61下降到2002年的0.59;之后2年則表現出強勁的上升趨勢,TO指數分別為0.62和0.68;且在2005年出現小幅下降之后,在2006年達到最高點,TO指數達到0.82;但2007和2008年又呈現出下降趨勢,TO指數均為0.7。總之,進入21世紀以來,中日雙邊服務貿易總體專業化程度較深且呈現出逐步加深趨勢。
具體到各服務行業,2000年-2008年,運輸及建筑服務的產業內貿易專業化程度較深;旅游及通信服務的產業內貿易專業化程度呈現快速深化趨勢,且在2008年旅游服務已完全實現產業內貿易專業化,通信服務的產業內貿易專業化程度也已達到0.95;保險、金融、其他商務服務及個人、文化及娛樂服務的產業內貿易專業化程度在2000年-2004年呈現出逐漸深化趨勢,但在2004年達到最高點之后,直至2008年,均呈現出下降趨勢;計算機及信息服務、版權及許可費及政府服務的產業內貿易專業化程度一直較低,說明這三類服務行業的雙邊貿易主要表現為產業間貿易專業化。
三、專業化程度影響因素實證分析
(一)變量選取及設定
在中日雙邊服務貿易專業化程度影響因素分析方面,本文分別從國家層面和產業層面選取服務貿易專業化程度的影響變量。國家層面選取兩國需求結構差異度、匯率及雙邊服務貿易開放度三個變量作為其主要影響因素;同時,選取服務業發展不平衡度、服務市場規模差異度、雙邊服務貿易差異度三個變量作為產業層面的主要影響因素。各影響因素的具體設定見表4。

表4 雙邊服務貿易專業化程度影響因素的選取及設定
首先,中日雙邊服務貿易總體專業化程度是在各服務行業專業化程度的基礎上,采用加權方式得出。其次,關于服務業發展不平衡度、服務市場規模差異度和需求結構差異度的計算,均是在采取Balassa[12]提出的用于衡量兩國經濟發展相對不平衡指數的基礎上,進一步采取不同的權重計算而得,其中,采取一國人均服務業GDP占兩國總人均服務業GDP比重作為服務業發展不平衡度的權重[13-19];
采取服務業GDP替代服務業發展不平衡度權重中的人均服務業GDP,此時Balassa相對不平衡指數可用來衡量服務市場規模差異度[13-19];采取一國人均收入占兩國總人均收入的比重作為Balassa相對不平衡指數的權重時,該指數又可以用來衡量兩國需求結構差異度[14]。再次,雙邊服務貿易差異度是將Fontagne等[15]提出的衡量產業內貿易產品差異指數應用于雙邊服務貿易而得出,該指數能夠同時考慮到貿易產品或服務的橫向和縱向差異。最后,雙邊服務貿易開放度是在兩國各自服務貿易開放度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入權重而得,權重是兩國在雙邊服務貿易中的出口占雙邊服務貿易總額的比重。
(二)計量模型構建
關于中日雙邊服務產業內貿易專業化程度的影響因素,本文已分別從國家層面和產業層面進行了選取和設定,在此進一步構建雙邊服務貿易專業化程度影響因素的實證檢驗模型,在構建模型過程中,由于多數變量數值小于1,故模型設定無法通過變量取對數形式來消除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只能在回歸過程中采取加權等方式進行消除,所構建的模型為:

式中:c為常數項;ut為隨機擾動項。
(三)回歸結果分析
本文實證檢驗運用計量軟件Eviews6.0進行分析,同時在回歸過程中采取White heteroskedasticity-consistent standard errors &covariance來降低異方差對模型估計結果的影響,估計結果見表5。根據回歸結果,模型修正決定系數達到0.930,說明模型能夠較真實地反映現實狀況。此外,除變量QI、EX和DI對TO的影響不顯著外,其他變量的P值均小于0.05,即都通過了5%顯著性水平檢驗。
具體來看,中日兩國需求結構差異度、服務業發展不平衡度及人民幣兌日元匯率對服務業產業內貿易專業化程度分別呈現正向、負向及負向影響效益,但影響效應不顯著。這是由于一方面,中日兩國在歷史、文化及空間方面的因素而導致兩國需求格局極為相近,需求結構差異度的增加能夠引起產品差異度的提高,從而促進產業內貿易的發生;另一方面,服務業發展不平衡度能夠影響兩國的資本-勞動比率差異度,差異度越大,產業內貿易水平越低。而在匯率影響因素方面,匯率變動對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復雜多變,故本幣匯率的升值并不一定會提升產業內貿易水平[16]。

表5 模型估計結果
在影響顯著的變量中,中日雙邊服務貿易差異度會對兩國服務業產業內貿易專業化程度產生顯著的負向效應,即隨著服務貿易失衡規模的上升,其產業內貿易水平會逐漸降低。中日雙邊服務貿易開放度和服務業市場規模差異度會對服務業產業內貿易專業化程度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應。一方面,服務業的貿易壁壘越高,則其產業內貿易水平越低;另一方面,由于多數產品的差異性是在規模報酬遞增的條件下實現的,市場規模差異度的增加能夠提升兩國產品的差異度,進而提高產業內貿易水平。
四、結論及啟示
本文基于產業內貿易視角對中日雙邊服務貿易專業化程度的相關研究,得出結論如下:其一,雙邊服務貿易現狀。首先,在服務市場融入程度方面,日本通過服務出口對中國服務市場的融入程度逐漸減小,而中國對日本服務市場的融入程度卻呈現逐漸加深趨勢。其次,不論從短期內還是長期上來看,中日雙邊服務貿易發展都以產業內貿易為主。其二,產業內貿易專業化程度。總體上來看,中日雙邊服務產業內貿易專業化程度較深,且呈現出逐漸加深趨勢;具體到各服務行業,運輸及建筑服務的產業內貿易專業化程度較深,旅游及通信服務的產業內貿易專業化程度呈現出快速加深趨勢,而保險、金融、其他商務服務及個人、文化及娛樂服務的產業內貿易專業化程度在近年來出現下降趨勢。此外,計算機及信息服務、版權及許可費以及政府服務的產業內貿易專業化程度較低。其三,專業化程度的影響因素。中日兩國需求結構差異度、服務業發展不平衡度及人民幣兌日元匯率對兩國服務業產業內貿易專業化程度影響不顯著;中日雙邊服務貿易開放度和服務業市場規模差異度則會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應,而中日雙邊服務貿易差異度卻表現為顯著的負向影響效應。
中日雙邊服務產業內貿易的主要形式以及專業化程度的逐漸加深揭示了兩國服務貿易結構具有較強的趨同性,同時也推動了兩國服務業產業內貿易的進一步發展。然而,在中國對日本服務市場融入程度日益加深的同時,中日雙邊服務產業內貿易主要集中在傳統的服務行業,如旅游、運輸等方面,在一些技術密集型服務行業,如計算機及信息服務、版權及許可費等方面,其產業內貿易專業化程度卻較低。對于中國而言,當前的中日雙邊服務產業內貿易狀況勢必會減緩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速度,且不利于中國服務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以及對日本服務貿易逆差局面的扭轉。因此,中國應采取更加積極主動的服務業及服務貿易發展政策。
在服務業發展方面,中國服務業發展體現出較為嚴重的行業不平衡性,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批發和零售業等傳統服務行業比重較大,2001年-2009年的增加值占服務業總增加值的平均比重達到33.3%,而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則較為滯后。中國應加大在傳統服務業的科技和人力投入,以保持傳統服務項目的原有優勢;同時,要拓展服務業新領域,通過在技術、管理、人力方面的突破以及構建良好的發展軟環境來創新服務業競爭優勢,發展技術密集型服務業,使其成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重要推動力。
在服務貿易方面,實證結果顯示,服務貿易開放度是中日雙邊服務產業內貿易專業化程度的最重要的一個影響因素。因此,應把握中日經貿發展的重要機遇,加強兩國在服務貿易領域的合作,逐步消除兩國服務貿易壁壘和投資壁壘,為中日服務業產業內貿易的發展提供廣闊的空間。此外,要形成以企業為主體的服務貿易行業協會,發揮行業協會在服務貿易發展中的促進作用,減少貿易摩擦,為中日服務貿易的進一步開放創造良好的環境。
[1] Bobirca A,Miclaus P G.A multilevel comparative assessment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services trad-e competitiveness:the case of romania and bulga-ria[J].World Academy of Science,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2007(30):1-6.
[2] Grigorovici C.Analysing the degree of specialization in romania’s services trade[J].Romanian Journal for Economic Forecasting,2009(6):94-114.
[3] 崔日明,陳付愉.中日服務業產業內貿易研究[J].國際經貿探索,2008(8):51-55.
[4] 王 濤,姜 偉.中日服務業產業內貿易問題實證研究[J].世界經濟研究,2010(6):51-56.
[5] 陳雙喜,王 磊.中日服務業產業內貿易實證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10(8):76-83.
[6] 程大忠.國際服務貿易: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7] Marwah K,Klein L R.The possibility of nesting south asia in asia-pacific economic integration[J].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1995(1):1-27.
[8] Simsek N,Seymen D,Utkulu U.Turkey’s competitiveness in the EU market:a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trade measures[J].Dokuz Eylülüniversitesi So-syal Bilimler EnstitüsüDergisi,2010(2):107-139.
[9] Lasser C,Schrader K.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changing trade patterns:the case of the baltic states[R].Kiel Working Paper,2002(1088).
[10] Brulhart M.Marginal intra-industry trade:measure-ment and relevance for the pattern of industrial adjustment[J].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1994(3):600-613.
[11] Finger J M,De Rosa D.Trade overlap,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protection[C]∥Herbert Giersch.On the Economics of Intra-Industry Trade,Tübingen,1979:213-240.
[12] Balassa B,Bauwens L.Intra-industry specialisation in a multi-country and multi-industry framework[J].The Economic Journal,1987(97):923-939.
[13] Andresen M A.Empirical intra-industry yrade: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need to know[R].NBER Working Paper,2003(5221).
[14] Sichei M M,Harmse C,Kanfer F.Determinants of south africa-US inter-industry yrade in services:a wild bootstrap dynamic panel data analysis[J].South African of Economics,2007(3):512-539.
[15] Fontagne L,Freudenberg M.Intra-industry trade:methodological issues reconsidered[R].CEPII Working Paper,1997(97-01).
[16] 張誼浩.匯率變動對產業內貿易影響的一個分析模型[J].世界經濟文匯,2003(3):1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