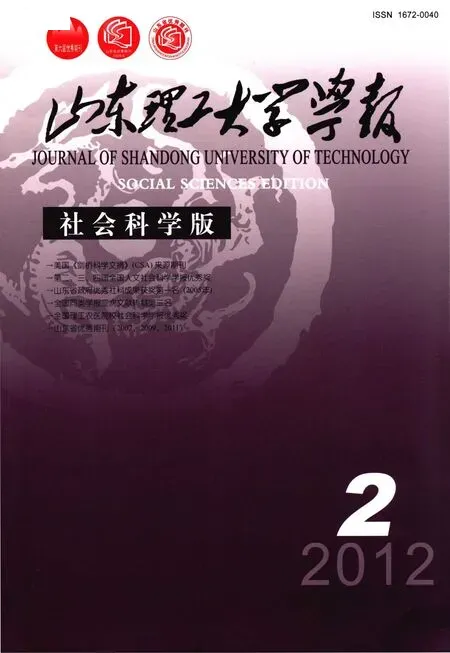媒體史敘事視角下的電視媒體“娛樂化”
張文潔
(山西財經大學文化傳播學院,山西太原030006)
一、媒體雙重控制體系的形成
在國家發展的不同階段,政府會有針對性地出臺相應的媒體政策。媒體制度的發展經歷了以下階段:計劃經濟時期,媒體是全民所有制下“國家經營的事業單位”;市場經濟時期“以公有制為主,多種經濟成份并存”經濟制度下,媒體是“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一業為主多種經營”。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一方面,媒體作為經濟個體的運行情況受到市場的制約;另一方面,媒體作為大眾傳播工具所具有的特殊政治功能又決定了其受到政府的制約。政府和市場從不同角度的新聞管理對媒體形成了雙重控制,市場控制下的媒體“娛樂化”以追求經濟效益,政府控制下的媒體“限娛”以追求社會效益。
二、電視媒體“娛樂化”的必然合理性
(一)媒體的經濟屬性在市場經濟體系中得到確認
伴隨著市場與消費主義的興起,媒體發展所需要的經濟來源經歷了從國家財政支持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轉變,媒體作為市場經濟中經濟個體的身份得到確認。市場經濟講求以市場需求為經濟發展導向,媒體的生存取決于其提供的產品與服務對市場需求的滿足程度,也即市場控制著媒體發展的命脈。
(二)市場控制論下對經濟效益的本能追求
社會學理論假設人類行為由社會和社會環境所塑造。[1]10按照這個觀點,作為社會運行中的個體,媒體的娛樂化亦是由其所處的社會與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媒體所處的社會背景與環境是解釋媒體“娛樂化”以及“泛娛樂化”的根本原因。
民粹主義的歷史敘事認為,媒體擺脫了精英文化的控制,重視市場的重要地位,市場促使媒體對大眾的需求作出更為迅速的反應,其將快樂和占有欲從少數人擴大到了普通大眾,媒體被轉變為大眾獲得娛樂的主要來源,這也是消費主義發展史的延伸。
媒介要生存,必然展開同業競爭,競爭的目標是受眾的注意力。在一個提倡休閑的時代,“泛娛樂化”是資本控制下信息全球化的必然產物。一方面資本的趨得性要求媒體最大限度的占有受眾;另一方面信息全球化的必然結果是信息的利益相關性降低。利益相關性直接影響到大眾的信息獲取動機,而娛樂是最能與最廣泛大眾(異質性階層)建立一定利益相關性的傳播內容。“媒介的命運取決于受眾選擇”,[2]迎合受眾的需求以獲得最多的受眾注意力從而實現經濟效益,是媒介生存的本能追求。人們要求媒體提供更多的娛樂,最終他們從媒體那里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娛樂。
三、“限娛”的合理性
(一)人類學、社會學角度語言對社會結構的構建作用
根據社會學、人類學的觀點,語言比任何其他的符號體系都更為全面地構建了我們的文化。一些語言學家和社會學家認為不同特征的語言對言語者看待世界的方式產生不同的影響。根據薩皮爾—沃夫[3]46假設推論①薩皮爾—沃夫假設是指語言間的區別不僅僅反映了言語者的需要和環境的影響,而且它們會對言語者看待世界的方式產生影響。,現實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群體語言習慣上無意識的構建而成。由于我們群體的語言習慣已預設了我們理解世界的方式,我們將會很自然地用這一方式去觀察、去聽、去感受事物,語言決定了我們對現實世界進行思考的方式。國家是一種文化建構,媒體在構建國家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媒體語言的“娛樂化”對社會形態、傳統價值觀的消解。
娛樂化的節目內容對社會大眾的議程設置發生了始料未及的重大影響。媒體的“泛娛樂化”不僅僅體現在娛樂節目的數量上,還再現在媒體的發展思路與發展風格中。從針對“娛樂化”提出的應對之策也被戲謔為“限娛令”,就可以看出“泛娛樂化”的思維與語言方式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娛樂化”節目的盛行對傳統的價值觀發起了挑戰。現階段中國國情下有兩種社會價值觀在主導人們的日常生活。一種是傳統的價值觀,要求人們艱苦樸素、奮發進取,強調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淡化個體意識;另一種則是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以個體獨立、追求自我的實現為導向的觀念,這種價值觀直接表現為人們對享樂主義的追求,對自我舒適度關注的增加,這種自我層面的追求與實現是個人主義的現代發展形式,導致人們對社會的集體目標缺乏關心。行為方式的變革是社會價值觀的外在邏輯結果,電視媒體的“娛樂化”恰恰是個體對自我滿足的過分追求。
通過對“泛娛樂化”一定程度限制,我們其實是對“娛樂化”語言完全建構社會的拒絕,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對傳統價值觀精華部分的維護。中國社會正在經歷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巨大發展與變遷,以娛樂化甚至低俗化為特征的媒介對傳統社會價值觀的沖擊、對轉型期社會結構穩定性的消解作用不容忽視。
2.政府控制論下媒體在“權力結構”中的特殊性,“娛樂化”造成了單向度的人,傷害了公共領域討論的可能性。
哈貝馬斯在對“公共理性”興衰的歷史敘述中指出,公共領域的結構在十八十九世紀經歷了一個結構上的轉變,以理性為基礎的公共生活受到破壞,現代媒體陷入了公共關系、廣告和大企業的的控制之中。“商業化的通俗文化能夠為大眾提供一種補償性的方式,使得那些處于社會弱勢地位的人能夠適應宰制性的社會秩序,并且從中得到放松、滿足和消遣”。[4]275-278新一代的大眾傳媒激發的是消費主義的冷漠癥,通過為受眾提供事先包裝好的、通俗易懂的思想,弱化甚至取消了其對社會存在的批判能力與批判精神,形成意識形態領域單向度的人。公共領域存在的前提是持不同觀念人群以追求公共福祉為前提、利用媒體針對公共問題展開公開的論爭,單向度的人則取消了公共領域討論的可能性,壓制了人們對現狀的否定和批判,而“娛樂化”沖擊嚴肅新聞地位,媒體使命感喪失,有違我國的新聞傳播政策。
在各種媒體制度下,都或明或暗地對報道實施政策控制,按照一定政治制度的要求,在創辦媒體、傳播內容和產品發行方式上形成規定,建立了體現社會統治權的媒體制度。結合我國具體的傳播政策,毫不避諱地說,“媒體是人民利益的衛士、是受眾的教員、是人民的教科書”。[4]283作為思想力量的提供者,“媒介應推動人類精神的變革以及由此帶來巨大的經濟變化”。[4]283媒體“娛樂化”的內容沖擊了嚴肅新聞的顯要地位,報刊、電視節目變成商品消費指南和“聲色犬馬”的“西洋景”,失去了新聞媒體的使命感。媒體從業人員、受眾、媒體批評家都越來越傾向于把媒體視作一種信息傳遞的工具,忽視它的思想屬性,忽視其思想與理性的抗爭。
四、多角度正確看待“娛樂化”與“限娛”
(一)“娛樂化”、“泛娛樂化”以及針對其不良影響提出的“批娛”、“限娛”只是中國媒體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然階段,是傳媒業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折射
從歷史發展的高度來看,“娛樂化”、“泛娛樂化”以及“限娛”都是媒體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宏觀而言都是媒體自身與社會環境互動產生的結果,是媒體從不成熟走向成熟迂回前進的過程。我們可以理解,電視媒體為了適應受眾的需求而產生“娛樂化”,但是縱觀“娛樂化”節目從產生到發展的生存狀態,即使沒有“限娛”以及與之相類似的行政干預手段,媒體的“娛樂化”也絕不會毫無節制地永遠發展下去。以曾經紅極一時的電視相親節目為例,除江蘇衛視《非誠勿擾》、湖南衛視《我們約會吧》依然保持較高的收視率外,一半以上的相親節目已經停播。對該類節目的批評與質疑之聲也不絕于耳,我們甚至可以由之推論,娛樂內容的泛濫亦是其自身走向衰退的信號。受眾的需求總是在不停的變化中,優勝劣汰的市場規則將催促媒體不停地尋找新的發展方向,一定程度上“泛娛樂化”是“去娛樂化”的征兆。
(二)“泛娛樂化”提示的不僅僅是娛樂類節目過多的問題,而是相對應的非娛樂類節目從質到量的“絕對弱勢”
對某一類媒體內容的發展現狀進行判斷,傳統標準將媒體時間同質化,忽視了媒體不同時間段不同的傳播價值與意義,而采用黃金時間段相關指標的比較則更具科學性。黃金時間段某一類節目的播出比重、收視比重以及二者之比可以反映出當下某類節目的情況。以CSM媒介研究對2010年度省級衛視各類節目收視情況的統計分析為依據,[7]我們將綜藝娛樂類節目與其他類節目進行比較。
根據表1、表2、表3的相關數據,對省級衛視不同周天各類節目的播出量進行分析如下。

表1 2010年省級衛視綜藝娛樂節目不同周天播出收視比重表(71城市,19:30-22:00)

表2 2010年省級衛視電視劇不同周天播出收視比重表(71城市,19:30-22:00)

表3 2010年省級衛視其他類節目(包括新聞/時事類)不同周天播出收視比重表(71城市,19:30-22:00)
省級衛視綜藝娛樂節目的播出和收視高度集中于周末,在一周多數的工作日綜藝娛樂節目僅占晚間19:30-22:00黃金時段節目量的7%,周五至周日的黃金時間綜藝娛樂節目播出量有所提升,但最高值僅為周六的20%。相較于電視劇最高值達到43%的播出比重,娛樂節目在量上并沒有明顯“泛濫”的趨勢。但包括新聞/時事類節目、生活服務類、教育類等在內的其他多種類節目總量在不同周天的黃金時間最高值僅為周一的50%,處于絕對弱勢的地位。非電視劇、非綜藝娛樂節目總量的弱勢必須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
收視與播出之比是單位播出量所獲得的收視量,反映了觀眾對節目的認可與接受程度,是對節目品質進行判斷的一個重要標準。比值高則相對應的節目受認可的程度要高。不同周天綜藝娛樂節目的收視與播出比結果變化不大,基本維持在2的高位,相比較而言,包括新聞/時事類節目在內的其他類節目整體的收視與播出比值卻僅有0.6左右,最高位為周一的0.68。
在其他變量基本相同的情況下,不同周天黃金時間段包括新聞/時事類節目在內的其他節目類型的收視與播出比值的明顯過低反映了其自身存在的品質方面的絕對弱勢。
同時根據CSM媒介研究對2010年主要節目類型節目資源使用效率的調查顯示:綜藝娛樂節目的資源使用效率最高達到57.2%,而新聞/時事類節目的資源使用效率為35.4%,電視劇的資源使用效率為12.1%,而生活服務類節目的資源使用效率為-45.8%。資源使用效率相當于企業運行中的投入產出之比,使用效率越低,對媒體的價值越低,甚至可能成為媒體發展的負擔,其發展必然陷入惡性循環,直至完全消失,這是非娛樂節目絕對弱勢的又一表現。
(三)媒體發展過程中,專業價值與市場價值之間的此消彼長
由于專業主義所倡導的能力和公正性受到了反復的攻擊,媒體專業主義的權威被削弱。專業主義也受到了日益擴張的市場和市場價值的侵蝕。媒體作為經濟個體,實施以市場為導向的管理體制,電視節目的制作越來越公式化,把新聞和時事節目推到了黃金時間的“邊緣地帶”。媒體機構的日趨中心化和雇用了越來越多的臨時工,導致了記者自主權的式微,同時也導致了編輯標準的下降和媒體公信力的進一步跌落。“泛娛樂化”則深刻體現了專業價值與市場價值的對立中一方的存在是以犧牲另一方為代價的現實,這種對立導致了媒體質量的整體下降。
(四)精神生產方式與精神文明是對物質生產方式與物質文明的反映
馬克思曾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5]82有什么性質的物質生產方式和物質文明,就有什么樣性質的精神生產和精神文明,反之,精神生產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反映了物質生產過程中的矛盾。媒體“娛樂化”作為精神生產過程中一個倍受爭議的現象,同樣反映出當前我國社會進行物質文化生產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社會貧富差距過大,人民生活壓力、生活成本過高,導致不同階層的人都尋求一種“解脫”與“逃避”的方式,繼而選擇沉浸在媒體創造的“娛樂化的擬態環境”中。
五、應對“娛樂化”的具體措施:監管與引導并舉
媒體的娛樂化、行政主管部門以及行業協會出臺的種種針對性的“限娛”措施,都是媒體在發展過程中利益相關者對媒體行業發展施加影響的正常表現,大可不必以洪水猛獸待之。在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精神的引領下,一方面,在政府的主導下,應該加快我國媒體問責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出臺有利于“非娛樂”類節目生存的優惠制度,從監管與引導兩方面入手,明確媒體的社會責任,正確認識娛樂節目的“相對強勢”,才能改變“非娛樂節目”絕對弱勢的局面,促進電視媒體的健康發展。
[1][美]戴維·波譜諾.社會學[M].李強,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2]瑞亞,陳梁.世俗背景下媒介娛樂化的必然性[J].媒介時代,2010,(10).
[3][美]詹姆斯·卡倫.媒體與權力[M].史安斌,董關鵬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4]劉建明.媒介批評通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