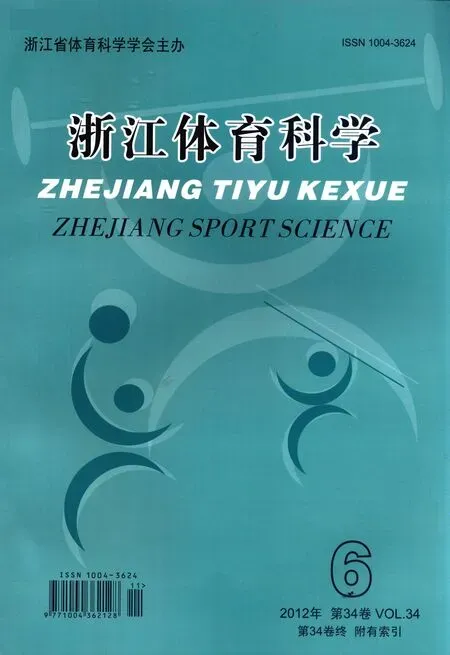論農村體育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民理性
傅振磊
(紹興文理學院 體育學院,浙江 紹興312000)
0 前 言
農村體育現代化隨著我國社會現代化進程而逐步推進,并屬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題中應有之意,時下又被列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主要內容,它在農村的移風易俗、改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質量方面發揮著巨大作用。換句話說,農村體育現代化是我國社會現代化進程中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實在過程。本文作者已先后發表《農村體育現代化商榷》、《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溯源》、《農村體育新解》以及《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變遷》等多篇論文,并對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的內涵、特征、起源以及發展變遷等相關問題進行了廣泛研究。然而,農民理性是我國兩千余年傳統農業文明的結晶,是農業社會賴以生存、發展的文化支柱,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關鍵問題。它既反映出中華民族的聰明智慧,又體現了我國農民的日常社會生產、生活狀態。在我國當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農民理性與農村體育現代化相遇,那么農民理性則必然將成為農村體育現代化研究所面臨的重要課題。鑒于此,本文循著此理論觀點與基本思路,進一步探索我國農村體育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民理性問題。
1 農村體育現代化的相關理論觀點
當提到農村體育現代化問題時,人們首先將它與高度發達的發展水平聯系起來,于是往往會產生“農村是否存在體育現代化、現階段提出農村體育現代化是否合適、農村體育能否實現現代化”等一系列疑問[2]。因此,就一般理解而言,農村體育現代化首先表現為一種結果,也就是特征屬性。然而,農村體育現代化也確實是我國現代化發展進程中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20世紀20、30年代,陶行知、梁漱溟等部分精英知識分子推動下的“鄉村建設運動”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蘇區體育運動”共同開啟了我國農村體育現代化之門。隨著我國現代化進程,尤其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逐步展開,農村體育現代化也相應地逐步推進。因此,農村體育現代化還表現為一個發展過程,也就是過程屬性[3]。本文作者在探索與研究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時全面考察了上述兩方面問題,并提出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是指在處于部分連接、未連接狀態的鄉級地域和村級地域以及常住人口不足3 000人或3 000人以上非獨立的各類特殊區域內,以農民為參與主體的群眾體育和競技體育所發生的轉型與動態發展過程。其變遷過程歷經“增強體質”與“提高生活質量”兩大發展階段,并具有組織管理民主化與法治化、社會功能世俗化與生活化、體育技術傳播知識化、體育設施多樣化以及體育格局和諧化等五大特征[4]。(讀者欲了解詳細內容,請參閱本文引言中所列出的相關文獻,此處不再贅述。)
2 農民理性及其作用
理性是什么呢?從哲學理論角度來說,理性是與感性相對應的,專指隱藏于紛繁復雜的各種現象背后的普適性規律,而且,這種規律能夠解釋客觀事物外在的現象、運動或變化。由此而言,農民理性可理解為農民對各種紛繁復雜事物或現象感性認識的加工,并最終達到理解和把握感性其運動和變化規律的過程。然而,農民理性更多的來自于農村社會現實生活。從社會現實生活角度來說,農民理性主要指農民通過自身及其前輩的生活經驗形成的意識、態度和看法,并體現于日復一日的日常生產和生活中所形成的各種諺語、口頭禪等日常話語之中[8]。從某種程度上說,它們是農民意識和態度更加直觀、形象的反映,屬于文化體系中的“俗文化”或“小傳統”范疇[9]。這種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哲理對農民的影響更長久、更深遠。因此,本文以此為切入點來分析農村體育現代化進程中,農民日常生活中的諺語、口頭禪等內容的作用與意義。
2.1 人情
我國傳統農業社會是一個“親情社會”和“熟人社會”。村落是我國農民生、老、病、死的發祥地,村落居民長期的緊密交往形成親情關系,比如:血緣關系、地緣關系等。就此角度而言,我國傳統農業社會還是一個“人情社會”,有時候人情甚至大于王法,因為人情可以給農民帶來信任、依托、互助等各種優越性。當農民遇到無法解決的問題和陌生環境時,首先想到的是可以信任、依托和互助的親戚、朋友和鄉鄰等這些所謂的“自家人”。
在傳統農業社會形態下,我國農村體育參與者主要局限于以同宗或同姓氏相聚居的村落成員,成員之間均為血緣、地緣等親情關系[1]。在這種人情關系社會背景中,體育參與者所出現的矛盾或糾紛基本上分為兩類:一類是前輩與后輩之間,另一類是同輩之間。前者一般在儒家倫理秩序控制下,后輩會敬畏前輩的權威而做出讓步,或以“大人不與小孩子一般見識”而了事;后者所產生的糾紛也會在親情關系或熟人關系調停下而出現緩和,再加上本族年長者出面調節,而且后輩們都會給長輩們一個“面子”。因此,這種人情社會關系內的矛盾或糾紛一般也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自近代社會以來,中國踏上了以“現代化”為標志的社會發展征程,村落與外界的聯系日益增多,而各地農民工相互流動又進一步加劇了農村地區各村落地域之間的相互聯系。農村體育參與者不再局限于具有血緣關系或親情關系的“自家人”,而是增加了“外來者”,出現了“主”、“客”角色,其矛盾或糾紛也出現了新類型。以儒家學說所倡導的天、地、君、親、師的倫理秩序和“三綱五常”的倫理控制在這種新矛盾或糾紛面前黯然失色,家族或宗族中年長者的“面子”也顯得分量不足。因此,在處理族群內部成員與外部成員之間關系時需要一種新型的方式:契約管理與法律管理。
與現代化社會發展相適應,中國農村體育發展也呈現出現代化需求,在農村體育現代化進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趨于復雜,傳統的倫理關系和倫理控制經常無法解決或調解其關系糾紛,而倫理控制轉向契約控制、法律控制則成為歷史發展必然。然而,中國農民的“人情理性”也是幾千年傳統文化長期積淀的結果,實現轉變并非一蹴而就,而且,在當前階段,這種“人情理性”依然影響著我國農民的社會生活。但無論怎樣,“人情理性”與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需要相背離是現階段中國農村體育發展的現實,盡管在一定歷史時期能夠繁榮中國農村體育,但在處理農村體育過程中紛繁復雜的人與人的相互關系時,農民的“人情理性”卻阻滯了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進程。
2.2 勤勞
勤勞是指辛勤的勞動,將勞動視為生活的源泉,也是人生最重要的價值,它是農民理性的最基本要素。傳統農業社會的生存主要依賴土地和勞動兩大生產要素,然而,土地相對有限,生產的增長不得不主要依靠勞動投入,即勞有所得。勞動不僅是生存的目的,而且成為一種人生的態度,是人的一項神圣天職。特別是在人多地少的中國,更需要通過不斷的勞動投入才能得以生存。“勤勞苦做”、“起早貪黑”是高尚的、為人稱道的行為;而“游手好閑”、“好吃懶做”、“偷懶耍滑”則是不符合傳統道德要求,屬于被農民所鄙視的行為。
我國農村體育涵蓋兩部分內容,一是以我國傳統文化為核心的傳統農村體育,二是以西方外來文化為代表的現代農村體育[6]。傳統農村體育在我國歷史上已存在很長歷史階段,在勤勞的中國農民看來,它是在特定時節所舉行的祭祀、慶祝儀式,屬于祖宗遺留下來的、不可更改的規矩,而且,在祭祀、慶祝儀式上,絕大多數人也只能給能工巧匠們做觀眾或看客,不可能讓他們人人參與。農民將辛勤的體力勞動與現代農村體育看作一回事,都可以起到增強體質、鍛煉身體的作用,經常參加體力勞動,沒有必要再參與現代體育活動[10]。另外,從我國農民傳統思維角度,農村體育與絕大多數辛勤的體力勞動者無關,農村體育的參與者要么是能工巧匠,要么是非體力勞動者。他們將參與農村體育活動的行為稱為“不務正業”、“偷懶耍滑”或“游手好閑”,屬于不符合傳統道德要求的、被鄙視的行為。然而,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則要求農村體育社會職能世俗化和生活化,即農村體育不再只是節慶日上的宗教祭祀、慶祝儀式,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利,而應屬于絕大多數農村社會成員日常生活應有內容。由此看來,中國農民的“勤勞理性”將農村體育現代化需求排斥于農民的日常社會生活之外,使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進程步履維艱。
2.3 經驗
經驗是指農民在長期的農業生產和社會現實生活中所積累的精神財富。人們將其編成歌謠、順口溜或諺語,用以指導農業生產和社會現實生活,比如:白露早、寒露遲、秋分種麥正適時,冬天麥蓋三層被、來年枕著饅頭睡,冬吃蘿卜夏吃姜、不用醫生開藥方,飯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等。在農業生產和社會現實生活中,前輩通過榜樣示范和口授的方法將農業生產和生活經驗傳授給后輩,而后輩也在潛移默化、耳濡目染中了解和掌握了前輩們的生產生活經驗,而且,在農民看來,這些經驗是亙古不變的絕對真理。后輩遵從祖宗、前輩的旨意將會受到人們的大加贊賞,并冠之以“孝”道的美譽;若不聽前輩教導、違背前輩經驗而一意孤行、我行我素則被扣上“叛逆”或“大逆不道”的罪名。
在中國傳統農業社會,“天、地、君、親、師”處于倫理秩序的最高層次,而“師”的地位僅次于“天、地、君、親[6]”。若向某人學習技藝,需在正規、嚴肅的場合下,以莊重的態度行“拜師禮”,自此,師傅與徒弟的關系正式確立,并遵從師徒倫理。師傅的責任是傳道、授業、解惑,而掌握師傅所傳授的技藝則成為徒弟的義務。在農民看來,體育本質上也就是身體活動的經驗,比如:博大精深的中華武術、中醫領域的康復治療手段以及具有傳統文化色彩的某些技藝表演,這些都是經過前輩或師傅將自身練習的經驗和感受發掘、整理后,通過“師傅帶徒弟、徒弟再帶徒弟”的順向方式代代相傳,而在前輩或師傅的身體活動中耳濡目染也就成為后輩獲得身體活動經驗的主要途徑。前輩或師傅掌握著體育的“源”,處于壟斷、權威地位,其技術造詣與修煉水平也遠遠高于徒弟,后輩或徒弟若要“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只能靠自身的悟性,“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便是其真實寫照。千百年來,中國農民一直信奉著這一幾乎永恒的體育技術傳播方式。然而,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則要求體育技術傳播知識化,即傳播體育技術的人應具有專門體育知識,并經過專門訓練;傳播體育技術的途徑也應以報刊、廣播、電視以及互聯網等現代化方式為主流。顯然,中國農民的經驗理性與農村體育現代化要求不一致,并阻礙了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進程。
2.4 節約
生產和消費是農民日常社會生活中的一對矛盾統一體。如果說農民理性在農業生產方面表現為勤勞,那么在消費方面則表現為節約,盡量壓縮開支,即將消費支出降低到最低限度。在傳統農業社會,農業生產收益非常有限,農民不可能拿出較多的財富進行消費。在農民的日常社會生活中,生產和消費是一體的,節約也就意味著財富積累,即增收。同時,由于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下,農業生產受自然環境的影響很大,豐歉難保,而且,農民又沒有其它的生活保障,他們只能依靠自己的日積月累進行自我保障,由此形成農民的節約理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家庭生活水平有了較大幅度地提高,這是無可爭議的。然而,農民的節約理性仍在發揮作用。上世紀90年代,國家統計數據顯示,我國農村家庭收入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于是,有研究者就提出“體育市場化”、“體育商業化”的觀點,進入新世紀以來,國家又發布了多項與體育產業相關的法律法規,鼓勵體育市場化和體育產業化發展[7],然而,我國農民體育消費卻仍處于較低水平,農民不愿意花錢購買體育服務和體育設施。究其原因,我國尚未建立起完善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農民基本上更是沒有多少保障,他們必須依靠自身的力量尋求正常的生活保障,將消費限制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也就是農民經常掛在嘴邊的“吃飯穿衣量家當”。
在農民看來,體育設施屬于額外消費品,與柴米油鹽等生活必需品不可同日而語,也不能與教育、醫療那些與他們生存、發展息息相關的領域相提并論,因為這些東西在農民日常生活中尤其重要。在無外源性收入情況下,農業生產收入非常有限,農民不得不統籌規劃有限收入,使其效用最大化,有或沒有體育設施,他們都有辦法解決自身的體育需求問題,或以其它活動替代,或選擇那些無需設施的農村體育。就算是富裕階層,寧愿將資金投入到再生產,以錢生錢,或更多的儲蓄以應對不測,也不愿花錢購置體育服務或體育設施,許多豪華健身俱樂部門可羅雀,足以證明了這一點。長期以來,我國農民一直維持著無體育設施或僅有簡單體育設施的農村體育發展現狀,或者農民對體育設施的要求不高,或者能夠忍耐農村體育設施的缺乏,這些均與我國農民的節約理性有關。然而,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則要求“體育場地設施多樣化”,以滿足中國農民日益增長的、多樣化的體育需要。很顯然,中國農民的節約理性與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要求產生了沖突,限制了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的進一步推進。
2.5 忍受
在傳統農業社會,我國農民的所生存的環境極其復雜,既要應對來自變幻莫測自然環境的挑戰,又要面對來自統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在復雜的生存環境下,他們學會了忍耐,學會了逆來順受。無論在什么樣的生存環境下,他們總能夠找到適合自身生存的空隙。
農村嚴重缺乏體育設施、農村體育缺乏指導以及農村體育缺乏組織領導等已成為我國現階段所公認的農村體育現實。然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我國農村并不缺乏體育,而是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前者以城市體育為參照,以現代體育為內容所得出的結論;后者則以我國傳統村落為參照,以傳統體育為內容而得出的研究結果[4]。至于,在我國廣大農村地區體育格局的真實現狀則無法體現出來,因為已有相關數據缺乏這方面的調查與統計。依據相關文獻資料所述,我國農村地區的現代農村體育與傳統農村體育發展不均衡,要么傾向于現代農村體育,要么傾向于傳統農村體育,然而,我國農民對此卻表現出“無所謂”的漠然態度。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則要求農村體育格局和諧發展,二者互相促進、互相補充,不能相互替代,而和諧程度、和諧標準應以長期生活在農村的農民的親身感受和需求為依據。由此看來,中國農民的忍受理性已使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的體育格局和諧發展失去了可參考的、來自農村一線的民聲訴求,以至于迷失了明確的發展方向,而成為政府體育管理部門和體育學術界一廂情愿的事情。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農民的“忍受”理性對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的發展都是極其不利的。
3 結 語
農民理性與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發展充滿了重重矛盾,人情理性制約了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的法制化進程;勤勞理性使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的社會職能難以世俗化、生活化;經驗理性對中國農村體育技術傳播知識化不利;節約理性限制了中國農村體育設施多樣化的現代化需求;忍受理性使中國農村體育格局和諧化發展失去了明確的方向。然而,這并非絕對,理性是特定環境的產物,其內容、形式和功效十分復雜。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逐步推進,農民理性也在發生著微妙的變化,法治理性、科學理性、消費理性、知識理性以及人權理性等現代化理性越來越得到我國農民的認可與追求,它們也必將在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進程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1]陳勁松.儒學社會通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229.
[2]傅振磊.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之商榷[J].浙江體育科學,2010,32(2):5-12.
[3]傅振磊.我國農村體育現代化溯源[J].浙江體育科學,2011,33(2):4-6.
[4]傅振磊.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內涵與特征研究[J].體育科研,2010,31(6):88-91.
[5]傅振磊.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研究[D].蘇州大學,2011.
[6]郭修金,虞重干.從村落看村落體育[J].上海體育學院學報,2008,32(3):1-6.
[7]呂康娟,郭偉.上海農村體育發展戰略研究[J].體育科研,2008,29(4):29-38.
[8]徐勇.農民理性的擴張:“中國奇跡”的創造主體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10,181(1):103-118.
[9]鄭萍.村落視野中的大傳統與小傳統[J].讀書,2005(7):11-19.
[10]田雨普.農村體育研究中“農村”含義的辨析[J].體育文化導刊,2005(10):4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