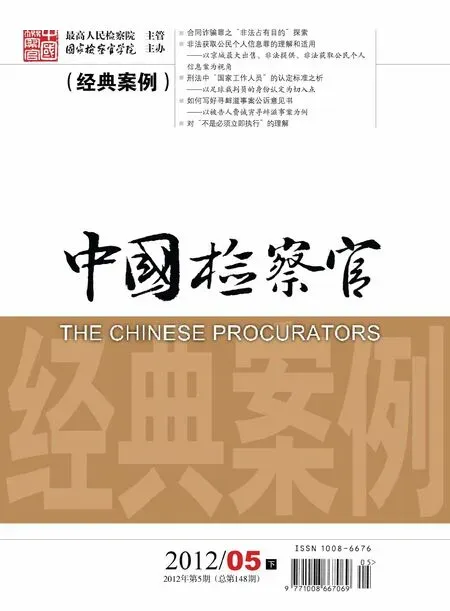刑法中“國家工作人員”的認定標準之析以足球裁判員的身份認定為切入點
文◎程國棟李秦英羅至曄
刑法中“國家工作人員”的認定標準之析以足球裁判員的身份認定為切入點
文◎程國棟*李秦英**羅至曄**
[案例一]被告人龔建平于2000年至2001年期間,受中國足球協會(以下簡稱“中國足協”)指派,擔任全國足球甲級A、B組聯賽主裁判。在此期間,龔建平利用職務之便,先后9次非法收受參賽方青島頤中海牛、上海申花、浙江綠城、大連實德、山東魯能、江蘇舜天足球俱樂部給予的財物,共計人民幣385 000元。北京市宣武區人民檢察院以京宣檢經訴字(2002)第41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龔建平犯企業人員受賄罪,于2002年12月19日向北京市宣武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2003年北京市宣武區人民法院以受賄罪判處龔建平有期徒刑十年、沒收贓款三十七萬元([2003]宣刑初字第32號)。被告人龔建平對判決不服提起上訴,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2003)一中刑終字第345號作出終審裁定,駁回龔建平上訴,維持原判。[1]
[案例二]2012年2月16日,遼寧省丹東市中級人民法院,對社會廣泛關注的一批涉足球犯罪案件作出一審判決。其中,被告人陸俊、黃俊杰、周偉新、萬大雪分別利用其執裁足球比賽的職務之便,為相關足球俱樂部及相關人員謀取不正當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被判處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同時周偉新為謀取賭球贏利等不正當利益,對黃俊杰等4名足球裁判員行賄被判處對非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行賄罪。[2]
一、問題的提出
同樣是秉執球賽輸贏大權的裁判員,同樣是利用裁判的職務之便,為相關足球俱樂部及相關人員謀取不正當利益,并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法院在對龔建平與陸某等四位裁判的身份認定上作出了截然不同結論。案例一中,雖然宣武區人民檢察院在起訴書中則龔某認定為非國家工作人員,但宣武區人民法院與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認為被告人龔建平是國家工作人員,因而認定其構成受賄罪。案例二中,丹東市中級人民法院亦將陸俊等四人認定為非國家工作人員,因而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對其定罪量刑。
值得一提的是對裁判身份的不同認定在定罪量刑方面所帶來的巨大差異。根據《刑法》第163條第1款之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而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根據《刑法》第386條之規定,對受賄罪的處罰按照刑法第383條貪污罪的規定處罰。根據第383條第1款之規定,個人貪污數額在十萬元以上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情節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可見,兩罪在量刑上的差異之大,同時也是明晰這一問題的意義所在。
二、足球裁判人員的身份認定分析
根據對裁判人員身份的不同認定,理論學界與司法實務界對上述案件的處理主要存在以下三種不同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裁判人員的上述行為不夠成犯罪。原因在于,中國足球協會雖然是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人民團體,裁判也必須要服從中國足協的管理,向其交納注冊費,但其實質上是一種典型的行業管理關系,并非上下級的行政隸屬關系。而且,足球裁判員并非中國足協的在編人員,而是受到中國足協的臨時約請或者指定,擔任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的裁判工作,他們可能來自不同的公司、企業、高校、人民團體等,在比賽結束后,仍要回到原單位繼續原來工作,因此他們與中國足協之間只是經濟合同關系。最主要的是,無論是球員還是裁判,都是按照事先設定好的比賽規則進行的,裁判與球員只是在比賽中的具體分工不同,而無論是比賽規則的設置還是裁判人員的安排都是由中國足協進行的,因此裁判活動并不具有“公務性”。因此,裁判不屬于刑法規定的國家工作人員,同時由于中國足協不屬于公司、企業,因此足球裁判人員在比賽中,不具有公司、企業人員的性質,故不能以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論處。[3]綜上,對上述裁判人員的行為不應該認定為犯罪。[4]
第二種觀點認為,上述行為構成受賄罪,其立足點在于上述裁判人員應該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理由在于,裁判人員屬于中國足協工作人員,而按照《體育法》的相關規定,國家授權中國足協對足球運動進行行業管理,顯然具有公共事務(即公務)職能。足球裁判對比賽的裁判活動實際上是代表足協而非個人,對足球競技進行評價(判定勝負),其實質是足協行使對足球運動的行政管理職能的組成部分,當然是在從事公務活動,因此應當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5]
第三種觀點認為,上述行為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其立足點在于上述裁判人員不屬于國家工作人員。理由在于,如同第一種觀點所述,裁判人員從事的不是公務活動,不屬于國家工作人員,裁判臨時受聘于中國足協,可以認為是中國足協的工作人員,其裁判活動可以視為是代表中國足協執法,而非代表個人,因其并非國家工作人員,因此可以視為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其利用執掌裁判活動的職務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應認定為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6]
筆者認為,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受賄罪”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兩種觀點上,其實質仍然是對足球裁判的身份認定這一問題。筆者贊“受賄罪”的觀點,即認為裁判人員在進行裁判活動時應該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但是在認定理由上與上述觀點略有不同。筆者將在下文詳細論述,首先提出的是對“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這一觀點的質疑。因為根據刑法第163條第1款之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是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也就是說要該當此罪必須具備“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工作人員”這一主題要件,反之,如果不是“單位的工作人員”也就不能該當該罪的犯罪構成。然何為“單位的工作人員”?筆者認為,從字面意思理解可以作以下兩種解釋:第一,例如甲為某高校的體育教師,同時具有裁判資質,受到中國足協的臨時約請,擔任幾場球賽的主裁判。因為甲的編制與人事關系都在高校,因此可以認為甲是“單位的工作人員”;第二種解釋是,這里的“單位的工作人員”,必須是中國足協的這一單位的工作人員,因為甲作為裁判在執行裁判活動期間,是利用其擔任比賽裁判的職務之便,收受他人財物的,與其之前的工作單位并無關系。因此這里的單位必須是委托其從事某項職務活動的單位,具體到案件中要求具備“中國足協這一單位的工作人員”的主體要件,也就是說該罪的構成要件中,強調主體的單位性。顯然,第一種解釋是不合理的,因為足球裁判一般都是兼職人員,其本職工作可能是大學教師和國家干部,也可能是公司職員和企業工人,也可能是自由職業者。在職業足球聯賽中,他們是受中國足協的委托或委任,擔任裁判職務的,與其本職工作沒有多大聯系,因此不能作為認定其擔任裁判期間受賄行為主體的根據。[7]
接下來我們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足球裁判員是否屬于中國足協的工作人員?也就是足球裁判與中國足協之間的關系問題。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第29條之規定,“全國性的單項體育協會對本項目的運動員實行注冊管理”。第31條之規定,“全國單性體育競賽由該項運動的全國性協會負責管理”。同時,按照《中國足球協會章程》第3條之規定,中國足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從事足球運動的單位和個人自愿結成的唯一的全國性的非營利性社會團體法人。第60條之規定,足球裁判員須按照規定每年參加年度培訓、按規定繳納注冊費,在規定時間內報協會注冊、備案等。由此可見,在我國中國足協負責對足球活動的組織與管理工作,享有與足球運動相關的管理權、處罰權與對外代表國家的權力。基于法律與國家的授權,其對足球有關的競技活動與足球會員的處理等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因此它是對中國足球活動具有管理職能的人民團體。足球裁判是中國足協的注冊會員,按照規定參加會議、接受培訓,并按時交納注冊費,中國足協與足球裁判之間的關系是行業內的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足球裁判并非中國足協的在編人員,其編制與人事關系不在中國足協,因此不能因為其從事幾場足球裁判活動便認為其是中國足協這一單位的工作人員,如同律師與律協之前的關系,不能因為律師參加了全國或者地方律協組織的法律宣傳活動,便認為其是律協的工作人員。[8]
經過上述論證,我們不難發現,足球裁判不具備中國足協的工作人員的特征,同時因為其從事的裁判活動與本職工作沒有聯系,因此也不能認定為其本職工作單位的工作人員,也就是說不符合“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工作人員”的主體身份要件,因此不能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論處。
那么足球裁判是否可以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理由何在?筆者認為在對此進行論述之前,需要明確“國家工作人員”的認定標準問題。
三、“國家工作人員”的認定標準辨析
筆者在這里僅就與足球裁判身份認定有關的,“準國家工作人員”中的“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這一具體問題進行闡述。明晰“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的認定問題,首先要厘清國家工作人員范圍的認定問題,即以什么標準作為國家工作人員的認定標準。對此,主要存在以下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國家工作人員犯罪是一種身份犯,當然要強調身份的重要性,故國家工作人員需要具有國家工作人員或者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的身份,這是其從事公務的前提,所以在界定國家工作人員范圍時,應以其是否具有一定的身份與資格作為認定標準:第二種觀點認為,“從事公務”是國家工作人員的本質特征,一定的人從事公務,就使得這些人獲得相應的特定身份,只要這些人員通過特定的公務活動體現了國家管理職能,這些人就可以被視為國家工作人員。[9]第三種觀點認為,上述兩種觀點皆有失偏頗,在界定國家工作人員的范圍時,應該將“身份”與“公務”結合起來,綜合進行判斷。[10]
第一種觀點將身份與資格作為認定國家工作人員的標準,固有其合理之處,但司法實踐中存在諸多問題。第一,身份認定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我國正處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轉型的過程中,與之相伴的是政治體制的改革,計劃經濟體制下存在的很多企業、機構、組織的性質復雜、繁瑣,很多情況下難以界定,司法工作人員花費大量精力與資源于此,有違司法經濟之原則。同時,在轉型過程中,很多企業或者單位的性質出于不斷變動的狀態,很可能一紙政令或者一則政策出臺即發生變化,存在不確定性,與法律的相對穩定性的原則相違背;第二,有違法律公平性原則。例如甲乙皆為足球裁判,甲是某公辦高校教師,乙為民辦高校教師,如果單以身份論,甲享受事業編制,是國家公務人員,而乙則不是。甲乙二人在足球比賽中利用裁判職務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賄賂。在情節相同的情況下,甲因為具有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可能被判處受賄罪,而乙因為其所在高校為民辦院校,則被判處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如此認定,恐難以為國民所接受;第三,存在遺漏犯罪的嫌疑。如果裁判甲原為某公辦高校體育教師,此后辭去工作,出于未就業狀態,此時受中國足協委托擔任某場球賽的裁判員,期間利用職務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此時,行為人既非國家工作人員又非其他單位工作人員,故難以對其定罪量刑。
第三種將“身份”與“公務”結合起來綜合認定的觀點是為折衷說。該觀點在司法實踐中固然可以處理所有的問題,因為實踐中若非身份認定的問題,即為公務認定的問題,但實際上并沒有統一的認定標準,而是由法官進行自由裁量,不僅會帶來同案不同判的問題,而且還會帶來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濫用,實不可取。
第二種觀點,即“公務說”的觀點為筆者所贊成。原因在于:第一,從公務性的本質特征把握國家工作人員,較從身份與資格方面來把握,更為簡易也更具可操作性;第二,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通過的《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這一立法解釋,農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協助人民政府從事法律規定的行政管理工作時,屬于“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可見這里“從事公務活動的人員”的認定,不要求以具備特殊資格或者身份為前提,而是根據其從事公務活動進而賦予其國家工作人員的主體身份。因而,只要行為人所從事的活動具有公共事務管理、監督、領導方面的特征,就可認定其為國家工作人員,這樣就避開了從單位、企業等主體資格來認定所帶來的難題;第三,從社會發展的目標長遠來看,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完善,中立的社會第三方的完善成熟,未來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公權力會觸角會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逐漸收縮,很多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職能會移交給社會第三方,例如行業自治組織,NGO(非政府)組織等來完成,而且隨著體制改革的進一步完善,計劃體制下的很多產物會逐漸淡出公眾視野,在此背景下,以事公務活動作為認定國家公務人員的依據,具有長遠性與穩定性,也更能發揮該罪的應有功能,更有效地遏制職務犯罪。
四、揭開足球裁判員的身份面紗
明確了國家工作人員的認定標準,接下來就要揭開裁判員身份的面紗了。筆者擬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第一,中國足協的性質。正如上文所述,中國足協是管理全國足球運動的全國性協會,是國家體育總局的下設機構,屬于國有事業單位。根據法律規定與國家授權,中國足協對全國足球行業具有行政管理職能。
第二,中國足協與足球裁判員的關系。即裁判接受中國足協的臨時約請擔任足球賽事裁判由此所產生的中國足協與足球裁判之間的關系。中國足協既然負責對全國足球運動的管理事務,當然有權組織全國性的足球體育賽事,如中超聯賽等比賽,當然也有權根據相關比賽規則對比賽的勝負進行裁決。但中國足協是抽象的團體,其裁判權交由具有一定資質的裁判人員進行,既符合相關規定,也更有利于比賽活動的展開,因為足球裁判是比較專業的職業,須由熟悉比賽規則并獲得相應資質的裁判來勝任。中國足協在足球比賽活動中,按照相關規定,將比賽勝負的裁判活動交由裁判來執行,相當于將比賽的勝負裁決權交由裁判執行。這樣就在中國足協與裁判之間形成了一種委托關系。同時筆者認為這種委托關系的依據可以是法律,也可以是規章或者制度、章程等,只要符合相關規定的條件與程序即可,不一定僅為法律授權。例如村民委員會等農村基層人員協助人民政府從事救災、搶險、防汛等行政管理工作時,未必有法律明確規定,只要是人民政府按照相關條件與程序授權即可。同樣,中國足協按照其章程規定,將比賽裁判權委托給裁判,當然有效,也在兩者之間形成了委托與受托關系。
第三,足球裁判活動的性質。足球裁判員負責維持賽場秩序,跟進整個比賽的進程,并根據比賽規則對比賽活動進行裁決,裁判員不僅對爭議的比賽活動有作出判決的權力,而且對違規的球員有判罰權等,這些活動都是體育賽事的監督與管理活動。而公共事務不僅僅是國家事務,還包括社會事務、集體事務等,內容覆蓋政治、經濟、文化、體育、教育、衛生等各個方面。對足球比賽這一體育活動的管理與監督屬于社會事務,也是公共事務的組成部分。雖然裁判是按照中國足協設定的規則進行裁決,但不可否認的是裁判員在規則規定的范圍內掌握著一定的裁量權,而這也是其權力尋租的空間所在,不能單單因為其依照比賽規則進行裁判就否認其公務性。
綜上,我們認為上述案例中的裁判應該被視為“其他依照法律規定從事公務的人員”,即準國家公務人員。需要強調的是,對足球裁判員不能一概都認定為國家公務人員,應結合比賽的性質與委托單位的性質來進行判斷,例如兩所高校之間組織的比賽中的裁判員便不能被認定為這里的國家工作人員,而由中國足協組織的全國大學生足球聯賽則不然。因此首要的條件是其裁判活動是否具有公務性,裁判人員國家工作人員資格是基于其從事公務活動而被賦予的,而對其公務性的判斷又需要結合委托或者派遣單位的性質進行判斷,因此三方面的條件缺一不可。
注釋:
[1]參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編:《刑事審判參考》(總第31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243頁。
[2]華春雨、楊維漢:《遼寧丹東中院16日一審宣判一批涉足球系列犯罪案件》,載新華網http://news. xinhuanet.com/legal/2012-02/16/c_122710798.htm,2012年3月19日訪問。
[3]該罪已于2006年6月29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六)》第七條所修改,擴大了本罪的主體,增加了“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的規定,也就是現在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故關于該點的爭議已不存在問題,爭議的焦點集中在其是否為國家工作人員這一問題上。
[4]王作富、田宏杰:《“黑哨”行為不以犯罪論處》,載《政法論壇》2002年第3期。
[5]謝望原:《“黑哨”、“黑球”與“傷熊”行為的刑法學思考》,載《政治與法律》2002年第6期。
[6]參見李建玲:《足壇“黑哨”刑法定性探析》,載《上海體育學院學報》2008年第2期。
[7]何家弘:《足球“黑哨”問題之我見》,載《法學雜志》2002年第2期。
[8]同注[4]。
[9]趙秉志主編:《中國刑法案例與學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頁。
[10]江禮華:《論國家工作人員范圍的界定》,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1998年第4期。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2010級刑法學碩士研究生[100089]
**河南省鄭州市金水區人民檢察院[450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