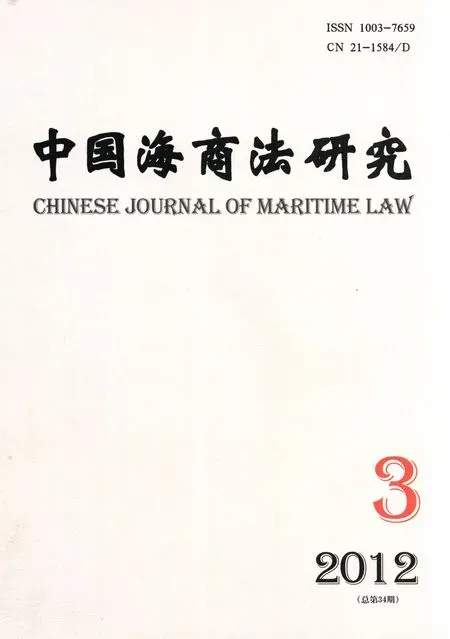中國在北極的國際海洋法律下的權利分析
韓立新,王大鵬,2
(1.大連海事大學法學院,遼寧大連116026;2.大連海事大學航海學院,遼寧大連116026)
隨著全球變暖,海冰逐漸融化,一直處于封閉狀態的北極地區,在航運、漁業和石油天然氣開發等方面所呈現出的巨大商業和戰略價值使其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
相較于《南極條約》近半個世紀的成功運行,北極地區是一個多維的國際法規制對象,各種國際公約紛紛涉足。目前,北極地區的法律規制包括四個層次:一是全球層面的國際公約。典型的有《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簡稱《海洋法公約》)。作為世界海洋秩序的“憲章”,基于其適用范圍的普遍性,北極當然成為《海洋法公約》調整對象。[1]二是多邊層面的制度安排。如1920年由挪威與英國、丹麥、荷蘭、瑞典等多個國家共同簽署的《斯瓦爾巴德條約》(又稱《斯匹茲卑爾伯根群島條約》)、1990年由加拿大、丹麥、芬蘭、冰島、挪威、瑞典、美國和前蘇聯共同簽訂的《國際北極科學委員會章程》(又稱“八國條約”)、2008年挪威、俄羅斯、丹麥、加拿大和美國首次就北極問題召開部長級會議并通過的《伊魯利薩特宣言》等。三是雙邊層面的制度安排。例如1988年美國和加拿大簽訂的《北極合作協議》、1994年美國和俄羅斯簽訂的《美國政府和俄羅斯聯邦政府關于防止北極地區環境污染的協議》、1998年挪威與俄羅斯簽訂的《環境合作協議》等。[2]四是環北極國家針對其“理論上所轄北極水域”①部分環北極國家的主張與現行國際海洋法秩序相沖突,且未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所制定的國內法。如俄羅斯的《北部航道航行規定》和加拿大《北極水域污染防治法》等。
中國盡管為非北極國家,但中國是多個涉及北極的國際公約和多邊協定的締約國,分析中國在北極海域所享有的國際法下的權利,進而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并爭取更大的北極利益應是中國政府積極考慮和應對的問題。
一、中國在北極海域享有的權利
(一)航行權
著名的“海權論”者馬漢指出,“海洋使其本身成為最重要和最惹人注目的是其可以充分利用的海上航線”,[3]并將航行權作為海洋法權利的三大環節之一。航行權包括公海上的自由航行權、穿越毗連區和專屬經濟區受一定條件限制的無害通過權以及群島海道和國際航行海峽中的過境通行權。
1.自由航行權
1982年通過的《海洋法公約》把世界海洋劃分成領海、毗連區、專屬經濟區、大陸架、公海、國際海底區域等具有不同法律地位的區域,建立了全新的海洋法律制度。《海洋法公約》確立的分區性海洋體系,使得不同海洋區域的航行權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公海自由原則作為“海洋法之父”格勞休斯所確立的國際海洋秩序的基礎原則,在《海洋法公約》中依然得到了明顯體現,《海洋法公約》第87條再次確認了公海的自由航行原則,公海向所有國家開放,環北極國家和非北極國家均享有在北極公海海域自由航行的權利。
除了公海的自由航行權得以保留之外,《海洋法公約》新確立的海洋區域——專屬經濟區,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沿岸國的管轄范圍,將其主權權利進一步向海洋伸展,但專屬經濟區制度依然沿承了公海制度中的自由航行權,《海洋法公約》第58條明確提出了非沿岸國船舶在沿岸國專屬經濟區內享有公海制度中的自由航行權。
2.無害通過權
北極海域處于多個國家的環繞之中,《海洋法公約》規定的“領海”制度是國家主張主權權利的法律依據,環北極國家的領海也成為航行權受限最多的區域。即便如此,《海洋法公約》為了保障非沿岸國船舶的海上航行權,在第17條規定了“無害通過權”,即船舶在不損害沿海國和平、良好秩序和安全的條件下,“不論為沿海國或內陸國,其船舶均享有無害通過領海的權利”,而無需事先通知或取得沿海國的許可,并在第19條②《海洋法公約》第19條規定:“如果外國船舶在領海內進行下列任何一種活動,其通過即應視為損害沿海國的和平、良好秩序或安全:(a)對沿海國的主權、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進行任何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或以任何其他違反《聯合國憲章》所體現的國際法原則的方式進行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b)以任何種類的武器進行任何操練或演習;(c)任何目的在于搜集情報使沿海國的防務或安全受損害的行為;(d)任何目的在于影響沿海國防務或安全的宣傳行為;(e)在船上起落或接載任何飛機;(f)在船上發射、降落或接載任何軍事裝置;(g)違反沿海國海關、財政、移民或衛生的法律和規章,上下任何商品、貨幣或人員;(h)違反本公約規定的任何故意和嚴重的污染行為;(i)任何捕魚活動;(j)進行研究或測量活動;(k)任何目的在于干擾沿海國任何通訊系統或任何其他設施或設備的行為;(l)與通過沒有直接關系的任何其他活動。”以列舉的方式表明了非無害通過的種類。[4]
領海的“無害通過權”制度是《海洋法公約》對沿海國領海主權的一種限制,但同時,《海洋法公約》在第21條賦予了沿岸國制定航行安全及海上交通管理規定的權利,要求外國船舶在履行國際公約義務的基礎上予以遵守。此外,《海洋法公約》第53條“群島海道通過權”也是對“無害通過權”的有力支撐。
3.過境通行權
由于各國領海基線的外展,國家管轄范圍不斷向海洋延伸,部分海峽成為了國家所屬的“領峽”。尤其是北極海冰融化將加速“北極航線”的商業通航,而聯系亞、歐、美三大洲的最短航線分別是俄羅斯北部沿海的“東北航道”和加拿大基于群島直線基線方法納入管轄范圍的“西北航道”。為此,《海洋法公約》在第37條提出了介于“自由航行權”和“無害通過權”之間的“過境通行權”。“過境通行權”適用于在公海或專屬經濟區的一個部分和公海或專屬經濟區的另一部分之間的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但第三次海洋法會議并沒有就何謂“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達成一致。以“西北航道”為例,加拿大政府1970年出臺的《北極水域污染防治法》將北緯60度以北的水域劃為本國保護范圍,而《海洋法公約》第234條關于“冰封區域”環境保護的條款,為加拿大主張西北航道管轄權提供了法律依據。而美國、日本等國則堅持認為“西北航道”是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各國均有權“過境通行”。
對于這一北極航道法律地位的爭執,中國作為非北極國家,可以援引《海洋法公約》第35條的相關規定,“按照第七條確定直線基線的效果使原來并未認為是內水的區域被包圍在內成為內水的情況”不能影響國際航行海峽的“過境通行權”。因此,即使東北航道、西北航道適用俄羅斯和加拿大采用的群島直線基線的劃定方法,也不會影響中國在北極航道的“過境通行權”。
當然,俄羅斯和加拿大分別作為“東北航道”和“西北航道”管轄權的主張者,也會在不同層面對外國船舶的“過境通行”予以干涉,如俄羅斯在其《商業航運法》中提出對過境通行船舶的強制引航制度;加拿大則宣稱由于國際海事組織多年來對海域污染控制標準的缺失,沿岸國有權保護自身海岸和北極環境,對于不符合《北極水域污染防治法》要求的船舶禁止其在“西北航道”的通行。更有學者提出所謂“北極湖”理論,將《海洋法公約》所確立的航行制度在北極水域排除適用。
(二)海洋科學研究權
《海洋法公約》第十三部分“海洋科學研究”對世界海洋科學研究做出了原則性規定,第143條明確規定:“專為和平目的并為謀全人類的利益,各締約國可在‘區域’內進行海洋學研究。”第238條再次重申:“所有國家,不論其地理位置如何,以及各主管國際組織,在本公約所規定的其他國家的權利和義務的限制下,均有權進行海洋科學研究。”同時,針對不同海域的科學研究做出具體規定。這些規定當然適用于各國在北極的科考活動,也是中國等非北極國家從事北極科學考察的法律依據。
《海洋法公約》在“一般性規定”中強調各國均有進行海洋科學研究的權利,并限定了海洋科考的原則①參見《海洋法公約》第143條、第245條、第246條、第256條、第257條。:海洋科學研究應專為和平目的而進行,海洋科學研究應當遵守公約的其它方面的規定,海洋科學研究不應妨礙依照公約其他部分所進行正當活動,海洋科學研究活動不應構成對海洋環境任何部分或其資源的任何權利主張的法律根據。并且強調應當加強海洋科學研究方面的國際合作。依照《海洋法公約》,中國等非北極國家在北極的科學研究權利包括:在北極公海海域范圍內,享有自由科學研究的權利;經沿海國明示同意,可在環北極國家領海內從事海洋科學研究;經沿海國同意,可在環北極國家專屬經濟區內和大陸架上從事海洋科學研究。
在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上進行海洋科學研究,應至少提前6個月,通過官方渠道向沿海國提供科研計劃,詳細說明活動性質、目標、時間、區域、方法和工具、主持機構和主持人及沿海國可能的參與。為便利科考,《海洋法公約》還規定了“默示程序”,即:如通報后4個月,沿海國未拒絕計劃,也未要求補充材料,且提出計劃的國家或主管國際組織未因先前的研究對沿海國負有尚未履行的義務,則有關國家或國際組織可依通報的計劃開展科研活動。同時,為避免沿海國無故拖延,《海洋法公約》第246條規定:“在正常情形下,沿海國應給予同意。為此目的,沿海國應制訂規則和程序,確保不致不合理地推遲或拒絕給予同意。”
除《海洋法公約》外,與北極地區直接相關的國際條約是1925年生效的《斯瓦爾巴德條約》②斯瓦爾巴德群島(the Svalbard Islands)位于北冰洋,由斯匹茲卑爾伯根島(Spitsbergen)等三個大島和數十個小島組成,總面積達6.3萬平方公里,1920年由挪威、美國、丹麥、法國、意大利、日本、荷蘭、英國、愛爾蘭、瑞典等18個國家簽署了《斯瓦爾巴德條約》。,目前共有42個締約國,中國也是締約國之一。該條約第9條確立了斯瓦爾巴德群島成為北極地區第一個,也是惟一的一個非軍事區。[5]該條約第5條也授予中國等締約國進出地處北極的群島地區從事科研等活動的權利。
(三)海底使用權
《海洋法公約》提出了一個新概念——“國際海底區域”。該區域具體指國家管轄范圍以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即領海、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以外的深海洋底、底土,也包括海床及其下原來位置的一切固體、液體或氣體礦物資源。這一部分約占全部海洋面積的65%以上。《海洋法公約》第137條規定,國際海底區域及其資源是人類共同繼承的財產;任何國家不應對該區域的任何部分或其資源主張行使主權權利;任何國家或自然人或法人也不應將其據為己有。國際海底區域內的資源屬于全人類,由締約國組成的“國際海底管理局”(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代表全人類行使對其的一切權利;尤其是對區域內的活動進行組織和控制。[6]
至于在北冰洋海底究竟有多大的區域屬于國際海底區域,仍需等到北冰洋的沿海國確定了各自200海里以外的大陸架外部界限之后才能確定。如果北冰洋沿海國在北冰洋的外大陸架得以確立的話,北冰洋國際海底區域將縮小到現在的1/9,即從288萬平方公里縮小到34萬平方公里,這是對北冰洋全球公域的一種嚴峻挑戰。[7]那么中國在國際海底管理局的管理之下,既有分享、開發海底區域資源的權利,也有保衛海底區域資源、防止開發海底資源造成海洋環境污染、和平解決海底區域爭端的國際義務。中國已被聯合國批準為深海采礦“先驅投資開發國”,在東北太平洋靠近北極水域擁有一塊15平方公里的礦區,可以享有準主權的開辟活動。而且,到1999年,其中7.5平方公里的富礦已經由中國進行排他性開采,具有永久性管轄權。
(四)海洋生物資源開發權
北極海域擁有豐富的漁業及海洋生物資源。1984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北極研究與政策法案》,在該法案中指出了北極對于美國的重要價值,其102(a)款明確提出:“北極的可再生資源,如魚類和其他海產,代表著國家的重要貿易資產。”中國是《斯瓦爾巴德條約》的締約國,《斯瓦爾巴德條約》第2條明確提出:“締約國的船舶和國民應平等地享有在第一條所指的地域及其領水內捕魚和狩獵的權利”,且該條約“平等地適用于各締約國的國民,不應直接或間接地使任何一國的國民享有任何豁免、特權和優惠。”同時,《海洋法公約》第61條和第62條分別規定,沿海國應決定其專屬經濟區內生物資源的可捕量并決定其捕撈專屬經濟區內生物資源的能力。第70條規定,當一個沿海國的捕撈能力接近能夠捕撈其專屬經濟區內生物資源的可捕量的全部時,該沿海國與其他有關國家應在雙邊、分區域或區域的基礎上,合作制訂公平安排,在適當情形下按照有關各方都滿意的條款,容許同一分區域或區域的地理不利國參與開發該分區域或區域的沿海國專屬經濟區內的生物資源。也就是說,北極水域沿岸國在沒有能力捕撈全部可捕量的情形下,應通過協定或其他安排,并根據公約規定,準許其他國家捕撈可捕量的剩余部分。[8]
此外,在北冰洋的附屬海域白令海,中國與白令海的兩個沿海國——俄羅斯、美國以及其他3個公海國日本、韓國、波蘭共同簽署了《中白令海峽鱈資源養護與管理公約》,通過沿海國與公海捕魚國的合作建立了一個對公海漁業養護、管理和最優化利用資源的制度,對公海漁業的管理提供了一個先例。這個公約的簽署明確了中國在高緯度北極海域的公海進行漁業捕撈與管理的權利,也是中國通過多邊協定主張北極海洋法權利的有益嘗試。
(五)海上事故或事件調查權
國際海事組織是聯合國負責海上航行安全和防止船舶造成海洋污染的專門機構,其出臺的國際海上公約和指南當然適用于北極水域。中國已連續12次當選國際海事組織的A類理事國,享有國際海事組織相關公約賦予的權利。
《海上事故或海上事件安全調查國際標準和建議做法規則》(簡稱《事故調查規則》)于2008年5月在國際海事組織海上安全委員會第84屆會議上通過,并被納入《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第十一章,已于2010年1月1日生效。《事故調查規則》生效前,海事調查權主要由沿岸國掌控,中國船只航行于北極水域時發生海上交通事故,一般由環北極國家等沿岸國負責調查并做出結論。
《事故調查規則》最大的調整就是海事調查權向船旗國的回歸,第2.14條規定:“海事安全調查國系指船旗國或依據本規則經多方協商決定負責海事安全調查的有關國家。”《事故調查規則》同時引入了“實質利益國”概念,第2.20條對實質利益國進行了規定①《事故調查規則》第2.20條規定:“有重大利益的國家系指:1.海上事故或海上事件中當事船舶的船旗國;或2.海上事故或海上事件發生地的沿岸國;或3.由于海上事故,該國的環境受到了嚴重污染(包括國際法規認可的該國內水或領海);或4.海上事故或海上事件造成或可能造成該國或該國有管轄權的人工島嶼、裝置以及構筑物等嚴重損害;或5.海上事故造成該國人員死亡或重傷;或6.海事安全調查國認為該國控制著對事故調查有用的重要信息;或7.海事安全調查國出于其他理由認為該國涉及到重要利益的。”。《事故調查規則》第7章又對船旗國與其他實質利益國協商實施海事調查進行了規定。由此可見,根據《事故調查規則》,沿岸國、船旗國、船員來源國等實質利益國家均可參與調查,并通過協商決定哪個國家為主要負責調查國家。據此,中國對于本國船只在北極水域發生的海上交通事故擁有不可置疑的調查權。
(六)海上搜尋救助權
國際海事組織海上安全委員會出臺的《1979年國際海上搜尋和救助公約》(簡稱《搜救公約》)將世界海洋劃分為13個搜救協調區,每個搜救協調區由一個或幾個國家充當信息搜集國。北極海域是第13區,挪威為信息搜集國。該公約第三章第3.1.2條賦予了締約國“為了搜尋發生海難的地點和救助該海難中遇險人員的目的,進入或越過沿岸國領海和領土”的權利。《搜救公約》適用于發生在北極海域的船舶事故,中國是《搜救公約》的締約國,有權基于北極水域海上救助目的進入或越過環北極國家領海。
此外,2011年5月在丹麥格陵蘭島首府努克召開的第7屆北極理事會外長會議上,與會國家外長簽署了北極理事會成立15年以來的首個正式協議——《北極搜救協定》,就各成員國承擔的北極地區搜救區域和責任進行了規劃。《北極搜救協定》是北極理事會第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其第十八章規定“協定的任何締約國可以在適當的地方尋求和非締約國間的能夠有利于搜救工作執行的協作”,中國不是《北極搜救協定》的締約國,但有權與相關締約國開展協作,航行于北極水域的中國船只有權接受搜救服務。
此外,《海洋法公約》所確立的便利交通原則、公平利用海洋原則和可持續發展原則都可以成為中國在北極主張權利的依據。1996年4月23日,中國經國際北極科學委員會決議,成為《海洋法公約》第16個成員國,[9]可與北極國家開展多邊和雙邊合作,進行環北極科學研究,并共享研究數據。根據北極理事會通過的《北極海上油氣活動指南》第1.2條、第3.6條和第7.1條,中國作為非北極國家可就“北極油氣活動的規劃、勘探、開發、生產等活動”參與協商,并貫穿整個項目始終,還可以參與應急國際協作,等等。
二、中國參與北極事務以爭取更多海洋法權益的視角分析
俄羅斯《國際生活》雜志曾發表過一篇標題為《圍繞北極的冷戰》的文章。文章透露,北冰洋沿岸一些國家打算在盡可能小的圈子里瓜分北極,希望通過“內部協商,外部排他”來處理北極領土和權益問題,并進行北極治理。因此,北極問題既是科學問題、法律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既是區域問題,也是國際問題。中國作為北半球國家,地處中緯度地區,北冰洋和北冰洋氣候變化將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自然環境產生重要影響,保留北冰洋作為國際公海的地位,符合中國戰略利益要求。[10]所以,中國需要從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出發,積極參與北極地區事務,確定中國在北極的身份定位及利益范圍。
(一)政治角度
1.明確北極問題的性質,制定國家北極戰略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提高,大國爭奪的觸角已經深入到地球的各個角落。北極地區極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豐富的自然資源,已成為大國爭奪經濟利益的新戰場。雖然北極地理位置具有相對獨立性,但它屬于復雜的國際關系和國際法互相交錯的共同指向,深受雙邊和多邊關系的影響;北極地區各種矛盾錯綜復雜,既有北極國家之間的矛盾,也有北極國家與非北極國家之間的矛盾。北極爭端實質上就是對北極海域政治價值、軍事價值、自然資源、航運貿易乃至科研價值的控制與壟斷,北極是將由國際社會公平、公正、科學、和平地開發利用還是任由大國、強權所操縱,這不僅關乎各國利益,而且對國際局勢的穩定、國際秩序的維護、國際格局的演化和國際安全的保障都意義深遠。只有從更加宏觀和戰略的視角中考量北極事務,才能理清脈絡。如若單獨審視北極問題,而不去考慮諸多影響因素,就無法在紛繁復雜的國際事務中剝繭抽絲。
對中國來說,保留北冰洋作為國際公海地位,符合中國戰略利益要求。所以,中國要將國家外交戰略、海運戰略和北極戰略結合起來,制定相應的有關北極的國家戰略,從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出發,全面研究北極潛藏的地緣戰略價值和經濟價值。中國要積極適度地參與到北極相關事務中去,認真研究維護中國在北極正當權益的各種途徑,確定自己利益的范圍并最大限度地維護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這絕不是部分媒體所渲染的“進軍”、“爭奪”等。對北極海域公海地位的維護,不僅有利于促進世界各國安全通航的要求,更為重要的是使各國都有權參與北極地區的資源開發和利用,能夠有效制衡和防范部分大國對北冰洋資源的壟斷,有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經濟新秩序。
2.強化北極事務參與的切入點,積極開展北極問題研究
北極事務中包括了資源權利等敏感的國際紛爭與海域、大陸架等主權分歧,也包括了各國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合作。北極事務是一個涉及到諸多因素的復雜的全球性問題,北極形勢容易受到北極海洋權益爭議的影響,而環保、科學、社會發展等領域的合作則將國際社會凝聚在一起。在當今國際社會“低度政治”盛行的形勢下,中國參與北極事務的切入點宜從科考、環保等方面入手,保持并加強與北極區域的“親密接觸”,積極參加北極區域的相關活動,增加在北極區域能夠代表國家形象的“現實存在”。在此基礎上向其他縱深領域拓展,逐漸擴大中國對北極事務的參與權。
為此,中國需要積極開展北極相關問題的研究,科技實力是北極爭奪戰中的關鍵因素,如果缺少科研的支撐,在北極爭奪戰中很難取勝。不同于殖民地時代,各國想要在北極主張權益,必須提出合理合法的依據。想要在北極爭奪中占據先機,中國必須加大對北極地區科考研究的力度,研究范圍要涉及到北極自然資源、漁業資源、礦產資源及其氣候變化對中國環境、氣候、地緣政治、經濟、航運等各個領域所造成的影響,并爭取將研究成果應用于北極的開發利用,讓“中國制造”的軟實力覆蓋北極區域的多個層面。
3.努力尋求加入北極相關組織,提升中國的參與層次
北極區域環保、社會和人文組織數目眾多,如國際極地基金會(IPF)、北方聯合會(NF)、國際北極社會科學協會(IASSA)、北廷北極研究論壇(NARF)①在丹麥建立,主要從事北極當代問題的人文科學和交叉學科研究。、北極大學(UA)②由從事北極研究的大學和機構組成的大學聯盟,總部設在加拿大的育空大學。等。中國目前加入了國際北極科學委員會(1996年正式加入)、北極理事會(2007年成為非正式觀察員)等少數幾個組織,且常常錯過組織活動,如2007年10月由北極理事會和北方學會聯合主辦的北極能源峰會,日本、韓國、印度都派出代表參加,會議討論了全球變暖背景下,如何共享北極地區的能源信息和技術問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北極問題的研究也剛剛起步,在許多北極論壇和國際會議上很少看到中國學者的身影。通過積極參加北極組織并參與北極事務,中國能夠對北極地區事務的最新發展動態予以了解,關注相關熱點問題,還能夠通過參加一些科考項目分享最新的科學技術及學習應對相關問題的經驗。
(二)法律角度
1.積極推動《海洋法公約》在北極的適用
根據《海洋法公約》第58條、第87條,中國享有在北極國家專屬經濟區內的海洋科研自由、“無害通過權”以及鋪設水下電纜和管道等權利。如何在北極區域貫徹落實《海洋法公約》的相關條款,是以中國為代表的非北極國家在北極海域的集中利益訴求所在。
此外,如何在國際海洋法中界定冰架、冰山的法律地位并確定對其的管轄權,積極落實《海洋法公約》第76條關于外大陸架界限的規定,盡快解決北極國家的海域劃界爭議,推動北極航道國際化通航,也是未來國際海洋法值得探討和規定的新問題。在2000年“卡塔爾訴巴林”案之后,國際法院開始對領海直線基線的確立持嚴格態度,為中國主張在北極地區的權益,抵制北極國家的“藍色圈地”運動提供了法理和科學依據。
2.以國際海事組織為平臺,積極參與北極海事立法
北極理事會第七次部長級會議發表了《努克宣言》,督促國際海事組織加快“極地航運規則”的制定和出臺進程。在海事公約修正或制定的前期,中國應積極介入,力爭掌握話語權,使航行規則的訂立符合中國的航運利益。應克服北極非沿岸國的地理劣勢,積極推進建立制定北極航道航行規則的協調機制,具體參與點如下。
第一,《1972年國際避碰規則》適用于公海以及與公海相連一切水域,是當前海上航行船舶避碰的基礎公約,北極水域當然適用。但該規則沒有關于船舶在冰區航行時的相關準則,對于冰區船舶避碰和極地船舶也沒有專門規定,亟待調整立法。
第二,《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第七章和《國際海運危險貨物規則》(IMDG Code)中,對于海上危險貨物運輸的相關規定也存在北極適用問題,隨著北極商業通航的日趨臨近,有必要重新審視在低溫地區運輸海上危險貨物的標準。
第三,2002年,國際海事組織通過了《北極冰封水域船舶操作指南》,適用于在冰封水域航行的客船和500總噸及以上的貨船。該方針雖然在船體、破損穩性、消防、救生、助航設備、船舶操作、配員、應急、環境保護等方面均作了較為詳細的規定和說明,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陷,主要是相關培訓的國際統一標準和相關細節的欠缺,難以為航海人員提供真實準確的冰區航行經驗,關于預防和緩解船體積冰以及冰區拖帶作業的內容也是非常有限的。[11]
第四,北極航線的北歐部分相對比較成熟,目前,北歐各國一直在沿用,可以借鑒。但北冰洋東經90度以東沿岸到白令海航線(東北航線),除俄羅斯外較少有船舶航行。在加拿大,大約有240張關于北極海域的海圖,但其中僅有10%能夠達到相關標準和滿足航海需求。[12]中國應利用經濟實力,增加北極海圖繪制的勘測工作,盡快提高破冰船和其他船舶的造船技術和標準以及加強人員在冰上航行的培訓,以應對船舶在北極海域的商業性通航,為中國船舶北極航行的實施奠定基礎。
第五,除了美國,其他北極國家的海事管理機構都是《巴黎備忘錄》的成員,未來,北極海域國家或北極國家的港口監督管理機構完全可以比照全球港口國監督的區域性協議的模式,簽署一個“北冰洋或北極海域地區PSC備忘錄”。
三、結語
一個穩定繁榮的北極是中國的利益所在。作為非北極國家,中國一方面應堅持國際海洋法秩序現有的原則和制度,另一方面應積極參與未來北極相關的國際海洋法的修改與構建,堅持自己的立場與原則。正如中國代表團副團長沈韋良在《海洋法公約》出臺后的發言中所指出的,《海洋法公約》“還只是建立新海洋法律秩序的第一步……廣大發展中國家為維護公約的宗旨和原則,捍衛本國的正當權益,還需要繼續不斷做出努力”。[13]
[1]JABOURl J,WEBER M.Is it time to cut the gordian knot of polar sovereignty?[J].Review of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2008,17(1):29-33.
[2]嚴雙伍,李默.北極爭端的癥結及其解決路徑——公共物品的視角[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6):830-836.
YAN Shuang-wu,LI Mo.Arctic dispute and its solutions——the view of public goods[J].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09(6):830-836.(in Chinese)
[3]馬漢.海權對歷史的影響[M].安常容,成忠勤,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8:26.
MAHAN A T.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M].translated by An Chang-rong,CHENG Zhong-qin.Beijing: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ublishing House,1998:26.(in Chinese)
[4]張海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釋義集[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6:34.
ZHANG Hai-wen.Paraphrase sets on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M].Beijing:China Ocean Press,2006:34.(in Chinese)
[5]曾望.北極爭端的歷史、現狀及前景[J].國際資料信息,2007(10):11-17.
ZENG Wang.History,status and prospecs of Arctic dispute[J].International Data Information,2007(10):11-17.(in Chinese)
[6]王鐵崖.國際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288-290.
WANG Tie-ya.International law[M].Beijing:Law Press,1995:288-290.(in Chinese)
[7]郭培清.北極航道的國際問題研究[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59.
GUO Pei-qing.Study on the international issues of Arctic waterway[M].Beijing:China Ocean Press,2009:59.(in Chinese)
[8]劉振民.海洋法基本文件集[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2:39.
LIU Zhen-min.Basic documents of the law of the sea[M].Beijing:China Ocean Press,2002:39.(in Chinese)
[9]田興春.地球盡頭的狂熱角逐:插旗激起千層浪[EB/OL].(2007-08-06)[2012-05-14].http://world.people.com.cn/GB/89881/97034/607334.html.
TIAN Xing-chun.The fever for the end of the earth:Arctic contestation cause parties reaction[EB/OL].(2007-08-06)[2012-05-14].http://world.people.com.cn/GB/89881/97034/607334.html.(in Chinese)
[10]王酈久.北冰洋主權之爭的趨勢[J].現代國際關系,2007(10):17-21.
WANG Li-jiu.Trend of the sovereignty dispute over the Arctic ocean[J].Contempo 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07(10):17-21.(in Chinese)
[11]The IMO guidelines for ships operating in Arctic ice-covered waters[EB/OL].[2012-05-14].http://www.fni.no/doc&pdf/FNIR0207.pdf.
[12]曹玉墀.北冰洋通航可行性研究[D].大連:大連海事大學,2010:85.
CAO Yu-chi.The Arctic navigation feasibility studies[D].Dalian: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2010:85.(in Chinese)
[13]陳明.海洋法中的剩余權利與我國海洋權益的保護[D].蘭州:蘭州大學,2007:5.
CHEN Ming.The residual rights in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nd the protection of China’s sea rights[D].Lanzhou:Lanzhou University,2007:5.(in 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