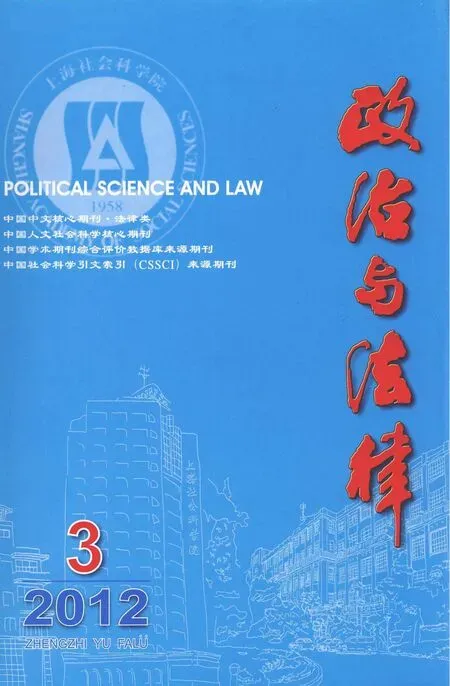龔某盜賣其父房產一案之我見*本文受上海市重點學科建設項目“刑法學”(項目編號:S30901)資助。——兼談不動產可以成為盜竊罪之對象
楊興培
一、問題的提出
《政治與法律》2011年第11期發表了吳家明的文章——《合同詐騙罪與表見代理之共存及其釋論——一起盜賣房屋案引發的刑民沖突及釋論》一文,文中就行為人龔某盜賣其父親房屋一案1提出了作者的鮮明觀點,認為該案應當以合同詐騙罪論處。但筆者細細品味該案,認為上述觀點在刑法理論上存在著諸多的瑕疵并且理論闡述不能自圓其說。筆者對這一類型民刑交雜的案件情有獨鐘,認為對其中一個案件的“解剖麻雀”,也能起到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的效果,這對刑法理論展開深入的研究和對刑法的經典教學大有裨益。為此,筆者很想與該作者進行一番商榷兼求教方家,以求獲得對一些刑法理論是非的澄清,以此促進對這一類案件的正確認定。
該案還有補充情節:其一,從龔某身份證上的照片來看龔某與其父相差無異,容易讓人誤以為龔某就是其父親本人,事實上王某的確陷入認識錯誤;其二,出示給王某驗看的身份證、房產證、公證文書都是真實的,王某有充分理由相信這一買賣就是龔某父親本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其三,龔某父親事后向法院起訴根本不承認這一買賣的合法性,堅決要回屬于其本人的房產。而人民法院的判決把本案的被害人確定為王某,判決內容之一為:“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予追繳后發還被害人。”因此,無論從法院的判決來看還是吳文的基本觀點來看,都是把本案看成是一起合同詐騙案。
從本案的基本案情介紹和補充情節來看,本案龔某與王某的房屋買賣屬于一種表見代理,因此王某通過龔某的表見代理獲得龔父房產的所有權是一種“善意取得”。但能否因龔某瞞著其父與王某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就可以認定龔某構成合同詐騙罪,因而本案形成刑法語境下的“合同詐騙”進而與民事法律中的“善意取得”制度發生沖突,并由此引發刑民交叉與刑法上的被害人如何定位等一系列問題,都有待于我們的深入討論。
根據民法的規定,合同是平等主體之間的雙方當事人為確立、變更、終止民事法律關系而簽訂的一種協議;而根據刑法的規定,合同詐騙罪是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等手段,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數額較大錢財的行為。合同詐騙罪基于合同的行為而產生和成立。因此,合同詐騙的行為人必須是合同的一方當事人,而合同詐騙罪的被害人也就必須是合同的相對方當事人,這是刑法明文規定的確切內容。如果本案龔某的行為可以構成合同詐騙犯罪,那這一合同詐騙罪的被害人必定是購房者王某,原先的房屋買賣合同必然屬于無效合同。但是這是就刑法理論與刑法實踐而言的。
然而如果就民法理論與民法實踐而言,無效合同或效力待定合同的法律效果從其一開始就為無效或者從合同效力被否定之時起無效,雙方必須各自返還已取得的財物,無過錯且受損失一方有權要求賠償。但如果在合同簽訂和履行過程中,他人基于某種合理合法的現象而善意取得他人的財產,即使發生刑事犯罪,法律也承認善意取得已確立所有權。民法上的表見代理,我國《合同法》第49條規定:“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后以被代理人名義訂立合同,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的,該代理行為有效。”該制度的意義也在于維護交易制度的誠信基礎和交易安全,保護無過錯交易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建立正常的民事流轉秩序。2007年10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頒布以后,不動產也適用善意取得制度,最顯著的特征表現為物權和債權相分離,即使房屋買賣的合同被判無效,但原先的房屋買賣基于物權的公示、公信原則已經登記過戶的,法律還是承認購買人取得不動產所有權。通過這樣的民法考察,合同詐騙與善意取得制度并不矛盾,就算是由于合同詐騙而使原房屋買賣合同無效,但由于物權和債權可以分離,善意購買人依舊可以取得房屋所有權。
然而在刑民交雜的刑事案件處理過程中,確定誰是被害人有時則使兩者的關系發生根本的變化,甚至會導致案件出現意想不到的邏輯錯誤。(1)將合同相對方作為被害人,這是絕大多數合同詐騙案件的通常做法,在司法實踐中也無多大爭議。然而在本案中,由于合同相對方作為善意第三人,民事法律保護他的合法權益,他已實際轉變成了本案房產的合法所有人,此時再將他認定為“被害人”顯然不妥。因為本案中此時的王某根本沒有“被害”,善意取得制度正在保護著他,房子已經屬于他了,他沒有遭受任何損失。也正因為此,王某也向司法機關提出申訴,不承認自己是“被害人”。(2)如果將房產的原先所有人作為本案合同詐騙罪的被害人,也就是龔某之父也有問題。首先,合同詐騙罪的前提是合同關系的存在,合同詐騙罪的被害對象法定為簽訂合同的對方當事人,而本案中的房產原先所有人并沒有參與簽訂合同,將其作為被害人不符合合同詐騙罪的實質要件。其次,刑事詐騙的一個核心含義就在于受害人基于錯誤的認識而做出一定的交付行為。但本案中房產的所有人既沒有產生什么錯誤的認識,也沒有做出與此相關的行為表示,由此看來,要將龔某之父作為被害人是沒有法律根據的。最后,如果將龔父作為被害人,相應的法律后果是使房屋回歸到原始狀態,即回歸到真正的所有人名下,合同一方被騙的錢款退回給被騙的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對方當事人,但這樣又勢必將違反民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造成刑法與民法的明顯沖突。進一步而言,如果將房屋歸還給房屋原先所有人的話,那么從民法的角度來看,房屋交易就變得極不安全。這是因為在正常的房屋買賣過程中,在第三人完全沒有惡意、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與他人進行交易,當對方出示的身份證、產權證件等均為真實、合法、有效后,還要其關注合同交易過程中的其他非法律規定的因素,那么任何一樁房屋買賣交易還可能正常進行嗎?所以,無論把誰確定為被害人,看似都無法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這些問題都需要進行深入的探討研究。
二、龔某與王某的房屋買賣行為構成表見代理
那么本案的焦點問題究竟在哪兒呢?我們對此進行法律分析的邏輯起點又在哪兒?在中國由于我們長期以來一直受“天人合一”的文化思想浸潤和我國刑事司法實踐中一直喜歡重實質、輕形式操作方法的影響,稍一疏忽就會將本案簡單化地認為這不過是一起刑民交雜、可以合二為一的案件而已。但基本的法學原理告訴我們,其實同一個案件事實是否包含著刑民交雜的兩個法律關系,就看某一法律事實是否能夠為兩種法律規范加以規定并為兩種法律規范加以調整。法律本身就是為規定和調整一定的社會關系而加以設定一定條件的專門規范。法律與法律之間的區別就是法律調整的社會關系的性質與范圍。我國《民法通則》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調整的是平等主體的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公民和法人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而刑法調整的是犯罪受害人與犯罪行為人之間圍繞如何追究刑事責任而結成的相互關系。在我國由于刑事法律的特別規定,受害人的追訴權是由有權指控和提起訴訟的國家特定司法機關代為行使(即國家公訴,自訴犯罪除外)的。一般意義上的刑民交雜案件往往包括著兩種刑民相關的事實關系。一是案件中包括著刑民兩種法律關系,但它們是一種縱向的重合關系,如刑事詐騙中本身包括著民事欺詐的行為要素。刑法意義上的“詐騙”與民事法律中的“欺詐”,在手段上均可以表現為采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等手法,使被害人產生錯誤的意識,進而基于錯誤的認識作出一定的意思表示。兩者的區別可以體現在主觀惡意程度、社會危害性大小、金額數量、行為方法與行為性質等方面,民法上的“欺詐”達到什么程度才能上升為給予刑罰處罰的詐騙犯罪,尤其是當合同詐騙類的犯罪與民法上通過簽訂合同進行欺詐存在一定競合的時候,在具體處理案件時可能難以精確區分兩者的界限。如在本案中,龔某通過委托丁某與王某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將其父親的房產出售,涉案的金額達到43.5萬元。如果將本案簡單地作為刑事案件處理,就是因為其涉案金額巨大的緣故嗎?那么按照現在的房價、地價,只要涉及房屋買賣的,動輒就是上百萬的交易額,這樣在房產交易領域是否就可以排除民事欺詐的可能性嗎?而無處分權的他人拿別人的房產去和第三人交易,采用的也是隱瞞真相的手段,事實上也是欺詐行為的一種表現形式。這樣一來,必然要在排除民事欺詐的同時也將善意取得的制度給否定了,這又不能為民法所認同。二是案件中同樣包括著刑民兩種法律關系,但它們是一種橫向的并列關系。當一個案件中包括著刑民兩種法律關系,但它們是一種縱向的重合關系時,司法實踐往往采取“先刑后民”的操作方式;而當一個案件中同樣包括著刑民兩種法律關系,但它們是一種橫向的并列關系時,這在司法實踐中應當是一種“橋歸橋、路歸路”的事實現象,它們必然要接受兩種不同的法律規范的評價。事實評價是我們進行規范評價的前提和基礎。當我們仔細分析研究本案事實時,必然會發現這里存在著的是兩個并列的法律關系。其一是,龔某瞞天過海盜竊其父親的各種有效房產所有權證明材料,進而與王某簽訂房屋買賣合同,這是一個具有表見代理性質的民事法律關系。其二是,龔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秘密竊取的手段盜取其父房屋的各種有效證明文件,然后又通過盜賣的方式占有其父親的房屋,盜賣房屋的錢款占有和揮霍行為是其盜竊行為的延伸,也是對其盜竊所得的處理方式。這一行為形式與房屋買賣行為有著本質的區別。因此我們必須通過已經還原的行為事實作深入的分析評定,應當將“龔某”還原為兩個不同法律關系中的一方“當事人”后進一步來認定其行為性質。
就第一個法律關系而言,龔某的盜賣行為在民法上是有瑕疵的。但由于民法已有表見代理的明確規定而使這種有瑕疵的民事行為依然具有法律效力,以此有利于保護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維護交易安全。王某作為一個民事買賣行為一方當事人,通過驗看龔某的各種有效的房屋證明文件而與龔某簽訂房屋買賣合同,這是一種正常的民事買賣行為。龔某的行為事實上具有欺瞞屬性,但不影響他對其父“房產”的取得。房產屬于不動產,根據物權法的規定,不動產必須進行登記過戶才能確認其所有權。王某已根據法律規定進行了房屋的過戶與登記,因此法律理應對王某的權利予以有效保護。
本案的核心問題出在第二個法律關系上,龔某憑什么出售其父親的房產。龔某與其父親雖為父子關系,但在法律關系上,兩人具有獨立的人格和各自獨立的財產所有權(本案不具有共有關系)。沒有經得其父親的知曉和同意,龔某是沒有權利處置其父親的房產的。如其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其行為方法觸犯了刑法的禁止性規定,就有可能構成相應的犯罪,就得接受刑法的否定性評價。而正是在這一個環節上,作為龔某來說,其行為完全以不為其父親知曉的方法,通過欺瞞的方式將其父親的房產秘密地加以出售,因而在刑法上構成了侵犯財產的犯罪。
三、龔某的盜賣行為不能構成合同詐騙罪
從實質意義而言,刑法上的“占有”與民法上的占有實際上是一個相同的概念,它是指人與財物的一種相互關系,也就是指他人對財物進行事實上的控制和支配。但對于財產性犯罪的行為人來說,他已經明知這是通過不合法的方式而加以實現的,是一種沒有法律支持的行為。由于財物的所有權是一個合法的權能,是一種法律的確認,對于犯罪所得物而言在法律上永遠無法得到合法的確認,所以在刑法理論上僅僅以非法占有作為表述的形式。具體地說,非法占有是指行為人針對原財物的事實占有人、控制人通過非法的行為將他人的財物形成處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作為自己的“所有物”進行占有、控制和處分的行為活動。
龔某的行為足可以構成財產性犯罪,但應當構成什么罪呢?能否像吳文所說應當構成合同詐騙罪呢?規范評價必須以規范的標準來加以衡量。何為合同詐騙罪?已如前述,是指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等手段,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數額較大錢財的行為。由于合同詐騙罪是從普通詐騙罪分離出來的一種法條競合性犯罪形式,合同詐騙罪同樣受制于普通詐騙罪的概念約束。詐騙,無非是指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造成他人發生錯誤的認識和作出錯誤的決定,從而非法占有他人自愿轉移交付的財物的行為。在本案中,如前所述,不宜將王某認定為合同詐騙罪的被害人,而如果以龔父為合同詐騙罪被害人,則龔某之父根本不知曉其子有如此之行為。因此對于龔某父親來說,既無發生錯誤認識的意識過程,也無作出錯誤決定的意志表示,更無自愿轉移交付財物的行為表現。由此一來,龔某針對其父可能構成詐騙之罪就無從說起。如果龔某連普通詐騙罪都無法構成,又如何能構成特殊的合同詐騙罪呢?因此龔某的行為不符合這一法定要件,理應不構成合同詐騙罪。但能否如吳文所說的通過對房屋買賣中的合同詐騙罪擴大解釋,從而將本案龔某的行為納入該罪?由于作為形而上的信仰意識的長期缺失,由此形而下地延伸到法律領域,中國至今還未真正建立起法律信仰的社會基礎,在一些任意性的意識支配下,法律有時很容易成為一種彈性道具,使一些擁有話語權的人輕而易舉地可以對本屬于“神圣”的法律進行任意的拿捏,而且使拿捏者感覺特別方便駕馭。在司法實踐中,法律一旦脫離了形而上的法律價值邊界的約束,那么形而下的層面在所謂“實質解釋”觀念的引導下,任何犯罪都可以是個“大籮筐”,憑著“價值先導”需要勢必什么東西都可以往里裝。至于認為龔某之父與王某可以同屬于本案“被害人”的觀點,可能是想從“二一添作五”的角度實現“利益均沾”以此息事寧人,但是一旦有人追問“其根據”,就往往會使司法實踐處于尷尬的境地而無法自拔。
至于吳文說到可以通過“三角詐騙”的形式確認本案的合同詐騙罪的性質是否行得通呢?這種觀點的一個吊詭之處就是將分析認定本案犯罪性質的邏輯起點放在行為一定構成詐騙的基礎上,于是導致價值先行、規范隨后的思維定勢直接轉化成了一種固定不變的操作方式。但筆者認為,司法實踐必須以法律為規范評價的依據;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可以以司法解釋為依據;而司法解釋都沒有明確規定的,可以由法官釋法。但即使進行法官、檢察官釋法,也必須依據罪刑法定的原則來進行,并在嚴格解釋的基礎上作出價值中立的解釋。然而在“三角型詐騙”的問題上,已有明確的司法解釋。2002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關于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物的行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答復》中指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物的行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審判活動,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作出處理,不宜以詐騙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由此我們可以明確地得出結論,即使本案具有“三角型詐騙”的行為特征,依然不能構成合同詐騙罪。
四、龔某的盜賣行為應構成盜竊罪
經過前面的分析認定,本案龔某實際上是以秘密的、不為其父親知曉的方法,非法地在占有其父親的房產基礎上又轉移了其父親的房產,并將所獲錢款揮霍一空,對此理應構成盜竊罪。將本案認定為盜竊罪,由此產生一個刑法理論上的新問題,即不動產也可以成為盜竊罪的對象。這是否會導致傳統理論觀點的責難呢?由于長期以來在刑法理論上一直將盜竊罪視為一種通過轉移他人合法財物加以非法占有的犯罪形式,因此不動產不能成為盜竊罪的對象幾成定論。但隨著社會生活內容的不斷豐富復雜,財物種類的不斷增加,盜竊犯罪行為的不斷翻新,只有動產才能成為盜竊罪的對象的觀點面臨著新的挑戰。
任何一種具有科學性的理論結論和實踐結果不應該存在于純粹的思辨之中,而應當存在于不斷進行的實踐中并接受實踐的檢驗。盜竊罪是一種侵犯他人財產所有權的犯罪,但由于所有權是一種法律的確認,不管犯罪以怎樣的手段獲得他人的財產,法律絕不會承認他的所有權,一旦犯罪東窗事發,財物還得物歸原主,犯罪行為人最多獲得了對財物的暫時占有。因此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實現了對財物的非法占有,即可以構成犯罪。占有是一種客觀的事實狀態。既然是占有,當然既可以對動產占有,也可以包括對不動產的占有。正如前述就其實質而言,刑法上的“占有”與民法上的占有實際上是一個相同的概念,它是指人與財物的一種相互關系,也就是指他人對財物進行事實上的控制和支配。正如日本刑法學者所說的,所謂非法占有的意思是指:“排除權利者,將他人之物當成自己的所有物那樣按照其用途進行利用或者處分的意思。”2非法占有的行為不過是這一主觀意思活動的客觀外在表現而已。
日本刑法典改正草案第326條規定:“因沒有得到占有者的同意,把他人的汽車、飛機及其他具有發動機的乘用物一時性的使用者,處三年以下徒刑或10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拘留。”3由此引發了對使用盜竊能否入罪的理論思考。正是由于刑法理論和有關的刑事立法例對非法占有進行深入本質的理解,將非法占有解釋成就是使用非法手段對他人所有的財物行使事實上的占有、使用、收益或處分權,從而侵犯他人對某一特定財物的所有權的正常行使。由此已有學者提出使用盜竊也是盜竊的觀點。4這種觀點已有一定的理論基礎和社會基礎。使用盜竊都可以成立盜竊罪,那么通過秘密的方法占有他人的財物并進行處分,即便是不動產,當然也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以中國刑法理論的傳統思維同樣可以證明:出罪者,舉重以明輕;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5筆者曾與一些刑法學者專門討論過不動產能否成為搶劫罪財物對象的問題,有學者曾在理論上虛擬當合法的所有人被暴力制服后,同意行為人長期占有其住房進行居住的例子說明,在理論上不動產完全可以成為搶劫罪的對象。本案中,龔某將其父親房屋的有效證明加以盜取后進行買賣交易,其實已經對其父親的房屋所有權進行了事實上的占有、控制和處分,從而使該房產在法律上脫離了其父親的占有和控制;也會在事實上脫離其父親的有效占有和控制。龔父房產的空間位置并沒有發生變化,但是其占有狀態卻在法律上和事實上已經發生了變化,即已經不再為龔父所占有著了,這正是盜竊犯罪所要達到的客觀效果。因此,龔某的行為可以構成盜竊罪并沒有什么法律障礙和理論障礙。
五、余 論
吳文中有一種理論觀點和理論闡述讓筆者有點不能輕易釋懷,即該作者在表達自己觀點尋求支持時,往往以司法實踐中的一些不具有典型意義的案例作為理論的來源,這也是當下一些刑法學人常常使用的一種論證方法。比如除了上面提到的根據所謂“實質解釋”的理論對一些刑法關鍵詞匯作擴大解釋、將三角型的欺詐視為詐騙犯罪。同時在一些本來極有爭議的刑民交雜案件中,往往以司法實踐的有效判決作為理論正確的“標尺”,例如有關“婚內強奸”的判例、事實婚姻中的重婚罪判例、銀行卡的合法所有人將他人存放在自己卡內的錢款加以提取后被判盜竊的判例。在中國由于實行的是成文法的法制模式,已判決案例并不具有天然的法律效力,即使在理論界大力提倡推廣判例制度的今天,司法實踐已經形成只有經過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確認的判例才有司法解釋示范作用的共識。對于一般司法實踐中的案例,我們承認其是有效的,但我們不能一概承認其是有理的甚至就是正確的,司法實踐中的一審再審不斷反復的案例大有存在,我們在進行理論研究時應當懂得有所取舍。事實上,“實質解釋”正遇上“形式解釋”的有力挑戰,司法解釋已明文規定三角型的欺詐行為不能以詐騙罪論處,“婚內強奸”在“王衛明強奸案”后再也沒有聽到有新的判例,隨著“二奶型”的非婚姻同居行為的大量出現,所謂“法律婚加事實婚”就是重婚罪的判例難覓蹤影,一個許霆案引起的激烈爭論足以使我們今天的司法實踐有必要進行反思與內省。于是在涉及一些刑民交雜案件和刑民法律關系并列案件的處理過程中,我們不是從基本的理論邏輯起點作為切入點,而是以其他案件的判決結果作為“邏輯終點”的依據,這種觀念的作祟對我們的司法實踐會有負面的影響,這應當引起我們的注意和警惕。
注:
1吳加明:《合同詐騙罪與意見代理之共存與釋論——一起倒賣房屋案引發的刑民沖突及釋論》,《政治與法律》2011年第11期。該案大致案情為:被告人龔某因賭博對外欠他人賭債,遂與丁某共同商議將龔某之父龔某某所有的一間房室出售后歸還賭債。被告人龔某、丁某經預謀后,至某公證處,由龔某冒充其父,辦理委托丁某持上述虛假委托公證書,以及龔某交付的其父身份證、房產證,與王某簽訂房地產買賣合同,騙取購房款人民幣43.5萬元,并將該房產過戶至王某名下。所獲錢款揮霍一空。
2參見[日]木村龜二主編:《刑法學詞典》,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684頁。
3轉引自趙秉志主編:《侵犯財產罪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652頁。
4尹曉靜:《財產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之否定》,《政治與法律》2011年第11期。
5沈家本:《歷代刑法志·晉書·刑法志》。
- 政治與法律的其它文章
- 論血液樣本證據的特性及其采集司法程序的完善
- 勞動爭議調解機制的構建:北侖經驗與啟示
- 原共同共有人優先購買權的解釋適用及其存廢*本文系中國政法大學青年教師學術創新團隊資助項目“中國民法典:歷史梳理與解釋適用”的階段性成果。
- 從檢察監督的兩重性看訴訟職權與監督職權的分離*本文為司法部一般課題“我國社會主義糾紛預防與治理機制整合問題研究”(項目編號:09SFB2031)的研究成果之一。
- 授權依據瑕疵行政行為的立法追認*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教育部青年基金項目“違法行政行為治愈制度研究”(項目編號:11YJC820163)、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行政法治愈制度研究”(項目編號:2010SJB82001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 論行政法學中“行政過程”概念的導入——從“行政行為”到“行政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