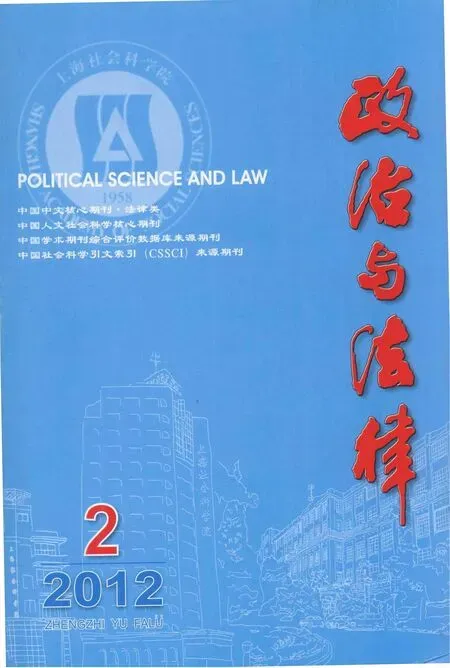“坦白從寬”入律之法理研究與實踐操作
王宇展 黃伯青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上海200070)
《刑法修正案(八)》將刑事政策中存在已久、實踐中一直作為酌定情節的坦白予以法定化,即增加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犯罪嫌疑人雖不具有前兩款規定的自首情節,但是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從輕處罰;因其如實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別嚴重后果發生的,可以減輕處罰。”自《刑法修正案(八)》實施以來,有關坦白的實踐操作分歧較大,難以統一。筆者擬在實踐的基礎上,結合刑法基礎理論及立法原意對入律后的“坦白”進行探索與思考。
坦白情節的法定化是貫徹和落實我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需要,體現寬的一面。坦白從寬是自首從寬的邏輯延伸,坦白情節的法定化有利于實現刑法的公平,保障量刑的公正;有利于鼓勵犯罪嫌疑人盡早交代犯罪事實,協助偵破案件,節省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鼓勵犯罪嫌疑人積極坦白,實現刑罰的目的。“坦白從寬”政策的法定化也是對我國《刑事訴訟法》即將引入的“沉默權”制度的有益補充。從西方發達國家實行“沉默權”的實踐看,“沉默權”是一把“雙刃劍”,具有加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保護,防止司法機關濫用職權的積極價值功能,但是絕對的“沉默權”也具有消極的一面,即不利于偵查機關獲得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不利于及時查清案件事實、提高訴訟效率。“沉默權”的本意是禁止偵查機關為了獲得供述而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強迫性手段,對偵查機關的偵查權進行一定程度的限制,而不是鼓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警察對抗。所以為了減少和消除“沉默權”帶來的消極影響,世界各國一般都會對“沉默權”加以適當的限制。如英美的辯訴交易制度、日本的起訴便宜主義制度、意大利的簡易程序處刑制度,以及各國量刑上的刑罰個別化,都體現了鼓勵供述的精神,實際上也是間接地對沉默權進行制約。“坦白從寬”正好是符合我國國情的彌補沉默權缺陷比較理想的配套措施之一。這項政策旨在引導、鼓勵真正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實陳述案情對于準確、及時地查明案件事實具有積極作用。所以將“坦白從寬”上升為法定從寬情節與“沉默權”制度結合起來,可以使二者相輔相成、取長補短。1
一、坦白成立條件之法理研究
(一)坦白的時間界限
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規定,一般自首的主體是“犯罪分子”;第二款規定,準自首的主體是“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第三款規定,坦白的主體是“犯罪嫌疑人”。在《刑法修正案(八)》出臺的過程中,曾有意見認為應將坦白的主體等同于一般自首或者準自首的主體,然而立法最終采納了“犯罪嫌疑人”這一稱謂。立法的設計顯然縮小了坦白的成立范圍,但筆者以為這樣的設計卻不失合理性、科學性,理由如下。一是坦白的功能在于鼓勵犯罪嫌疑人認罪悔罪,幫助偵查機關及時收集證據,偵破案件,節約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進入審判階段時,一方面犯罪嫌疑人悔罪認罪的主動性、徹底性難以體現,另一方面從法的經濟價值分析,此時坦白的積極功能大打折扣,遠低于自首,故對坦白的時間把握應比自首嚴格。將坦白的時間前置,更有利于發揮坦白的功能,更為嚴謹,也更符合立法的宗旨和精神。二是庭審中的如實供述仍可酌情從寬處罰。立法將坦白限制在庭審之前,是為了與當庭自愿認罪的情節相區別。當庭自愿認罪使得庭審因此得以簡化,體現了訴訟的經濟性要求,可以適當酌情從輕處罰。對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關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被告人認罪案件”的若干意見(試行)》和《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公訴案件的若干意見》均已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對于自愿認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從輕處罰。”
(二)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標準把握
坦白與一般自首除到案形式不同之外,均在條款中明確“到案之后如實供述自己罪行”。故如何把握和理解“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實質內涵是準確認定坦白成立的關鍵。具體應當結合自首中關于“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內涵來認定,理由如下。第一,舉輕以明重。對于坦白中“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掌握不能低于自首的要求,相對于自首,坦白所反映的主觀惡性更重,如果對“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掌握輕于自首,則會使主觀惡性更輕的量刑情節的成立條件要求更為嚴格,反之,主觀惡性更重的量刑情節卻要求更為寬松從而導致刑罰適用的失衡。第二,從刑法體系解釋的角度看,為避免斷章取義、達到整體協調,應將刑法第六十七條作為一個整體理解、看待,同一條文中的不同條款間的兩處“如實供述自己罪行”應作相同含義、同一性的解釋,這是文本邏輯和同一律的要求,也是刑法實現公平、正義的要求。綜上,在新的司法解釋未出臺之前,應將坦白中的“如實供述自己罪行”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職務犯罪案件認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職務意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等相關司法解釋及規范性文件進行把握。具體而言,坦白中的“如實供述自己罪行”主要包括如下內容。
首先,“如實供述自己罪行”中的“罪行”是指主要犯罪事實。主要犯罪事實是指足以證明其行為構成犯罪并直接影響定罪量刑的基本事實和情節。其可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把握。
第一,如實供述影響定罪的犯罪事實。犯罪的性質主要取決于犯罪構成要件,是否如實交代主要犯罪事實應從犯罪構成要件的四個方面進行把握。易言之,犯罪嫌疑人只要將自己所犯罪行的構成要件事實、情節作了較為全面并符合客觀實際的陳述,而沒有在直接影響定罪的事實和情節上故意作虛假陳述、歪曲真相、避重就輕,即使其他一些細節上存在不一致、不準確,也應認定為如實供述。如犯罪嫌疑人具有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必須如實供述,否則將影響案件性質的判斷而不能認定為如實供述。如實供述自己的真實身份是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應有之義,否則,供述虛假的姓名,等于供述他人罪行,不能認定如實供述。《意見》對此也予以肯定,其將供述自己的身份情況納入“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范疇,具體包括姓名、年齡、職業、住址、前科等情況。對于供述的身份情況有錯誤的,若與身份情況無重大差別且不影響定罪量刑的,應可以認定;若隱瞞自己真實身份影響對其定罪量刑的,一般不予認定。再如犯罪嫌疑人在奪取他人財物過程中,實施了威脅行為,但其在供述中隱瞞了實施威脅行為這一情節,那將會使重罪(搶劫罪)變為輕罪(搶奪罪),因為哪怕威脅行為僅僅是一句話、一個動作,也足以影響到此案的定性。
第二,如實供述影響量刑的犯罪事實。從刑法分則所規定的具體刑種和處刑原則看對不同的犯罪所規定的影響量刑的情節也不盡相同。如一些侵犯財產犯罪,影響量刑的情節主要是犯罪數額,諸如此類的規定還有“情節嚴重”、“重大損失”等等。筆者認為,“影響量刑的犯罪事實”應當是影響量刑層次的犯罪事實,如犯罪嫌疑人持槍搶劫,卻未交代持槍,此時不能視為如實交代了影響量刑的犯罪事實,因為兩者的量刑層次是不同的,普通搶劫法律規定的處刑是十年以下,而持槍搶劫是十年以上。在司法實踐中,針對不同的案件,影響量刑的犯罪事實是有差異的,這就要根據我國刑法所規定的處刑原則和量刑層次區別對待,具體案件具體分析,才能正確把握犯罪嫌疑人交代的犯罪事實是否屬于如實交代了影響量刑的犯罪事實。如朱某故意傷害案2中,被告人朱某與被害人王某發生糾紛,并且使用鐵棍擊打被害人,致被害人王某多處輕傷,且左腿骨折,經鑒定為重傷被告人朱某到案后如實供述其與被害人王某發生糾紛并毆打被害人王某的犯罪事實,但否認其使用器械造成被害人王某重傷的犯罪事實,辯稱系被害人自己摔倒所致。經調查數名證人指認朱某持械毆打被害人王某。鑒于朱某避重就輕,缺乏認罪表現,就不應認定為如實供述自己罪行。
此外,犯罪嫌疑人多次實施同種罪行的,應當綜合考慮已經交代的犯罪事實與未交代的犯罪事實的危害程度,決定是否認定為如實供述主要犯罪事實。畢竟對于多次實施同種罪行的犯罪分子,不能要求其到案后將全部罪行一次性交代清楚,應當允許其有一個逐步回憶、考慮的過程。主要犯罪事實之主要是相對于次要而言,如果用百分比表示主要是超過50%。3故對于到案后沒有交待全部犯罪事實的,但是如實交代的犯罪情節明顯重于未交代的犯罪情節,或者如實交代的犯罪數額明顯多于未交代的犯罪數額,一般應認定為如實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無法區分已交代的與未交代的犯罪情節的嚴重程度,或者已經交代的犯罪數額與未交代的犯罪數額相當,一般不認定為如實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
其次,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實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外,還應當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則應當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實,才能認定為如實供述。
再次,對“如實供述自己罪行”中的供述態度的理解要掌握供述的時間和誠實度。有些犯罪嫌疑人被動到案后并非主動坦白,偵查機關不出示證據,就不交代,出示多少證據,交代多少犯罪事實。因此,在偵查機關已經掌握主要犯罪事實,并且向犯罪嫌疑人出示證據后,其才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不能認定為坦白。值得注意的是,偵查機關已經掌握主要犯罪事實,但在偵查機關尚未出示相關證據之前,犯罪嫌疑人一到案后,立刻如實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可以認定為坦白。
(三)以接受國家審查和裁判為隱含前提
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處理當前自首和有關問題具體應用法律的解答》曾將“接受國家的審查和裁判”作為自首成立條件之一,1997年刑法修訂后,立法并未將該要件予以明確,但這并不代表自首的成立不需要以接受國家的審查和裁判,而是自動投案、如實供述本身就蘊含著接受國家的審查和裁判為前提,立法如此設計不僅表達上更科學,避免畫蛇添足之嫌,而且也防止了由此而可能給司法實踐帶來的危害和混亂,因為實踐中曲解執行“接受審查和裁判”要件,妨害自首制度正確貫徹執行的情況并不鮮見。《解釋》中關于“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認定為自首”;“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并如實供述自己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認定為自首,但在一審判決前又能如實供述的,應當認定為自首”的規定也接受了這一觀點。鑒于相同的道理坦白中的“如實供述自己罪行”也需以“接受國家的審查和裁判”為隱含前提,即如實供述本身就不能翻供。4
(四)坦白的到案形式
坦白的到案形式是被動到案。結合司法實踐,被動到案主要有以下三種情況:一是被司法機關采取強制措施;二是被司法機關傳喚到案;三是被公民扭送到案。在這里,被采取強制措施不限于拘留和逮捕,還包括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拘傳、取保侯審和監視居住措施此外,傳喚作為司法實踐中經常采用的通知犯罪嫌疑人接受詢問的一種形式,通常是在司法機關已掌握了犯罪人及其罪行的情況下采用的,一般認為是被動到案。但有例外——犯罪嫌疑人因司法機關捎帶口信或者接到電話通知后,自動到司法機關接受詢問或者調查因口頭或電話通知不屬于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強制措施,所以符合自動投案的特征。
二、實踐操作中的若干問題及應對
(一)坦白的具體認定
犯罪嫌疑人被動到案后,如實供述后又翻供,但在提起公訴前又如實供述,能否認定為坦白。翻供就是對原來如實供述的否定,即未如實供述,反映了犯罪嫌疑人拒絕接受國家的審查和裁判,故此依法不認定為坦白,但是在提起公訴前又能如實供述的,其坦白的時間節點仍符合坦白成立的時間要件,故此種情形應認定為坦白。
犯罪嫌疑人被動到案后,如實供述后又翻供,但在提起公訴后進入審判階段又如實供述,能否認定為坦白。理由同前,犯罪嫌疑人首先拒絕接受國家的審查和裁判,后在審判階段的如實供述又因不符合坦白成立的時間條件,故此種情形不構成坦白,其在庭審中的如實供述只能作為當庭認罪情節予以對待。
犯罪嫌疑人被動到案后,未如實供述,但在移送審查起訴或者提起公訴之前如實供述的,能否認定為坦白。對此應該參照《意見》中第二條第三款關于“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認定要求進行判斷,即如實供述是在司法機關掌握其主要犯罪事實并出示證據之前還是之后主動交代的。如在李某故意傷害案5中,李某與王某、錢某斗毆,廝打中,王某用刀刺李某,李某奪過刀子向錢某身上猛刺數刀致錢某死亡。李某到案后有六次供述:前四次訊問中堅稱是王某持刀扎他時,誤扎死了錢某;經過一段時間,在后二次訊問中又如實供述。李某這種情況能否認定“如實供述”,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李某是在何種情形下如實供述自己罪行,如果李某作了虛假供述后,公安機關經進一步收集證據,確定李某是殺人犯,李某原供述不實,在公安人員揭穿其謊言后才被迫承認犯罪事實,當然不能認定為如實供述。因為犯罪嫌疑人李某的供述對幫助司法機關偵破案件、認定犯罪并無重大價值不能體現節約司法資源的宗旨,也體現不出犯罪嫌疑人李某悔罪認罪的主動性和接受國家的審查和裁判的意愿。如果本案中李某雖然在前四次說謊,但在公安機關未經進一步偵查收集證據,尚未揭穿其謊言時就在之后訊問中如實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其后再也沒有翻供,則應當認定為如實供述。畢竟強求犯罪嫌疑人一到司法機關就必須認罪,不能有任何的思想斗爭或者猶豫,不切合司法實際,也不符合人趨利避害的本性,應允許犯罪嫌疑人到案后有一定時間的內心掙扎。
犯罪嫌疑人被動到案后,未如實供述,但提起公訴后如實供述被起訴之罪的,不能認定為坦白。提起公訴意味著司法機關已經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主要犯罪事實,并且也已向犯罪嫌疑人出示了證據,如前述理由,不能認定為坦白。但是對其在庭審中的如實供述,可以作為當庭自愿認罪的酌定情節處理。
在提起公訴之后,被告人如實供述了司法機關尚未掌握與起訴之罪同種的其他罪行,能否認定為坦白。雖然檢察機關已經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訴,如實供述的時間點已不在偵查、審查起訴階段,但由于被告人如實供述的是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其他同種罪行按照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對其所供述的內容應當啟動另一個刑事訴訟程序予以查證、追訴,故該如實供述應屬于坦白。
犯罪嫌疑人被動到案后,如實供述且具有較大的積極作用甚至避免特別嚴重后果的發生,后又翻供,直到庭審結束均未再如實供述。顯然,這種情形不能認定為坦白,也不能以當庭自愿認罪情節酌情處罰,但是對于如實供述所產生的積極影響,在量刑的時候可以酌情予以考慮。
(二)坦白從寬的把握
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三款規定,坦白原則上可以“從輕處罰”,但如果“避免特別嚴重后果的發生”,可以減輕處罰。對于坦白應當根據犯罪事實、情節、性質、坦白的時間、坦白的程度、坦白的態度、坦白對案件的意義等具體情況確定是否從寬以及從寬的幅度。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9月制定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規定,對于坦白,應當根據坦白的階段、如實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罪程度等情況確定從寬的幅度。
罪行的輕重是量刑的主要依據,犯罪一旦發生,犯罪事實便是客觀存在的。犯罪嫌疑人的坦白行為只是其認罪、悔罪、悔改心理態度的反映,僅能表明其人身危險性的弱化但其犯罪事實及其給社會造成的危害卻并不會因其坦白認罪而消失。這就決定了對具有坦白情節的被告人的量刑應如同對其他被告人的量刑一樣,仍要以犯罪事實作為確定刑罰的主要依據,最后處罰的輕重,主要取決于罪行本身的大小。筆者主張對坦白的被告人量刑時主要根據犯罪事實,決不意味著忽視坦白情節,而只是強調要把犯罪事實放在量刑時考慮的首位。這就正確地區分出犯罪事實和坦白情節這兩者在量刑中需要考慮到的不同因素。很顯然,犯罪事實是第一位的,坦白情節是第二位的。如對于罪行極其嚴重,罪該判處死刑的,即使有坦白情節,也可不從輕處罰。故罪行的輕重是決定坦白是否從寬處罰以及從寬處罰幅度的根本因素。
關于坦白的時間,主要是考慮犯罪嫌疑人被動歸案后,是立刻交代犯罪事實,還是經過一段比較長的時間狡辯,抑或經過一番教育思想斗爭才交代。坦白時間的早晚和背景不同,不僅說明了犯罪嫌疑人對自己所犯罪行悔悟的早晚,反映其人身危險性程度,還可能直接影響司法資源效益和刑事訴訟效率,從寬處罰也是需要區別對待的。
關于坦白的程度,是指犯罪嫌疑人是徹底交待全部罪行還是只交代主要罪行,每交代一件罪行是較為全面客觀地交代主要事實和情節還是避重就輕。坦白程度的不同,反映犯罪嫌疑人是真心悔改還是想蒙混過關,是被政策感召還是鉆政策空子。對于真心悔改的與避重就輕的從寬考慮自然存在差異。
關于坦白對案件的意義,是指犯罪嫌疑人的坦白交待在全案的證據中作用如何,是一般證據、重要證據還是關鍵證據。證據意義和作用不同,客觀上影響司法機關認定和處理案件。有的案件沒有犯罪嫌疑人的坦白交待,司法機關照樣掌握其罪行,或證據確鑿犯罪嫌疑人不能不供,這種情況下,犯罪嫌疑人的坦白對破案定性的作用相對要小;另外有些案件,沒有犯罪人的坦白交待,司法機關就難以充分掌握其罪行證據,或者難以詳盡無疑地掌握其犯罪事實,在這種情況下,犯罪人的坦白行為,對犯罪事實認定的作用就相對較強。坦白的客觀效果不同,對司法的積極意義也不同。如在張某故意殺人案6中,張某為謀錢財殺害金某,公安機關根據相關證人證言等證據抓獲張某,張某到案后否認犯罪公安機關經進一步偵查,在其暫住處發現金某的隨身財物,張某遂如實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實,并帶領公安機關辨認了掩埋被害人金某尸體及兇器的地點,因相關尸體和兇器是據以定案的重要證據,故張某的供述對于全案的及時偵查、及時結案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對此從寬的幅度要相對較大。
此外,針對“避免特別嚴重后果的發生”,筆者以為,從文義解釋的角度看,避免后果發生,不外乎是避免人員傷亡、財物損失以及其他后果的發生,對此,“避免特別嚴重后果的發生”應該包括:避免人員重傷、死亡的;避免特別巨大經濟損失的;其他特別嚴重后果的發生。對于坦白,并非只要“避免特別嚴重后果發生的”就一般應當減輕處罰,是否減輕處罰,必須結合罪行應當判處的刑罰分析:如果罪行應當判處的刑罰遠遠高于法定最低刑,有足夠的從輕處罰空間,就不必減輕處罰;如果罪行應當判處的刑罰接近法定最低刑,沒有從輕處罰的空間,就應當減輕處罰。7
(三)坦白與自首、立功的區別
一般來講,以犯罪嫌疑人到案的形式可區分坦白與自首。但是在被動歸案的情況下并不能否定自首的存在,還必須結合供述的內容。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釋》規定,對于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罪行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或者判決確定的罪行屬于不同種罪行的,以自首論。對于如實供述同種罪行的,可酌情從輕處罰。換言之,被動到案后,如實供述的內容為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其他不同種罪行的,屬于自首,否則均屬于坦白。自首和坦白所反映的犯罪分子人身危險性的程度有所不同。自首表明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險性相對較輕。因此,必須把坦白與自首之間拉開量刑幅度。如果二者同等量刑,往往使犯罪嫌疑人在被抓獲歸案之后再坦白,從而降低了自首的可能性,不利于鼓勵犯罪嫌疑人改過自新,也不利于節約司法成本。因此,必須將二者適當拉開量刑幅度。
司法實踐中,如何區分坦白中如實供述的必然交代與獨立于必然交代的提供同案犯下落的協助行為,是區分坦白與立功的關鍵,也是審判實踐中的難點。如在魯某故意殺人案8中,犯罪嫌疑人魯某因失戀遷怒于他人,與孫某共謀持刀將郭某殺死后逃匿。魯被抓獲到案后,又主動交代了孫某的藏匿地點。公安機關據此抓獲孫某。一種意見認為,魯某主動交代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其他同案犯的藏匿地點,是立功;另一種意見認為,魯某交代共同犯罪事實,必然要如實交代同案犯的姓名、藏匿地址等,屬于坦白。坦白要求如實供述其犯罪事實,共同犯罪中還要求對同案犯參與犯罪的事實加以供述,《解釋》第六條規定:“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到案后,揭發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實的,可以酌情予以從輕處罰。”但供述到什么程度,沒有任何的法律規定。這里特提出一個問題探討。如對共同犯罪事實的供述,是否要求供述同案犯的其他基本情況,如住址(包括暫住地)、電話籍貫、家庭成員等。筆者認為,我國地廣人多,有許多同名同姓的人,犯罪人要如實供述同案犯犯罪事實,必須要涉及同案犯的具體信息,故對同案犯的基本情況供述是如實供述的必然要求。《意見》第五條第二款對此予以了進一步的明確,即“犯罪分子提供同案犯姓名、住址、體貌特征等基本情況,或者提供犯罪前、犯罪中掌握、使用的同案犯聯絡方式藏匿地址,司法機關據此抓捕同案犯的,不能認定為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同案犯”。此外,如何界定立功中“協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意見》第五條第一款規定,按照司法機關的安排,以打電話、發信息等方式將其他犯罪嫌疑人(同案犯)約至指定地點按照司法機關的安排,當場指認、辨認其他犯罪嫌疑人(同案犯)的;提供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其他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聯系方式或者藏匿地址等,屬于立功。
(四)坦白與庭審中如實供述的并存處理
《刑法修正案(八)》將庭審中的如實供述排除在坦白之外,而司法實踐中二者經常交織在一起,要正確處理二者并存時的關系,對于司法實踐具有重要的操作價值。在檢察機關提起公訴之前,犯罪嫌疑人在司法機關掌握其主要犯罪事實并且向其出示相關證據之后才供述并且延續至庭審中的如實供述,以及在檢察機關提起公訴之前未如實供述且到了庭審才如實供述的,該兩種情形屬于當庭自愿認罪情節,不存在與坦白情節并存的問題,可酌情從輕處罰。對于在審判前坦白的基礎上,庭審中也是如實供述的,應該一并作為坦白情節處理,因為坦白情節與當庭認罪原則上不能重復評價,即對于同一犯罪事實如果已經認定為坦白了,即使當庭認罪,也不宜再單獨予以從輕處罰,此其一;其二,庭審中的如實供述是坦白的延續,屬于同一個刑法量刑情節的表現,也不應當分別評價。
注:
1參見張正君、錢進、張東偉:《坦白從寬政策應在刑事立法中充分體現》,《檢察日報》2010年8月16日。
2參見上海市閘北區人民法院滬(2011)閘刑初字第730號刑事判決書。
3參見周峰、薛淑蘭、孟偉:《〈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問題的意見〉的理解與適用》,《人民司法》2011年第3期。
4參見楊國章:《論“坦白從寬”的法律化》,華東政法大學2001年碩士學位論文,第31頁。
5參見上海市閘北區人民法院滬(2011)閘刑初字第378號刑事判決書。
6參見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0)滬二中刑初字第76號刑事判決書。
7參見張軍主編:《〈刑法修正案(八)〉條文及配套司法解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91頁。
8參見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1)滬二中刑終字第634號刑事判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