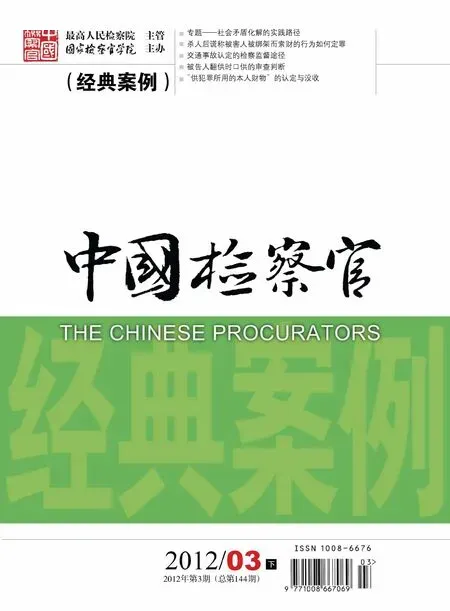騙租車輛并質(zhì)押給他人實(shí)施詐騙的犯罪金額認(rèn)定
文◎丁琢之
騙租車輛并質(zhì)押給他人實(shí)施詐騙的犯罪金額認(rèn)定
文◎丁琢之*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張某、趙某結(jié)伙,經(jīng)事先預(yù)謀,于2011年4月間,在了解到向汽車租賃公司租賃車輛到期,租賃人不歸還所租車輛時(shí),租賃公司可以通過車載GPS自行取回車輛這一操作流程后,由被告人張某向不同的汽車租賃公司先后租賃小轎車3輛,并偽造身份證、行駛證、車輛登記證等,再由被告人趙某冒充車主,謊稱將租賃車輛作為債務(wù)的擔(dān)保并質(zhì)押給他人,先后從三名債權(quán)人處共計(jì)騙得錢財(cái)人民幣183000元,贓款由兩名被告人花用殆盡,嗣后租賃車輛均被有關(guān)汽車租賃公司自行取回。
二、分歧意見
對于本案中被告人張某、趙某實(shí)施的行為性質(zhì)上構(gòu)成詐騙罪當(dāng)屬無疑,但對于其犯罪金額的認(rèn)定,則存在兩種不同觀點(diǎn)。
第一種觀點(diǎn)認(rèn)為,在通常情況下,汽車租賃公司不允許租賃人將所租車輛質(zhì)押給他人,而被告人張某、趙某在租賃車輛時(shí),向汽車租賃公司隱瞞了其欲將車輛用于質(zhì)押的真實(shí)目的,使得租賃公司產(chǎn)生錯(cuò)誤認(rèn)識并交付車輛,被告人從而非法占有了車輛,此后冒充車主將車輛質(zhì)押的行為,是對贓物的處理,屬于不可罰的事后行為,因此被告人詐騙犯罪的金額應(yīng)當(dāng)是車輛的價(jià)值。
第二種觀點(diǎn)認(rèn)為,被告人張某、趙某明知租賃車輛不能質(zhì)押給他人,仍偽造證件、冒充車主,虛構(gòu)事實(shí)、隱瞞真相,以車輛質(zhì)押為名騙取對方錢財(cái),因此其詐騙犯罪的金額應(yīng)當(dāng)是其實(shí)際騙得的數(shù)額,即人民幣183000元。
本案中從表面上看,被告人似乎是實(shí)施了兩個(gè)詐騙行為,即先通過詐騙汽車租賃公司而獲得車輛,后又通過詐騙他人而獲取錢財(cái),但并不能因此按照兩罪論處,而對于本案犯罪金額的爭議,實(shí)際上反映的是對于上述兩個(gè)詐騙行為之間關(guān)系的不同理解。
三、評析意見
筆者贊同第二種觀點(diǎn),犯罪金額的認(rèn)定離不開對行為性質(zhì)的正確評判,而對本案被告人行為的評判應(yīng)當(dāng)依照主客觀相統(tǒng)一的原則來進(jìn)行。
(一)被告人騙取車輛的行為不具有非法所有的目的
我國《刑法》沒有規(guī)定詐騙罪必須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司法實(shí)踐中一般都是將非法占有作為詐騙罪的犯罪目的來看待,并且包含在詐騙罪的主觀構(gòu)成要件之中。但是此處“占有”一詞的具體含義,則是需要探討的。
詐騙罪與盜竊罪、職務(wù)侵占罪、挪用資金罪等犯罪類似,在行為類型上屬于侵犯財(cái)產(chǎn)犯罪中的取得財(cái)產(chǎn)型的犯罪。取得財(cái)產(chǎn)型的犯罪也只能由故意構(gòu)成,即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非法占有目的包括兩種情況:一是以非法暫時(shí)占有(狹義的占有)、使用為目的,如挪用資金罪;二是以不法所有為目的,如搶劫罪、盜竊罪、詐騙罪、搶奪罪等等[1]。之所以要做這樣的區(qū)別,是因?yàn)閷?shí)踐中存在大量的不以“所有”為目的的騙用、盜用行為,這類行為的行為人客觀上雖然實(shí)施了騙取、竊取等非法行為,但是主觀上卻并不具有將財(cái)物“據(jù)為己有”等徹底排除權(quán)利人所有權(quán)或合法占有狀態(tài)的目的,而且一般也都能將財(cái)物歸還給權(quán)利人,使權(quán)利人的所有權(quán)或者合法占有恢復(fù)原先的狀態(tài),因此這種對于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的侵犯并未達(dá)到值得課處刑罰的程度,也就沒有認(rèn)定為犯罪的必要性。由此可見,詐騙罪的主觀目的只能是非法所有。
在本案中,被告人騙車的目的僅在于將車輛作為一種犯罪工具暫時(shí)占有和使用,而并無徹底排除租賃公司對車輛所有權(quán)的意思,實(shí)際上也沒有導(dǎo)致車輛滅失,因此本案被告人對所騙車輛并不具有非法所有的目的。
(二)本案被告人實(shí)質(zhì)上侵犯的不是汽車租賃公司對租賃車輛的所有權(quán),而是“債權(quán)人”對被騙錢財(cái)?shù)乃袡?quán)
被告人前后的兩個(gè)欺詐行為是基于一個(gè)總的犯罪故意實(shí)施的,即以非法所有債權(quán)人錢財(cái)為目的,明知自己冒充車主、使用假證的行為會使債權(quán)人陷入錯(cuò)誤認(rèn)識進(jìn)而發(fā)生向其交付貨幣的結(jié)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jié)果發(fā)生。在此故意支配下,被告人實(shí)施的騙取車輛的行為,實(shí)質(zhì)上是包含在整個(gè)詐騙債權(quán)人這一犯罪行為整體中的手段行為、預(yù)備行為。而且被告人實(shí)施這一手段行為、預(yù)備行為時(shí)并不具有非法所有租賃公司車輛的目的。雖然被告人使用了虛構(gòu)事實(shí)、隱瞞真相的欺詐手段從汽車租賃公司處騙得了車輛,但是被告人在明知車輛逾期不還時(shí)汽車租賃公司可以通過車載GPS定位設(shè)備自行找回車輛的情況下,并沒有采用拆除設(shè)備、隱匿車輛等手段妨害租賃公司尋找車輛。而且實(shí)際上被告人支付了車輛的租金,汽車租賃公司也均自行找回了車輛,因此汽車租賃公司對于租賃車輛的所有權(quán)并未受到實(shí)質(zhì)上的侵害。
在真實(shí)的債權(quán)擔(dān)保關(guān)系中,雖然債權(quán)人失去了對貨幣的所有權(quán),但由于作為債權(quán)擔(dān)保的質(zhì)物是債務(wù)人(出質(zhì)人)有權(quán)處分的財(cái)產(chǎn),因此當(dāng)債務(wù)人到期不履行債務(wù)時(shí),債權(quán)人根據(jù)民事法律的規(guī)定,可以采用拍賣、轉(zhuǎn)讓質(zhì)物等方式,就質(zhì)物的價(jià)值優(yōu)先受償,保障債權(quán)的實(shí)現(xiàn)。而反觀本案中的“債權(quán)人”,首先他們基于被告人的欺騙而產(chǎn)生了因?yàn)楸桓嫒耸擒囕v所有權(quán)人,所以有關(guān)車輛可以作為債權(quán)擔(dān)保的錯(cuò)誤認(rèn)識,進(jìn)而向被告人交付了錢財(cái),并暫時(shí)占有了作為質(zhì)物的車輛。但這種占有實(shí)際上是沒有保障的,客觀上汽車租賃公司自行取回車輛的行為,使得這種占有不可能再繼續(xù)下去,也使得債權(quán)人的債權(quán)由一種“有擔(dān)保”的債權(quán)變成了無擔(dān)保的債權(quán)。其次,被告人所采用的種種隱瞞真實(shí)身份的方式,也說明其主觀上并沒有向債權(quán)人到期履行債務(wù)的意思,客觀上被告人也沒有向債權(quán)人返還錢財(cái),因此債權(quán)人與被告人之間并不存在真實(shí)的借貸關(guān)系,被告人的行為也并非民事欺詐,而是以非法所有債權(quán)人錢財(cái)為目的的刑事詐騙。由此可見,被告人的行為實(shí)質(zhì)上侵害的是債權(quán)人對被騙錢財(cái)?shù)乃袡?quán)。
(三)被告人欺詐債權(quán)人的行為并非不可罰的事后行為
所謂不可罰的事后行為,又稱共罰的事后行為,是指在狀態(tài)犯的場合,利用該犯罪行為的結(jié)果的行為。如果孤立地看,符合其他犯罪的構(gòu)成要件,具有可罰性,但由于被綜合評價(jià)在該狀態(tài)犯中,故沒有必要另認(rèn)定為其他犯罪。[2]不可罰的事后行為這一概念,主要存在于大陸法系國家刑法理論以及我國臺灣地區(qū)刑法理論中,我國刑法理論沒有對此予以明確的解釋,一般認(rèn)為這種情況在我國大體上屬于吸收犯。比如,行為人盜竊槍支后又私藏槍支的行為,屬于吸收犯,也可謂不可罰的事后行為。又如,行為人盜竊財(cái)物后,又將所竊財(cái)物銷贓的,其銷贓行為被盜竊行為所吸收,也稱之為不可罰的事后行為。
近年來,我國刑法理論界對不可罰的事后行為也進(jìn)行了一定的研究,初步歸納了其法律特征:(1)該后行為形式上看似犯罪行為,但它與主行為一起,已被法律評價(jià)為一個(gè)整體,因此,實(shí)質(zhì)上已不具有獨(dú)立性;(2)該后行為是對主行為所造成的不法狀態(tài)的利用或保持,并且也是沒有侵害新的法益;(3)主行為的不法內(nèi)涵足以涵蓋后行為的不法內(nèi)涵,并且主行為對于法益的侵害要大于后行為,否則不屬于不可罰的后行為。[3]
對照上述有關(guān)不可罰的事后行為的概念及法律特征,本案中被告人將騙租的車輛質(zhì)押給他人的行為顯然并非屬于不可罰的事后行為。首先,被告人騙租車輛的行為由于不具有非法所有車輛的目的,欠缺犯罪主觀方面的要素,不能構(gòu)成犯罪,而之后將租賃車輛質(zhì)押的行為,則符合詐騙罪的主、客觀兩方面的犯罪構(gòu)成要件,具有刑事違法性,應(yīng)當(dāng)以詐騙罪論處,因此后行為并不能為前行為所吸收,而前行為卻恰恰包含在后行為的主、客觀內(nèi)容之中。其次,就法益侵害的角度而言,如果說被告人騙租車輛的行為侵犯了汽車租賃公司對車輛的占有(狹義)的話,那么這一法益隨著汽車租賃公司自行取回車輛,進(jìn)行自力救濟(jì)而得到了完全的恢復(fù),而被告人之后騙取債權(quán)人錢財(cái)?shù)男袨閯t侵犯了債權(quán)人對貨幣的所有權(quán),這一行為不僅明顯侵犯了另一新的法益,而且這一法益不能為前一法益所涵蓋,并隨著債權(quán)人失去質(zhì)物而失去了擔(dān)保,事實(shí)上債權(quán)人已不可能通過自力救濟(jì)的手段予以恢復(fù),因此被告人對這一法益的侵害程度也大于對前一法益的侵害程度。
由此可見,被告人的前行為雖然造成了其占有(狹義)租賃車輛的狀態(tài),而其后行為則利用了這種狀態(tài),但是前行為相對于后行為并不具有獨(dú)立性,被告人的前后行為可以為一個(gè)詐騙的故意所涵蓋,因此整體上應(yīng)當(dāng)評價(jià)為一罪,而這一詐騙罪實(shí)質(zhì)上侵犯了債權(quán)人對于貨幣的所有權(quán),因此被告人的詐騙犯罪金額也應(yīng)當(dāng)以其實(shí)際騙得的金額認(rèn)定。
注釋:
[1]張明楷,《刑法學(xué)》,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50頁。
[2]同注[1],第373頁。
[3]游偉、謝錫美,《論不可罰的前后行為》,《華東政法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2年第2期,第16頁。
*上海市虹口區(qū)人民檢察院[20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