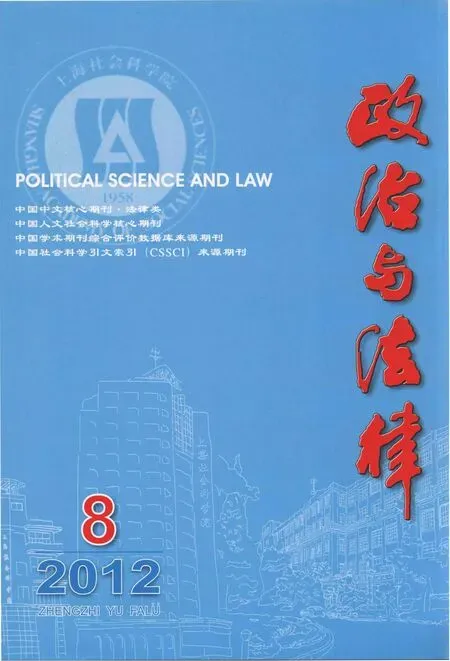論證券概念的擴大及對金融監管的意義*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項目“社會經濟變遷視野下的公司法結構與制度完善”(項目編號:12MSFJD820002)資助,特表感謝。
姚海放
一、問題的提出
在當前眾多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研究中,大多貫穿著一種思路:金融危機后以美國為代表的分業監管模式為適應綜合經營需要逐漸向統一監管模式轉變,中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也需采取相應變革措施,完善金融監管體系。筆者并非絕對否認金融統一監管模式的合理性,但對上述思路的論證方式仍然存有疑慮。第一,按照法律移植和制度借鑒的基本原理,僅有國外法制變革的現實而缺少對該制度在中國本土適應性的論證,提出法制借鑒的理由充分性是不足的。第二,金融體系的統分,起碼包括人員機構、經營業務、金融監管和法律規定等多個層面,并非是一項“統一”的理念或號召就能夠瞬時解決的宏觀問題,而應當選擇合適時機和步驟逐步完成。1這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我國1999年制定《證券法》時選擇美國式的分業經營、分業監管模式,按照金融產品保障、儲蓄和投資功能的基本分類,建立了“一行三會”為代表的金融監管體制。如今面對金融產品功能混合、金融業務綜合經營、金融集團機構發展的客觀現實,在采取逐步改進金融監管體制的方式下,如何區分金融產品功能以及確定相應金融監管機構將成為一項重要任務。此外,面對非正規金融的沖擊,銀行或證券監管部門是否應當介入、如何進行分工合作、如何對具體金融產品或行為定性管理等,也都是較為棘手的問題。筆者認為,上述問題的解決,僅有金融監管的宏觀理念和制度變遷描述是不足的,還必須深入到細節問題上,有必要從根本上擴張“證券”概念及范圍,這樣,才能對當下金融監管職責分工以及今后金融經營與監管的逐步融合,作出較為有力的回應。
二、中國《證券法》中“證券”概念的不足
按照2005年修改的《證券法》第2條對該法調整范圍的界定,該法調整“股票、公司債券和國務院依法認定的其他證券的發行和交易”、“政府債券、證券投資基金份額的上市交易”;同時,“證券衍生品種發行、交易的管理辦法,由國務院依照本法的原則規定”。
1999年《證券法》制定時,有一種觀點認為,《證券法》應當調整所有證券(包含其衍生品種)的發行、交易及相關活動;另有一種意見認為,“我國證券法所調整的證券關系主要是股票、公司債券等基本證券的交易活動,而對股票、公司債券的發行活動在公司法已作規定的基礎上,根據實踐中的新情況作出補充性規范。此外的其他證券,即政府債券、金融債券、投資基金券等,……需要另行制定法律、法規加以規范”。2立法者采用后一種調整范圍的觀點,稱此舉是基于“基本法理、立法慣例、現行體制和立法技術幾方面的綜合分析”。3這在學者看來屬于一種“過渡階段”立法。這種用經濟發展的“過渡階段”來解釋立法或修改法律的意圖并不具有充分的說服力,在修改《證券法》過程中對“適用范圍和適用對象的問題,已經成為執行《證券法》的一個非常關鍵性的問題”,“在沒有分散型法律、法規設計的情況下,統一型法律已經先期出臺了,其調整對象‘寬’比‘窄’好”。4然而,在2005年該法修改時,對法律調整的證券種類僅增加了“證券投資基金份額”一種;關于“證券衍生品種”的法律適用,《證券法》原則規定由“國務院依照本法的原則規定”。實踐中,僅有中國銀監會在部門規章的層次上于2004年《金融機構衍生產品交易業務管理暫行辦法》第3條中規定“衍生產品”是一種以“遠期、期貨、掉期(互換)和期權”為基本種類的金融合約,或者是包含上述一種或多種特征的結構化金融工具。修改后的《證券法》實施以來,國務院并未根據法律授權認定過“其他證券”的種類。總體上,我國目前《證券法》中的證券概念是以股票、債券為基本類型,相關證券發行、交易中的審查批準、信息披露、不當交易控制、法律責任等制度也基于此種證券概念的界定而構建。
面對以股票債券為基本證券形式而演化的金融衍生產品的新發展,現有立法中的證券概念顯然偏窄而不利于法律對金融實踐進行規制。國外法制經驗是,“多數國家和地區的證券法都對證券范圍有所規定,但通常是按照‘功能標準’對證券種類進行不完全列舉。功能標準,是指按照某種權利證書是否符合證券的基本屬性和功能來判斷其應否歸屬于證券,而不是按照該種證書是否被冠以證券之名而進行判斷。所謂不完全列舉,是指證券法只能列舉證券的主要和常見類型,而無法全部列舉各種證券形式”。5因此,有學者提出了需要擴大《證券法》中證券概念的建議,“在列舉法定證券種類的基礎上引入一般性的概念,為證券監管機關判斷某種金融投資商品是否屬于‘證券’提供判斷標準”。6如此,學理上需要探究說明的問題是,如果從列舉角度無法完整概括證券種類,是否可能設定兜底性條款或實質性標準來說明證券特征,以使監管執法及司法部門明確判斷金融產品是否具有證券屬性、是否適用證券法規范或比照相應原則進行規范管理。
三、證券概念的比較法研究
大陸法國家的法律傳統習慣于從上而下的體系構建和相關概念種屬確定或比較鑒別,以此確定某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學者通常從兩個層面提煉證券概念的特性。其一,證券是一種記載于某類介質上的權利憑證,由此其屬于法律中書證的范疇。由于證券法上證券通常表彰的是財產權利,并且按照該財產權利與證券介質之間的關系,證券概念被縮限在有價證券的范疇中。其二,證券是財產權利的憑證,其與民法上的物的概念具有密切聯系,兩者的區別是證券被等額劃分或標準化,以及隨之而來的是份額的自由轉讓,因此證券被認為具有標準化及流通性的特點。在大陸法學理中總結證券的特征為:證券是一種投資收益權憑證、是一種占有憑證、具有流通性和風險性。7學者進一步將有價證券區分為商品證券、貨幣證券和資本證券,并認為證券法中的證券為資本證券,而貨幣證券為票據法的調整對象。8
此種證券概念界定方式能夠勾畫出證券法上證券在民法書證或廣義證券體系中的地位,便于從形式上定位證券概念。然而,此種方法注重形式比較,沒有解釋出區分商品證券、貨幣證券或資本證券的實質,在足智多謀的金融投資者面前這種證券概念可能被突破。例如,美國SECV.W.JHoweyCo.案9(以下簡稱“Howey案”)中,美國最高法院認為該案中交易對象以果園和果樹等實物資產為表現形式,并不能排除法院對事實上存在證券的實質性的司法認定;而在RevesV.Ernst&Young10案(以下簡稱“雷維斯案”)中,作為投資工具的表現形式是農業合作社簽發的見票即付的本票,但在案件具體情境中美國最高法院依然將該案中的本票認定為證券。
以上述案件為例,筆者明顯感到,如果以大陸法慣常使用的證券形式概念和種類列舉方式,將會出現法律規制漏洞的問題。相較而言,以美國法為代表的證券法制較為注重法律關系的實質性,“聯邦最高法院采取了重經濟現實輕法律術語、重內容輕形式的分析方法。也就是說,不管你在形式上叫什么名字,是‘服務合同’還是‘買賣合同’,只要在經濟現實上與證券一致,就按證券論,要求登記披露,以保護投資者利益。反過來,即使其名字叫‘股票’,如果不具備股票的基本特征,還是不能按股票論”。11
美國證券法制中對證券的概念界定,實質上是采用雙層認定體制。首先,美國1933年《證券法》第2條a款及1934年《證券交易法》第3條a款第10項都有對“證券”種類的列舉式規定。其次,司法機關在具體案件中可以裁判認定證券的情形。盡管美國聯邦及州立法中對證券概念進行了頗為詳盡的列舉式規定,但實踐中具有證券性質的金融工具種類表現形式更為多樣。因此,司法機構承擔了在具體案件中判斷金融工具是否屬于證券以及是否需要接受證券法律規制的任務。美國聯邦法院通過判例,確立了幾項證券判斷的重要規則12:第一,盡管股票作為證券的一種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明確的,即股票的特征是按一定比例分享收益并享有投票權及承擔責任;但如果案件中金融工具不符合上述股票的基本特征,法院還應當判斷其是否屬于投資合同(investmentcontract)來判斷其是否屬于證券概念;第二,投資合同成為法院認定證券法列舉證券種類之外的金融工具,或是對金融工具證券定性存在爭議情形下的基本概念。事實上,美國借助投資合同這一含義不甚明確的概念,實現了法的穩定性和對經濟社會發展適應性的平衡,由司法機構承擔了面對實踐不斷產生、花樣翻新迅速的證券類金融工具性質的認定工作。
受美國證券法的影響,日本《證券交易法》第2條也采用列舉方式規定所調整證券的種類。13該條在詳盡列舉各種類有價證券之后,還概括性規定可適用證券交易法的“證券交易委員會因公益或保護投資者認為必要且適當,根據證券交易委員會規則規定的其他證券或證書”情形。為應對交易商品多樣化趨勢、重構資本市場與金融市場之間的秩序,特別是吸收證券化關聯商品的法律規制需要,日本1998年修改《證券交易法》時增加了第2條第18項,即在列舉第1-17項之外,法律概括性規定“斟酌流通性以及其他因素,為確保公益或保護投資者,認為有必要,政令(《證券交易法實施令》1條)規定的證券或證書”。142006年,日本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時,將“證券”定義擴展為“金融商品”的概念。盡管立法并未對“金融商品”進行明確定義,但為適應各種基金實踐需要而導入“集合投資計劃”定義,即在《金融商品交易法》第2條第2款第5項規定“集合投資計劃是指民法上的合伙、商法上的隱名合伙、投資實業有限責任合伙、有限責任事業合伙、社團法人的社員權以及其他權利,享有通過金錢出資進行的事業而產生的收益分配或該出資對象業務相關的財產分配的權利”。15盡管日本學者認為日本金融改革立法尚未最終完成,但從“集合投資計劃”概念的導入,到對有價證券概念定位采用“經濟實質性標準”的做法,顯然是受到美國“Howey案”判決的影響。這為日本《證券交易法》進行大幅度修改而變身為《金融商品交易法》,并使該法規制所有具有投資性金融商品,奠定了根基。
四、“投資合同”的概念及其構成
現代證券法的目的,逐漸從最初的規范證券市場秩序演進為規范秩序和保護投資者并重的格局。金融(證券)投資者保護理念對證券法的實質性內容產生了深遠影響。對投資合同概念的理解也需要置于這一前提之下展開。
從投資合同的具體概念以及構成來看,對其進行較為充分揭示的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Howey案”案。16該案中,美國Howey公司開發大片柑橘林,對外銷售果園土地,并允許購買果園者自愿與該公司簽訂一份管理服務合同,將所買果園委托給Howey公司負責種植、經營和銷售。如果果園投資者簽訂管理服務合同,未經公司同意,不得進入該土地,而只能在每年收獲季節接受公司經營收益。由于果園投資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地投資者,不可能親自進行果園管理,且鑒于公司技術和設備條件較為優越,因此有85%的投資者與Howey公司簽訂了此項管理服務合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判定該交易是否屬于“投資合同”進而應當進入證券的范疇時,提出了著名的“Howey檢驗標準”,即“檢驗標準應當是:該方案是否涉及到對于某項共同事業的金錢投資,而收益完全是來自他人的努力”。因此,金錢投資、共同事業、收益預期和完全來自他人的努力共同構成了Howey檢驗標準中的四大要素。在此基礎上,此后美國法院的判例主要沿循兩個方向發展。
第一,聯邦最高法院在雷維斯案中,闡述了Howey檢驗標準中四要素的結構問題,即采用“家族相似標準”來檢驗涉案金融工具是否屬于證券的問題。具體而言,家族相似標準一方面對Howey標準四要素的適用次序進行了邏輯分析,另一方面采用了更為靈活的權衡方法進行判斷,即具體分析各項因素在不同案件事實結構中所具有的不同地位,進行不同的解釋。雷維斯案所采用的家族相似標準,雖然沒能給出一個簡單而結論唯一的證券概念標準,實際上采用了類型化標準進行判斷,但在學者看來,這種做法“在界定證券范圍時,存在著大量的臨界狀態,基于類型模式的豐富性,法院可以考慮更多因素;由于不是刻板地如概念模式中涵攝那樣要求全部要素必須滿足,類型模式可以將各種狡猾的融資計劃納入證券監管的視野,權衡方法使證券法律更能應對金融創新給保護投資者這一證券法的根本宗旨帶來研究挑戰”。17當然,從根本上講,雷維斯案中采用的家族相似標準雖然比Howey標準更為寬松和靈活,但總體上兩者仍然大致相同。18
第二,盡管Howey標準四要素中的每一項在后續案件適用中都存在爭議或細節上的發展,但在“完全來自他人的努力”這一因素上的演變是最為突出的。如果完全按照字面解釋,證券的概念將完全排除投資者自身的努力,這不僅可預見地使Howey標準適用范圍大大減小,而且在如何界定投資者努力和他人努力方面也存在著不確定性。為此,美國法院一方面試圖將“完全來自他人的努力”擴張解釋為“主要依賴他人的努力”,將其轉換為“投資者以外的其他人所作的努力是否具有無可爭議的重要性,即影響到企業成敗的必要的管理方面的努力”的判斷。19司法試圖解決這一問題,但何種情形或程度屬于“主要”,依然具有一定的主觀判斷性質。另一方面,界定“完全來自他人的努力”因素標準在一定程度上還被轉換為界定“被動投資者”的問題,即可以從利潤來源來區分,也可以從交易構建的主動權安排來區分。20盡管對被動投資或者他人努力的重要性觀點仍然還存在一定的爭論,但該因素揭示了證券的重大本質及其對其進行法律規制的根本原因:投資者在交易關系中處于被動地位,而證券發行者獲取投資者資金進行經營,事關投資者的重大財產利益,因此證券發行者的資質、誠信狀態以及對投資行為監控就成為必要且關鍵的法律監管環節。
美國法上對投資合同概念的延伸后,將投資合同納入證券范圍,對其進行發行和交易監管,唯一理由就是保護投資者,因為證券發行人與投資者之間存在著嚴重信息及能力不對稱。通常情況下,投資者通過簽訂合同,將金錢投資于證券發行人所聲稱的事業時,其僅依賴他人的經營管理獲取收益,而無實質性了解、控制投資事業的渠道。在此情況下,一個公正的第三方監督(通常為政府監管)就成為必要。證券監管部門將此類投資合同,無論投資的具體表現形式是實物、票據或是其他,納入證券范圍,要求其進行登記、進行信息披露等,將有利于投資者了解自身所投資的事業,進而對投資做出理性判斷,以保障其權益。這種做法完全符合1929年美國聯邦《證券法》制定之初所采用的規制思路,即拋棄“價值規制”方案而采用羅斯福倡導的“信息披露管制”方案。當然,在例外情況下,如果投資者具有相應能力識別、控制投資事業,則可能排除將其作為證券投資者進行特殊保護的必要,例如:投資者具有投資經驗,或者與證券發行人具有特殊關系、或者有財產能力聘請專業人士幫助,則其能夠自己解決信息能力不足的問題,就不存在法律將投資合同納入證券進行管制的必要。因此,在立法或者案件適用中,將諸如機構投資者、小范圍私募的“投資合同”投資者等,排除在證券法適用保護之外,也就有了一定的合理性。
五、擴大“證券”概念的應用
美國證券法中投資合同的概念及其規制,其核心思想是:投資者使用金錢投資于標準化(或證券化)的資產,并主要依賴他人管理或努力而獲取收益,其交易客體應當納入證券發行與交易的監管范圍,以保護投資者權益。這為我國目前經濟金融領域的諸多法律問題提供了規制的新思路。
首先,實質證券概念及判斷方法的引入,可有效適用于我國各類交易所交易對象的定性及適用規則方面的問題。近年來,伴隨我國經濟發展和市場交易活躍,各地出現了大量產權交易、文化藝術品交易和大宗商品中遠期交易等類型的產權交易所。在現有法律規范不甚明確、地方政府利益驅動、各類產權交易所為拓展市場而相互競爭的情況下,為防范金融風險和穩定社會秩序,國務院于2011年11月發布《國務院關于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切實防范金融風險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決定》中規定的至關重要的清理整頓措施包括“除依法設立的證券交易所或國務院批準的從事金融產品交易的交易場所外,任何交易場所均不得將任何權益拆分為均等份額公開發行,不得采取集中競價、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進行交易;不得將權益按照標準化交易單位持續掛牌交易,任何投資者買入后賣出或賣出后買入同一交易品種的時間間隔不得少于5個交易日;除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外,權益持有人累計不得超過200人”。上述整頓措施實質上排除了財產權益證券化發行和交易的可能性,這在“交易所亂象”的背景下確實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手段。但是,從《決定》本身而言,一方面并未徹底排除交易所設立的可能性,規定對今后“凡使用‘交易所’字樣的交易場所,除經國務院或國務院金融管理部門批準的外,必須報省級人民政府批準;省級人民政府批準前,應征求聯席會議意見”;另一方面,從長遠來看,資產證券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合理化發展也是各國經濟發展的大勢所趨,因此,解決問題的關鍵就不單純是嚴厲地禁止,而應當是從制度設計角度考慮對其進行法律規制。從本質考慮,進入交易所交易的對象,無論其是實物資產、藝術品或文化產品,都具有兩方面的特征:第一,交易對象的標準化,即將交易對象的價值進行份額分割,以便于發行和交易,同時,資產標準化交易必然引發投資交易的公眾性特點;第二,投資者寄望于投資對象升值而獲益,而投資對象的升值往往并不主要決定于投資者個體的本身努力或控制。這些特征符合前述關于投資合同的特征,如果采用引導而非禁止的思路來解決問題,就有必要將其納入廣義證券概念范疇,在此類商品份額或財產權益交易過程中,確立證券監管部門的監管地位,并根據實際情況來確定對份額發行與交易進行審批、登記、信息披露或遏制惡意炒作等方面的具體要求。
其次,投資合同的概念也可運用于對企業通過系列合同安排向公眾進行融資行為的定性及法律規制方面。按照我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貸款通則》等法律法規的規定,貸款作為一項金融業務,貸款人必須是經銀行業監管部門批準,持有《金融機構法人許可證》或《金融機構營業許可證》,并經工商部門核準登記的主體;非金融機構的企業之間擅自辦理借貸或者變相借貸,由銀行業監管部門進行處罰。實踐中,無法獲得金融機構貸款的各類企業或公司,為解決經營所需資金而采用各種方法,其中一類為:集資方企業首先通過銷售某種產品獲取相對方資金,同時由相對方選擇與集資企業簽訂附加合同,構造另一項交易將先前集資款項及收益進行返還。目前我國對此類交易行為大都采取嚴格禁止的態度,通常按照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罪進行處理。然而,從企業的實際需求考慮,一定程度地開放企業資金借貸渠道,似乎又獲得部分學者與民眾的贊同,問題的關鍵還是政策制定者對民間金融開放的態度。筆者認為,目前我國嚴格禁止企業借貸的規定并不妥當,從國外立法看,鮮有禁止企業借款的立法例;從我國需求看,中小企業發展和民間資本投資渠道拓寬也要求適度放開企業資金借貸領域;從我國法律看,盡管金融法限制企業借貸資金,但《公司法》第149條有“將公司資金借貸給他人或者以公司財產為他人提供擔保”的表述,實際上也承認了公司的借貸能力。因此,開放企業向非金融機構的組織或個人借貸的渠道,可以作為立法發展的一個方向。當然,如果承認企業向非金融機構或個人融資的合法性,則問題的關鍵是如何防范金融風險、防止社會不穩定因素,關注的視角可以轉向“投資合同”的概念及法制。通常在上述方式的企業借貸融資方案中,集資方企業通過標準化合同關系獲取資金,并在合同中許諾給對方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回報;集資方發售標準化合同數量較大,具有公眾發售的典型特征;資金提供方主要不依靠自身努力來獲得承諾的回報,其對集資企業資金使用及其投資事業也缺乏了解和控制能力。基于經驗案例考察,這種融資方案的主要風險來源于:第一,集資企業存在明顯欺詐,如億霖集團非法經營案中聲稱購買林地的資金主要被用于揮霍和私分;第二,企業投資項目收益不足以支撐其經營成本與許諾回報的總和,導致投資事業發展不具有可持續性。實踐中出現風險的企業集資案件往往采用發展下線獲取收益(這往往被認為是傳銷)、以新貸換舊債的滾雪球方式等進行融資。如果將此類投資合同關系納入證券監管的范疇,要求其構成公開發行之前進行相關登記,至少可以解決上述集資企業明顯欺詐以及投資事業明顯不具有可持續性發展的情形,達到保護投資者利益的目的。當然,要求上述融資交易納入證券監管的登記及披露等管理,需要進一步提升監管機構的行政能力與效率。
此外,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目標之一是構建包括場內交易市場和規范的場外交易市場在內的多層次市場體系。場外市場交易以未上市的公司股票或債券為主,但也不排除出現非典型性證券交易的情況。同時,未來我國也必將逐漸開展金融衍生產品市場交易,以發揮其在轉移風險和價格發現方面的基本經濟功能,促進金融市場穩定發展、資源合理配置及資金有效流動。伴隨我國金融市場國際化發展、金融衍生品市場發展壯大,未來我國必然會出現諸多金融衍生產品類投資理財產品。按照學者的分類概括,法律意義上的金融衍生工具按照是否標準化區分為標準化衍生工具和非標準化衍生工具;對標準化衍生工具是否證券化又分為發行類衍生工具和非發行類衍生工具。21無論對金融衍生工具法律規制的立法模式如何,必然需要借助擴大化的證券概念涵蓋金融衍生工具,以使其發行交易納入證券監管的范圍。盡管上述場外交易市場、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場準入制度應當建立嚴格的“合格投資者”標準,22但不排除銀行等金融機構通過隱瞞風險等方式,將具有(或隱藏)一定衍生性交易在內的金融產品直接銷售給普通公眾,則在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律制度領域也必然涉及對金錢投資商品的定性與法律管轄歸屬問題。如果我國立法上仍然抱守狹義證券概念,就會發生金融監管機構對諸多金融理財產品定性不明、監管職責不分、損害金融消費者利益、最終損害金融市場健康發展的情形。
與此相關的一項問題是,我國立法上是否需要將現行的《證券法》修改或“升級”為金融服務法或金融商品交易法?有不少學者提出“應在修改或廢除現有的銀行法、保險法、信托法、證券法、投資基金法的基礎上,制訂一部綜合的《金融服務法》或《金融商品發行和交易法》”。23筆者認為,在綜合考慮立法、體制改革和民眾接受程度等各項成本的基礎上,一步跨越式地進入統一金融商品交易法在中國是有現實困難的。當然,如果固守現有狹義的證券概念,也是不足以滿足實踐需求的。因此,可行的道路是,在現有證券法制中適當擴張證券概念,引入實質性證券判斷的標準,將符合證券屬性的金融商品交易納入證券發行與交易監管法制軌道,以解決當務之急,并為進一步金融統一積蓄可能性。
六、代結語:監管機關的權力
承認中國《證券法》中“證券”概念需要引入實質性判斷標準以擴展其適用范圍,必然要涉及“認定交易關系的證券屬性”的權力安排問題。換言之,還需要考慮現有《證券法》采用“國務院依法認定的其他證券”的方式是否妥貼的問題。
首先,必須要承認,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其他發達國家的實踐看,現代國家的權利安排已從“權力分立、相互制衡”的分權模式日益發展為“行政中心主義”模式。有學者將其概括為從“麥迪遜觀點”向“施密特觀點”的轉變,即認為受政治條件限制,包括公眾對迅速行動的需求、大量不確定性以及明智的立法者意識到自己的疏忽和認為在此情況下別無選擇而只能將控制權力交給行政者以期望事情好轉等因素影響,使得在現代行政國中,實際上不可避免地使立法者、法官和公眾將處理這種嚴重危機的最終權力授予給行政部門。24中國向來具有以政府主導經濟社會發展的傳統,行政中心主義的特點更為明顯。事實上很難預見,在擴大證券概念及使用范圍的努力上,相對謙抑的中國司法部門會在具體案件適用中突破現有法律規定而擴張解釋證券的種類。
其次,如果由行政部門主導對證券概念的擴張解釋,則由國務院,或是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抑或是中國證監會負責,也有差異。盡管由最高國家行政機關負責認定證券范圍具有權威性,但該方案可能在靈活性和專業性方面有所欠缺;實際上,國務院在《證券法》修改后也未曾作出過認定。如果采用第二種方案,立法規定由“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認定,一個可能的后果是除中國證監會外還有其他部委也對證券監管有權力,則其是否能夠做出證券種類認定存在疑問。“在國務院系統中有若干個部門對證券活動具有監督管理權力,但并不意味著這些部門對證券市場活動都要承擔責任。例如,財政部、過去的國家計委和國資局、中國人民銀行、國家外匯管理局,甚至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稅務總局、環保局等。它們對證券監管有部分權力,但并不承擔直接的責任”。25這種職責、權力與責任不匹配的情況,必然會發生激勵機制錯位的問題。因此,筆者認為最為妥當的辦法是通過立法直接將證券認定的權力賦予中國證監會,由證監會對納入證券范圍的資本運作活動行使監管權。同時,證監會也應該承擔與其權力相適應的職責與責任,因疏忽、懈怠而疏于定界、解釋資本運作活動是否為發行證券并為監管的情況,也需要運用科學的問責機制來確定監管機構、領導及具體工作人員的責任。26也唯有此,才最有希望在實踐層面拓展中國證券法中的證券概念。
注:
1參見姚海放:《經濟法主體理論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209頁。類似的觀點也可參見陳斌彬:《危機后美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述評——多邊監管抑或統一監管》,《法商研究》2010年第3期。
2、3參見李飛:《關于如何確定證券法的調整范圍問題》,《中國法學》1999年第2期。
4參見吳志攀:《〈證券法〉適用范圍的反思與展望》,《法商研究》2003年第6期。
5葉林:《證券法》(第三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頁。
6李曉波:《論我國〈證券法〉上“證券”概念的擴大》,《中國商界》2009年第8期。
7、8參見朱羿錕:《商法學——原理·圖解·實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18-419頁,第415頁。
9328 U.S.293,66 S.Ct.1100,90 L.Ed.1244(1946).
10494 U.S.56,110 S.Ct.945(1990).
11朱錦清:《這些果園是證券——兼評〈經濟日報〉“莊園主”一文》,《法學家》2000年第2期。
12以下內容參見郭靂:《美國證券私募發行法律問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9頁。
13參見葉林:《證券法》(第三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3頁;廖大穎:《開發新金融產品與修正證券交易法》,載廖大穎:《證券市場與股份制度論》,臺北元照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59-160頁。
14參見[日]河本一郎、大武泰南:《證券交易法概論》(第四版),侯水平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7頁。15參見楊東:《論金融法制的橫向規制趨勢》,《法學家》2009年第2期。
16328 U.S.293,66 S.Ct.1100,90 L.Ed.1244(1946).
17于瑩、潘林:《概念抑或類型——雷維斯案界分本票與證券的啟示》,《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
18See Steinberg, Notes as Securities:Reves and Its Impl ication,51 Ohio State L.J.675 (1990).轉引自郭靂:《美國證券私募發行法律問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頁。
19SECv.GlennW.Turner Enters.,Inc.,474 F.2d,482;SECv.Koscot Interplanetary,Inc.,497 F 2d,483.轉引自[美]萊瑞·D·索德奎斯特:《美國證券法解讀》,胡軒之、張云輝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頁。
20參見彭冰:《非法集資行為的界定》,《法學家》2011年第6期。
21劉哲昕、劉偉:《金融衍生工具的法律解釋》,《法學》2006年第3期。
22參見熊玉蓮:《金融衍生工具的法律風險及其監管的國際比較》,《政治與法律》2006年第3期。
23郭鋒:《新自由主義、金融危機與監管改革》,載郭鋒主編:《金融服務法評論》(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24Eric A.Posner&Adrian Vermeule,“Crisis Governance 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9/11 and the Financial Meltdown of 2008”,Vol.76,No.4,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Review,2009,pp.1613-1682.
25吳志攀:《〈證券法〉適用范圍的反思與展望》,《法商研究》2003年第6期。
26參見史際春、馮輝:《“問責制”研究——兼論問責制在中國經濟法中的地位》,《政治與法律》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