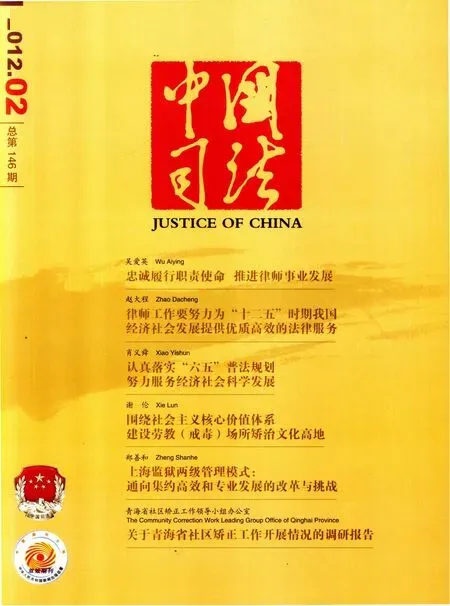法律監(jiān)督立法與司法學(xué)研討會綜述
劉家楠 (中國政法大學(xué)研究生院博士生 北京 100088)
張文靜 (本刊記者 北京 100020) ■文
法律監(jiān)督立法與司法學(xué)研討會綜述
Summary of the Seminar on Law Supervising Legislation and Justice
劉家楠 (中國政法大學(xué)研究生院博士生 北京 100088)
張文靜 (本刊記者 北京 100020) ■文
2011年12月30日下午由中國政法大學(xué)司法理念與司法制度研究中心主辦的“法律監(jiān)督立法與司法學(xué)研討會”在北京召開。來自最高人民檢察院、民盟中央、最高人民法院、中華全國律協(xié)、中國人民大學(xué)、中國政法大學(xué)及部分媒體的二十多位專家學(xué)者出席了本次會議,共同研討法律監(jiān)督立法的理論架構(gòu)與現(xiàn)實運作及司法學(xué)的學(xué)科體系,司法學(xué)學(xué)科中的中國傳統(tǒng)法律文化資源,以及司法學(xué)對時下中國社會司法現(xiàn)狀的積極影響。本次會議由中國政法大學(xué)司法理念與司法制度研究中心主任崔永東教授和馮永華研究員主持。中國政法大學(xué)前校長、終身教授、我國著名刑事訴訟法學(xué)家陳光中先生出席本次研討會并作主題發(fā)言。
一、主題發(fā)言
中國政法大學(xué)終身教授陳光中在主題發(fā)言中指出,本次會議的兩個主題“法律監(jiān)督立法”與“司法學(xué)”均屬較為復(fù)雜的問題,二者結(jié)合使得研究難度加大。陳光中教授由司法學(xué)的語義切入,司法學(xué)顧名思義是以司法作為研究對象,究其實質(zhì)學(xué)界對此的認(rèn)知存在較大分歧,定義的明晰不僅是理論上的問題,同時亦困擾實踐。他隨后談到本次刑事訴訟法修改的問題,表明并不贊同刑訴法修改中的某些提法,例如凡是參加司法活動的主體、刑事訴訟法的主體都是司法機關(guān)。他認(rèn)為,司法的狹義定義是審判,美國憲法規(guī)定司法權(quán)歸屬各級法院,此為一種定義,這種定義有其好處,憲法的規(guī)定排除了爭議,司法即是審判,但這是一種最為狹義的定義。此種狹義的提法于中國并非十分契合,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報告均提及的建設(shè)公正、高效、權(quán)威的司法制度,原屬法院提出,現(xiàn)在由黨的官方文件提出,不再僅指法院,顯然要擴大一些,司法制度不完全就是審判制度。
陳光中教授認(rèn)為司法就是訴訟制度,解決矛盾糾紛,但必須具有訴訟性質(zhì)才可以稱為司法。我國有三大訴訟——刑事、民事、行政訴訟,訴訟的特點必然要求審判,刑事訴訟、民事訴訟就是審判制度,是一致的。刑事訴訟以刑事審判為中心,其序列中的偵查、起訴亦屬于訴訟,也具有司法性質(zhì),偵查起訴是為后續(xù)審判制度作準(zhǔn)備。以刑事訴訟來說,司法就是審判,又顯狹隘,但如果說訴訟包括偵查制度等都是司法制度就較為切合實際。司法鑒定就是在訴訟中由專家對某方面的問題進(jìn)行鑒定的活動。將司法鑒定限定在訴訟中,訴訟外需要的鑒定不再稱為司法鑒定,因為民間也可以組織鑒定。部分學(xué)者持廣義解釋的觀點,認(rèn)為凡是解決糾紛的活動都是司法活動。陳光中教授不贊同泛化的解釋,認(rèn)為應(yīng)界定司法為一種國家活動,是國家機關(guān)的活動,是國家的職能,而不是一般的社會活動。我國的司法活動是國家活動中的一種,但是純粹的解決糾紛并不是司法活動。
陳光中教授特別強調(diào),除司法活動本身以外還有配套活動,配套活動要與本身進(jìn)行區(qū)別,配套乃是為了訴訟的需要。例如監(jiān)獄,監(jiān)獄是訴訟結(jié)束后,將被判刑人員送往服刑之場所。監(jiān)獄法是行政法,從性質(zhì)上來說不屬于訴訟法范疇,廣義上可以把監(jiān)獄法變成司法中的一個范疇,但陳光中教授認(rèn)為不納入為好。進(jìn)行一定司法活動的機關(guān)并不等于就是司法機關(guān)。以偵查為例,除檢察院外,公安機關(guān)行使大部分的偵查權(quán),國家安全機關(guān)對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進(jìn)行偵查,此外還有海關(guān)對案件的偵查,部隊保衛(wèi)部門的偵查,監(jiān)獄中犯罪的偵查,上述均為偵查活動。偵查活動在某種意義上是為最后的審判活動服務(wù),具有司法性質(zhì)。如果將行使一定偵查權(quán)的機關(guān)都視為司法機關(guān)是不適當(dāng)?shù)摹KJ(rèn)為在中國,司法機關(guān)只是檢察院與法院,其他行使一定司法權(quán)、偵查權(quán)的都不是司法機關(guān)。
在對司法問題進(jìn)行一定的厘清后,陳光中教授認(rèn)為法律監(jiān)督立法問題更為復(fù)雜。人大監(jiān)督政府,監(jiān)督各方面的立法。法律監(jiān)督是監(jiān)督法律的實施,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法律必須付諸實施,故而提倡“有法必依,執(zhí)法必嚴(yán)”,要嚴(yán)格依法,才能使法律真正充滿生命力。尊重憲法法律至上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監(jiān)督,法律監(jiān)督就是監(jiān)督法律是否得到執(zhí)行(真正、嚴(yán)格的執(zhí)行)。監(jiān)督法律實施的渠道、方法、途徑和機關(guān)是多方面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監(jiān)督法律實施的最權(quán)威的機構(gòu),法律由其制定,同時是否實施得當(dāng)也由其監(jiān)督。而社會監(jiān)督則為媒體監(jiān)督、群眾監(jiān)督、網(wǎng)絡(luò)監(jiān)督,對于網(wǎng)絡(luò)監(jiān)督要揚長避短。
中國的檢察機關(guān)是專門的法律監(jiān)督機關(guān),監(jiān)督法院審判,監(jiān)督檢察院自身,監(jiān)督公安機關(guān)。檢察院作為國家監(jiān)督機關(guān)并非監(jiān)督一切,現(xiàn)階段檢察院的監(jiān)督基本是訴訟監(jiān)督,涉及對行政違法的監(jiān)督并不多。陳光中教授指出,檢察機關(guān)的監(jiān)督要擁有較好的效果,要明確把握兩個要點:第一,自偵案件要減少,自偵案件增多后會導(dǎo)致自我監(jiān)督的局限性;第二,對偵查的監(jiān)督,尤其是對公安機關(guān)的監(jiān)督,檢察院要明確區(qū)分監(jiān)督與參與,反對聯(lián)合辦案、職能不分等非法治化狀況的出現(xiàn),聯(lián)合辦案與職能不分于程序正義而言也是極不適當(dāng)?shù)摹姆ɡ斫嵌榷裕O(jiān)督者與被監(jiān)督者之間必須保持距離,監(jiān)督者與被監(jiān)督者不能合二為一,否則任何形式的監(jiān)督都會空疏泛化,很難形成高效合理的監(jiān)督。在主題發(fā)言的最后,陳光中教授明確表示,法律監(jiān)督實際上是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專門監(jiān)督機關(guān)——檢察院以及各種社會上的力量,綜合形成的法律監(jiān)督網(wǎng),只有形成綜合性的法律監(jiān)督網(wǎng)才能保障監(jiān)督的有益、有效運行,并認(rèn)為法律監(jiān)督立法的復(fù)雜性決定了無論是法律監(jiān)督立法的理論探討還是法律實踐都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進(jìn)行認(rèn)真的理論考量與實踐經(jīng)驗總結(jié)。
二、法律監(jiān)督立法專題研討
中國政法大學(xué)刑事司法學(xué)院王平教授指出,我國的政治體制是人民代表大會下的一府兩院制,不同于西方國家的三權(quán)分立。在我國人大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權(quán)力,人大制定的法律與所作出的決定一府兩院必須執(zhí)行。在一府兩院層面,其中國務(wù)院是行政機關(guān),行使國家行政權(quán),法院是審判機關(guān),行使國家審判權(quán),上述兩點在理論和實踐中均未產(chǎn)生疑義。王平教授將檢察機關(guān)定位為法律監(jiān)督機關(guān),不理解為司法機關(guān)。他認(rèn)為如果將法院與檢察院均界定為司法機關(guān),一府兩院模式就成為一個行政機關(guān)與兩個司法機關(guān),此種模式下檢察院獨立的監(jiān)督權(quán)有被淡化的風(fēng)險。而且目前檢察院的法律監(jiān)督權(quán)存在界限不清的問題,監(jiān)督主要是監(jiān)督審判機關(guān)和行政機關(guān),監(jiān)督機關(guān)及其官員,不針對民眾,非訴訟監(jiān)督比較弱,除公安機關(guān)外,對其他行政機關(guān)不易監(jiān)督。王平教授認(rèn)為,現(xiàn)有的檢察機關(guān)的權(quán)力都是合理的,檢察機關(guān)法律監(jiān)督的統(tǒng)一立法值得考量,需要對目前分散的立法進(jìn)行整理,使檢察院的法律監(jiān)督權(quán)更加清晰、有用。
中國政法大學(xué)民商法學(xué)院宋朝武教授在發(fā)言中首先對法律監(jiān)督的概念進(jìn)行了法理學(xué)的梳理,即法律監(jiān)督的概念問題從法理學(xué)的角度看,包含兩方面即國家監(jiān)督和社會監(jiān)督,社會監(jiān)督包含媒體、群眾、社團、黨派的監(jiān)督;國家監(jiān)督是由憲法或法律授權(quán)的有法律監(jiān)督權(quán)的機關(guān)對法律進(jìn)行監(jiān)督,包括全國人大,各行政機關(guān),如審計署、監(jiān)察局、財政局等,還有一重要機關(guān)就是檢察院。檢察院的監(jiān)督權(quán)由憲法明確規(guī)定。目前在民事訴訟的審判與執(zhí)行中存在諸多問題,存在未依照法律規(guī)定審理案件的情形,并導(dǎo)致群眾的不滿,造成社會不公,影響了司法的公正和權(quán)威,因而在民事訴訟中加強檢察院監(jiān)督迫在眉睫。民訴法中人民檢察院有權(quán)以檢察建議和抗訴的方式對民事訴訟進(jìn)行監(jiān)督,其涵義有二,不限于審判活動,包括整個民事訴訟過程——全面監(jiān)督,增加了監(jiān)督方式——檢察建議。宋朝武教授最后指出,執(zhí)行問題是當(dāng)下民事訴訟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執(zhí)行監(jiān)督同樣是檢察院的一個重要職責(zé)。
最高人民檢察院理論檢察研究所陳文興研究員在發(fā)言中強調(diào),研究法律監(jiān)督立法要明確兩個問題,即明確法律監(jiān)督的必要性與法律監(jiān)督的目的。他指出,沒有監(jiān)督,人性的弱點就易顯現(xiàn)。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除抗訴職能外,法律監(jiān)督問題沒有配套程序,在抗訴、二審、再審程序中檢察機關(guān)的地位略顯模糊,監(jiān)督范圍不明確,程序不健全,制度不完善,許多現(xiàn)行規(guī)定缺乏操作性,不能適應(yīng)法律監(jiān)督的需要,因此法律監(jiān)督立法的必要性得以突顯。關(guān)于法律監(jiān)督的目的,首先,應(yīng)界定法律監(jiān)督的概念和范圍,現(xiàn)行法律界定不清,理論界與實務(wù)界爭議頗大,法律監(jiān)督的第一步也即概念問題需要進(jìn)行理論上的省思與界定;其次,規(guī)范監(jiān)督方式,完善監(jiān)督程序及監(jiān)督保障措施,切實提高法律監(jiān)督實效;再次,法律監(jiān)督中法律后果的規(guī)定缺失,條文約束力弱;第四,要對監(jiān)督者適用監(jiān)督機制,促進(jìn)檢察機關(guān)自身建設(shè),防止檢察職能濫用,對審判獨立造成不當(dāng)干涉。
中國人民大學(xué)李奮飛副教授認(rèn)為,在法律體系已經(jīng)建成的大背景下,關(guān)注法律的實施是有意義的,而法律實施的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監(jiān)督,法律監(jiān)督涉及三大訴訟,法律監(jiān)督理應(yīng)成為未來的研究重點。刑訴法雖然賦予檢察機關(guān)一定的監(jiān)督權(quán)力,但不充分,對檢察機關(guān)的監(jiān)督性質(zhì)、監(jiān)督的未來走向存有爭議。他認(rèn)為未來的檢察院監(jiān)督職能應(yīng)當(dāng)強化,強化檢察院的監(jiān)督有利于應(yīng)對司法腐敗問題,并進(jìn)一步認(rèn)為,就刑事訴訟而言以下方面需要在手段上、在領(lǐng)域上有所拓展,在效果上應(yīng)當(dāng)強化。以立案監(jiān)督為例,立案監(jiān)督局限于對不立案活動的監(jiān)督,監(jiān)督后果并不明確;偵查問題更需要強化,冤假錯案的產(chǎn)生是在偵查的方式與謀略上存有問題,有刑訊逼供行為,檢察院在監(jiān)督此方面的事項上大有可為;檢察機關(guān)不適用非法證據(jù)排除,即便是法院排除非法證據(jù)的情況也較為罕見,現(xiàn)在雖賦予檢察機關(guān)一定的權(quán)限,但相應(yīng)的程序和手段均屬粗線條;監(jiān)所監(jiān)督,多為事后監(jiān)督,受行政執(zhí)法中重大事故的啟發(fā),對于重大刑事案件,檢察機關(guān)可提前介入,即看守所階段。另外對偵查訊問進(jìn)行監(jiān)督十分困難,雖然理論界提出很多舉措,但都較為有限,檢察監(jiān)督對此應(yīng)當(dāng)體現(xiàn)一定的功能,這方面的立法還有待研究。
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改革辦公室王洪祥主任在發(fā)言中認(rèn)為,法律監(jiān)督立法要注重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法律監(jiān)督立法中的法律監(jiān)督主要指檢察機關(guān)的法律監(jiān)督,對于檢察機關(guān)的法律監(jiān)督應(yīng)當(dāng)從憲政學(xué)、憲法學(xué)及政治制度層面來解讀,否則容易得出錯誤認(rèn)知。第二,法律監(jiān)督的立法應(yīng)當(dāng)與時俱進(jìn),逐步完善。目前全國三十一個省市自治區(qū),地方人大都出臺了關(guān)于加強檢察機關(guān)訴訟監(jiān)督的決定或決議,應(yīng)當(dāng)說隨著法治的發(fā)展,時代的進(jìn)步,文明的演進(jìn),加強對公權(quán)力的監(jiān)督、保證社會的公平正義,是社會各界一致的呼聲。在這樣的背景下,完善檢察機關(guān)的監(jiān)督,特別是檢察機關(guān)的訴訟監(jiān)督已經(jīng)形成社會共識。但在地方立法基礎(chǔ)之上形成統(tǒng)一的全國的適時的檢察機關(guān)法律監(jiān)督立法需假以時日。第三,完善法律監(jiān)督立法就要有針對性地反映實踐當(dāng)中民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一是要明確法律監(jiān)督的范圍,特別是訴訟監(jiān)督的范圍,對民事訴訟,對于調(diào)解,對于死刑,不應(yīng)當(dāng)立案而立案的監(jiān)督 (涉及公權(quán)力對個人私權(quán)利的侵犯);二是檢察機關(guān)對行政執(zhí)法機關(guān)的監(jiān)督,要有暢通的監(jiān)督渠道,信息的共享平臺;三是檢察機關(guān)要有調(diào)查核實權(quán),必要時的閱卷權(quán);四是要有相應(yīng)的監(jiān)督手段。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辦公室范明志處長在發(fā)言中認(rèn)為,檢察監(jiān)督是非常復(fù)雜的課題,是帶有中國特色的課題,是憲政的課題而不僅僅是訴訟的課題。隨著我國社會形勢和司法形勢的發(fā)展,檢察監(jiān)督需要與時俱進(jìn)。而檢察監(jiān)督的有限性及越位問題,是值得我們認(rèn)真對待的。明確監(jiān)督的范圍,如果界定為在訴訟體系下來探討該問題,檢察監(jiān)督不僅僅是糾正法院違法的問題,也是影響當(dāng)事人利益的一個問題。如果把檢察監(jiān)督作為訴訟制度進(jìn)行改造和完善,必須考慮到對當(dāng)事人的影響。對于監(jiān)督的范圍,應(yīng)當(dāng)增加一項,即法院是否依法獨立行使審判職權(quán)。賦予檢察院一定的手段來了解被監(jiān)督對象的情況不僅是檢察院的權(quán)力也是檢察院的義務(wù)。一是要賦予檢察院一定的知情權(quán),二是應(yīng)當(dāng)賦予檢察院一定的聽證的權(quán)力,尤其是針對民事案件,兼聽雙方當(dāng)事人的觀點后決定是否抗訴,而不是僅依據(jù)一方當(dāng)事人的觀點作出結(jié)論。現(xiàn)在研究檢察監(jiān)督必須研究設(shè)計一種適合中國國情,適合中國政治體制、司法體制的行之有效的監(jiān)督辦法。
中華全國律師協(xié)會民委會賀寶建副主任針對本次研討會的課題從法律實務(wù)角度談及兩點看法:第一,法律監(jiān)督立法十分必要,目前缺乏專門的法律監(jiān)督立法。(1)公訴權(quán)與偵查權(quán)非司法權(quán),不屬于監(jiān)督范圍。在實踐中,法院開庭,檢察院是公訴人,代表國家行使檢察權(quán),公訴方最好與監(jiān)督身份分離,控辯應(yīng)當(dāng)是平衡的,審判是中立的,而現(xiàn)在的控方又帶有監(jiān)督色彩,上述內(nèi)容在監(jiān)督立法中應(yīng)當(dāng)予以明確,監(jiān)督立法實際上是實踐操作的法律;(2)關(guān)于檢察院對民事案件的抗訴問題。應(yīng)當(dāng)在法律監(jiān)督立法中授予檢察院權(quán)力,使得法院審判不受非法干涉,保證獨立審判。第二,在法律監(jiān)督立法中,也要規(guī)定對行政執(zhí)法相應(yīng)的監(jiān)督。現(xiàn)在檢察院對行政行為進(jìn)行監(jiān)督的空間比較小,通過行政訴訟的方式來解決行政機關(guān)的違法問題有著成本較高的缺陷,依靠立法規(guī)定檢察院可以在政府實施行政行為時實施一些監(jiān)督,是十分緊要的。對于政府采購的監(jiān)督,由政府監(jiān)察部門進(jìn)行監(jiān)督,但政府監(jiān)察部門仍屬于政府機關(guān),這種內(nèi)部監(jiān)督并未達(dá)到法律監(jiān)督的層面,因而在法律監(jiān)督立法中應(yīng)當(dāng)加入對行政機關(guān)的法律監(jiān)督。
三、司法學(xué)與司法傳統(tǒng)專題研討及總結(jié)發(fā)言
中國人民大學(xué)法學(xué)院趙曉耕教授認(rèn)為上一單元討論的主題與明清以來的中央司法情況有高度的類同性,根據(jù)當(dāng)下法律文本的表達(dá),檢察機關(guān)又稱為法律監(jiān)督機關(guān),檢察院的法律監(jiān)督主要執(zhí)行的是訴訟監(jiān)督,并不承擔(dān)一般的監(jiān)察職責(zé)。清代案件的受理主要為刑部,類同今天的法院,而皇帝是“最高法院”,中央刑部一般不干預(yù)地方督府案件,刑部的職責(zé)受到高度規(guī)范,外在的限制力量是大理寺,類同今天的檢察院,大理寺并不承擔(dān)一般監(jiān)督職能,在帝制之下一般監(jiān)督職能由都察院享有。在談及糾紛解決問題時趙曉耕教授認(rèn)為,訴訟一般是糾紛的解決,監(jiān)獄是最終的解決,刑事案件的最終解決恰是要通過監(jiān)獄,沒有監(jiān)獄這一環(huán)節(jié)不能說刑事案件已經(jīng)解決,古代的制度對我們今天面臨的有些棘手的問題提供了參酌,傳統(tǒng)監(jiān)獄中有官方的積極監(jiān)督——錄囚制度,我們今天的制度設(shè)計卻是被動的制度。正是因為繼受了西方的部門法,并在該話語下進(jìn)行種種區(qū)分,才使得監(jiān)督的內(nèi)涵、外延如此混淆,甚或無所適從。從近代歷史變革的角度和經(jīng)驗來看,這是一個我們不斷面對的問題。今天面對的諸多話題應(yīng)該去回溯近代的歷史,不能斷然說會對今日有多少助益,但至少會有許多警示。趙曉耕教授在發(fā)言中特別強調(diào)今日回溯歷史最大的價值就在于歷史的經(jīng)驗。
中國政法大學(xué)法律史學(xué)研究院副院長林乾教授認(rèn)為,本土法律資源,特別是傳統(tǒng)法律資源需要認(rèn)真的清理與客觀的對待,有很多值得借鑒的內(nèi)容尚待發(fā)掘。此處特別要強調(diào)三法司,自隋唐后三法司一直穩(wěn)定存在,明代廢除丞相以后,皇帝成為絕對的權(quán)威,三法司均對皇帝負(fù)責(zé),刑部主審判,大理寺復(fù)核,都察院監(jiān)督。都察院的監(jiān)督是全程監(jiān)督,擁有法律豁免權(quán),可以風(fēng)聞言事。在康乾盛世時,法律規(guī)定兩議制度,即大理寺或都察院不同意刑部的判決,另擬意見由皇帝裁決,但隨即爭權(quán)問題出現(xiàn),皇帝一直在平衡權(quán)力與權(quán)限之爭,為此乾隆規(guī)定,兩議可在,但是不能由一部門對另一部門持完全不同的意見,可以由都察院或大理寺的工作人員提出異議,而不宜以都察院或大理寺兩衙門來對抗刑部,結(jié)果出現(xiàn)“鴉雀無聲”的局面。上述實例意在表明中國古代,在清代康乾盛世這段時間三法司確實起到了互相監(jiān)督的效果。林乾教授接著談到作為清代司法制度之一的秋審制度,秋審結(jié)果分為四類,一實,事實確鑿,法律適用得當(dāng),進(jìn)入秋決;二緩;三矜、疑,法律層面可以處決,情理上看有矜免的可能,皇帝并不勾決,兩或三次后入流刑;四存留養(yǎng)親,清代的存留養(yǎng)親是定制,是儒家法文化的優(yōu)點。林乾教授認(rèn)為傳統(tǒng)司法制度與理念有很多今天可以借鑒的地方,并呼吁學(xué)者對此投入更多的精力進(jìn)行深入的探討與研究。
《法學(xué)雜志》苗延波副主編強調(diào)中國古代的司法制度與法律文化十分契合當(dāng)時的歷史背景,并維系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說明該司法制度有可行性和存在的必然性。我們在建國后學(xué)習(xí)蘇聯(lián),后轉(zhuǎn)向?qū)W習(xí)西方,對傳統(tǒng)形成了一定的割裂,直至當(dāng)下。在中國特色的憲政體制下進(jìn)行司法研究與改革,應(yīng)當(dāng)突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地位,主張大司法的概念。
中國政法大學(xué)法學(xué)院姜曉敏副教授在發(fā)言中同樣強調(diào)研究當(dāng)下問題,不應(yīng)當(dāng)忘記歷史,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理應(yīng)成為現(xiàn)實司法實踐的優(yōu)秀理論源頭。并且法律史與部門法需要進(jìn)行溝通,對于促進(jìn)研究乃是十分必要的。
《法制文萃報》編輯部呂錚主任指出檢察院對于行政機關(guān)的監(jiān)督應(yīng)當(dāng)由被動介入轉(zhuǎn)為主動介入,對政府違法行為進(jìn)行糾正應(yīng)當(dāng)是未來法律監(jiān)督立法的重要研究內(nèi)容,并且司法學(xué)應(yīng)當(dāng)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崔永東教授認(rèn)為中國傳統(tǒng)法律文化并非沉重的包袱而是資源,不是一潭死水而是源頭活水。世界上任何民族都尊重自己的傳統(tǒng),過去我們對于傳統(tǒng)的認(rèn)知有些妄自菲薄,而今天對司法學(xué)學(xué)科的構(gòu)建應(yīng)當(dāng)注意利用傳統(tǒng)的資源,如仁道傳統(tǒng)、中道傳統(tǒng)。仁道代表了人類的普世價值,是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能夠認(rèn)同的,儒家的仁道就是仁愛之道,對他人的關(guān)愛,對他人生命價值的尊重,此種傳統(tǒng)擁有永恒的價值,如錄囚制度、直訴制度、會審制度、大赦制度、死刑奏報制度、死刑監(jiān)侯制度 (今日的死緩制度)、春秋決獄、秋冬行刑和存留養(yǎng)親,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了儒家的仁道精神,于今日亦有可以借鑒的地方。多數(shù)朝代進(jìn)行大赦,大赦的結(jié)果之一就是大大降低了死刑的適用率,實際上也就是在一定時間段、一定范圍內(nèi)廢止了死刑。中道就是中庸之道,追求適中、均衡,反對極端的思想和方法論。作為一種方法論,在司法領(lǐng)域中一方面表現(xiàn)為司法公正,另一方面又表現(xiàn)為司法平衡。司法平衡有兩層含義,一層含義是利益的平衡,另一層含義是情理與法律之間的平衡。對待司法傳統(tǒng)我們應(yīng)當(dāng)認(rèn)真地加以清理與總結(jié),優(yōu)秀的資源應(yīng)當(dāng)借鑒并發(fā)揚光大。
在總結(jié)發(fā)言中崔永東教授就司法學(xué)的學(xué)科體系、理論基礎(chǔ)、現(xiàn)實意義等層面進(jìn)行了概括與解析。他認(rèn)為,司法學(xué)是一門研究司法理念、司法制度和司法實踐的學(xué)問,也是一門研究司法傳統(tǒng)與司法現(xiàn)實的學(xué)問。應(yīng)當(dāng)從廣義上來把握司法學(xué),一切與化解糾紛有關(guān)的制度、措施和觀念均可成為司法學(xué)研究的對象。從學(xué)科體系來看,司法學(xué)應(yīng)當(dāng)有一系列子學(xué)科,司法哲學(xué)、司法史學(xué)、司法證據(jù)學(xué)、司法倫理學(xué)、司法行政學(xué)、司法社會學(xué)、司法行為學(xué)以及比較司法學(xué)等等,另外亦應(yīng)當(dāng)包括刑事政策學(xué)、法律監(jiān)督學(xué)。法律監(jiān)督自身可以獨立成學(xué),為司法學(xué)下的子學(xué)科。訴訟法學(xué)也應(yīng)當(dāng)是司法學(xué)下的子學(xué)科,司法學(xué)是法學(xué)的二級學(xué)科,包含上述子學(xué)科。立法學(xué)與立法權(quán)對應(yīng),行政學(xué)與行政權(quán)對應(yīng),那么與司法權(quán)相對應(yīng)的學(xué)問應(yīng)當(dāng)是司法學(xué),但是現(xiàn)在司法學(xué)缺位。司法學(xué)學(xué)科的建立有重大的現(xiàn)實意義和理論意義,有利于法學(xué)學(xué)科的完善,有利于司法權(quán)配置和運行的科學(xué)化,有利于司法制度和司法體制的完善化,有利于司法文明和法治文明的進(jìn)步。
(責(zé)任編輯 張文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