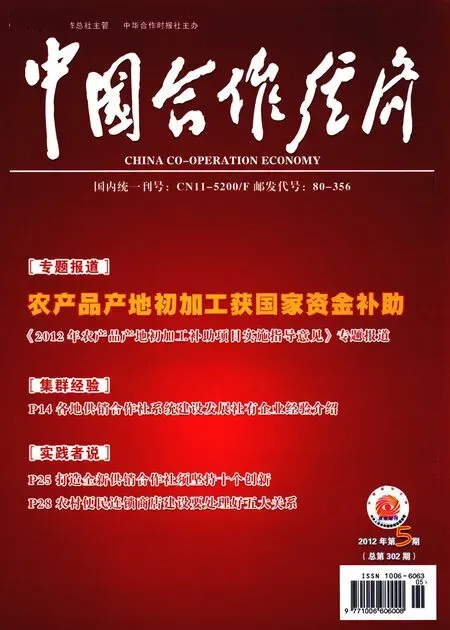農民的自我終結——評《農民的終結》
文/蘇 琦
“這本書是一個文明的死亡證明書。”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孟德拉斯如此評價自己的著作 《農民的終結》:在一代人的時間里,法國目睹了一個千年文明的消失,這文明是它自身的組成部分。
這里的文明指的是由千千萬萬戶小農組成的傳統農業文明,在大規模工商業文明出現以前,它在數千年的時間里曾是人類文明的主要形態,而且迄今仍在那些后發國家里頑強地存在著。作者在闡述寫作本書的目的時指出,20億農民站在工業文明的入口處,這就是在20世紀下半葉當今世界向社會科學提出的主要問題。對于這一問題,社會科學能夠給予什么樣的回答呢? “要想知道怎樣使全世界的農民進入工業文明,以便使他們能夠自己解決吃飯問題和走向繁榮,難道思索的最好例子不是西方國家已經完成飛躍的農民嗎?”孟德拉斯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作為反傳統的 “田野教學派”的一員,孟德拉斯強調研究必須建立在經驗調查的基礎上。為此,他和他的團隊花了12年時間 “上山下鄉”進行這項調查。孟德拉斯認為法國的農村給社會學家 “提供了一種實驗室,那里收集了很多可供進行各種分析的 ‘自發性試驗’”,因此雖然所論述的僅僅是法國,但讀者可以 “自由地探索可能的推論和借鑒”。
對于正在經歷快速的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中國來說,這樣的命題顯然具有濃厚的現實意義,那些先行者的進退得失足以為中國這樣的后來者所借鑒。
在本書寫就的1967年的法國,以小農戶為代表的農業文明的消亡進入尾聲。從1946年到1965年,法國的拖拉機停車場從2萬處左右發展到100多萬處,新技術直接來自實驗室的研究,而不是來自進步農業勞動者的摸索。
沖擊不僅僅來自技術層面。那些沉迷于 “個人主義”和 “土地戀”的法國農民一度懷有這樣的夢想:在吸收了一些新技術和接受了一些經濟制約之后,也即適應期的危機過去之后,他們可以重新創立一種能夠和以前一樣持久的耕作與經營體制,進而重新找到類似他們父輩熟悉的那種平衡。
然而技術文明有著自己的節拍。像其他生產領域一樣,農業也必須服從工業社會中技術和工業變化的節奏。一切農業生產都受消費者的欲望和市場的變化所支配。農民不僅遠未重新找到傳統的穩定,而且將經受技術革新和經濟趨勢帶來的長期變動。開弓沒有回頭箭,為了應對這一長期變動,法國農民或主動或被動走上了農業現代化和經營集中化的道路,從而 “被卷入了”一場從變革 “技術結構”始,至變革 “社會結構”終的歷史性事業。
在孟德拉斯看來,法國農民尤其是青年農民具有驚人的適應性,一旦對經濟的前途和 “鄉村職業的高尚”重新確立信心,他們可以按照工業社會的經濟規則行事,利用鄰居外流的時機擴展自身,并以 “驚人的可靠直覺去創立一些全新的和非常符合現代要求的機構 (農業技術研究中心、農業集體利益協會、家庭鄉村培訓所等等)”。
在這里,不難看出, “鄰居外流”和農民的 “自組織”是“終結”小農戶的兩個關鍵前提,前者是農業現代化的物質基礎,后者是對接技術與市場變化的載體。從這個意義上講,盡快結束對農民工進城的 “欲迎還拒”,盡快放開對農民自我組織的限制,同樣是順遂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不可或缺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