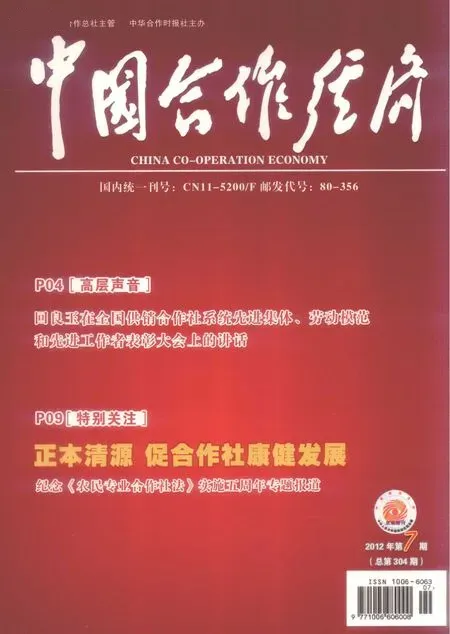中國農業需要可持續發展——對《四千年農夫》的思考
文/石 嫣
1909年,美國的農業經濟學家富蘭克林·H·金來到中國,隨后他又走訪了日本和韓國,他不是因為對中國的好奇而游歷中國,而是為了研究中國農民的實際生活情況。1911年,金的妻子在他過世后完成了他的著作——《四千年的農夫》的出版。
書中序言說:“我們不要想當然地認為我們可以指導全世界的農業,認為我們有巨大的農業財富并大量出口到其他國家。其實,我們也就是剛剛會耕作。農業耕作的最基本條件就是如何保持肥力。這個問題東方人已經遇到并且有他們自己的解決辦法。或許我們不能采取任何特別的方法,但我們卻可以從他們的經驗里多多獲益。我們必須學習他們是如何進行環境資源保護的,這是土地的根本。”
作者產生了疑問:“中國農民數千年來如何成功地保持了土壤的肥力和健康,他們沒有使用大量的外部資源投入,他們幾千年來的耕作都沒有讓土壤的肥力降低太多,同時又養活了這么高密度的人口。為什么美國這樣的國家僅僅耕作幾百年的歷史,就已經面臨著如何保護土壤健康的問題,并面臨著農業如何可持續下去的危機呢?”
當時我看這本書的時候是在美國,讓我讀這本書的那個美國朋友半開玩笑地說:“也許金今天再去中國就會看到中國的農業已經因為跟隨著歐美的腳步變得越來越不可持續了。”為什么我們要向那些土壤只因為幾百年的耕作就已經貧瘠化了的國家學習? “一定是那些來自推銷員腔調的僅憑猜測和推測的大學的研究以及內向的文化壓力讓你們認為那是 ‘現代’,可惜你們卻沒有認識到你們在人類歷史上所立下的功勞有多大,能夠讓你們的土壤這么長久的保持健康。”金寫這本書的目的本來是希望用他的見聞來教育美國人,但現在,距離那時又將近一個世紀的當今,讀來卻對我們有極大的教育意義,也有一定的諷刺性。
這本書讓我們看到只是在100年前,我們的祖先是如何讓日常運轉并不依靠那些現代科技,用行動告訴世人,人類需要做出努力才能保持土壤肥沃和多產,而保存土地這種稀有資源會讓世世代代過一種合理的、舒適的、可持續的生活,并用事實表達了這樣一個世界我們能傳遞給我們的子孫的自信態度。而當時的美國人并不擁有這些,他們擁有的是被現在的我們過多吹噓的所謂“生活質量”。如今,我們正在我們祖先的生產生活方式和國外所謂現代化的生活方式這樣一個十字路口徘徊,我們該怎么辦?我們到底要什么?這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事實上,中國農業的多樣性是有歷史根據的。據考古發掘,中國已經有7000年的蠶桑和6400年的稻作農業史。承載中國農業文明史的傳統家庭經營,是有利于生態環保的有機生產,且具有食品安全、環境維護和社會穩定三大正外部性,與最近40年才被當作發展方向的農業現代化導致大規模推進的化學農業、石油農業相比,后者只不過是中華農業文明史中的短暫一瞬。盡管短暫,
閱讀卻已經讓我國的農業變成了不可持續農業,在農村造成了嚴重的生態和環境災難,在城市造成嚴重的食品不安全。也恰恰由于短暫,我們還有機會恢復我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在農業現代化發展與可持續發展中找到平衡點,目前在農村推進環保和開展農業生態修復顯然是事半功倍的最佳政策選擇。
中國在這種全部耕地只占世界的7%,水土光熱比只占國土面積的9%,而人口數量卻占世界20%的基本國情等硬性條件約束下,越是追求農業作為現代產業的產量和效益的增長,就越會造成不斷追加的化學品的投入,也就越發使得我們的農業不可持續。
然而這種常識是否被社會接受,不會一般化的取決于社會大眾,而主要看各地涉農利益部門的多重博弈。要想將農戶的生產行為轉向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方向上來,必須提供足夠的行為激勵。然而,當化學化種植和規模化養殖成為農業的主流生產方式之后,不可避免的形成涉農利益集團占有收益和轉嫁成本的制度,并對其后的發展和制度變遷形成路徑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