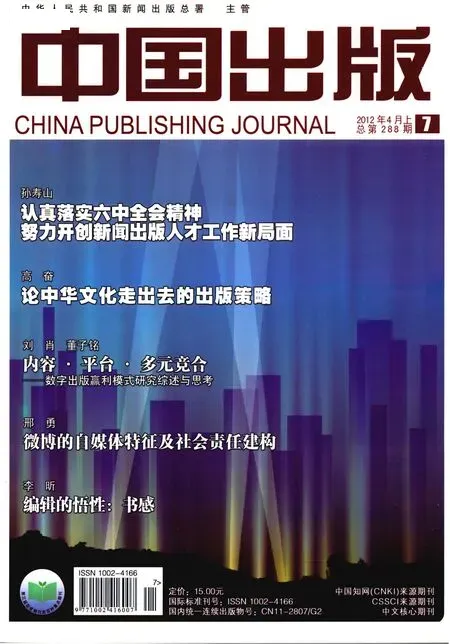論中華文化走出去的出版策略
文/高 奮
在21世紀推動中華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進程中,中國出版業憑借其文化產品的普及力、影響力和深刻度等特性,將在中華文化走出去中擔負重任。書籍流通的廣泛性和普及性可以讓中華文化進入世界各地尋常百姓家,書籍閱讀的耐久力、重復性和便利性有利于中華文化的傳播、記憶、吸收和保存,書籍內涵的博學性、思辨性和感悟性有益于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創新。中國出版業要擔負起向世界推廣中國文化的重任,需要思考下列兩個重要問題:出版業需要讓哪些文化走出去?文化出版走出去的有效途徑是什么?
要回答這兩個問題,我們可以以史為鑒,對中學西漸悠久的出版歷程作出梳理,進行反思,獲得啟示,把握世界對中國文化的內在需求。在此基礎上提出的走出去策略將是有益而可行的。
一、中學西漸中圖書出版的回溯與分析
中華文化走出去的歷史悠久而富有成效,國內學者通常將這一持續而綿延的文化傳播過程稱為中學西漸或東學西漸。幾千年的中華文化傳播主要包括物質產品、科學技術、社會制度和精神文化幾大部分,各個歷史時期的傳播側重和途徑各不相同。
自秦漢至唐宋(前221-13世紀),中國文化主要通過物品商貿與文化交往傳入世界。中國的陶鼎、陶鬲、青銅劍、絲綢、銅鏡、服飾、瓷器、茶葉等物品,鑄鐵技術、農耕技術、音樂、建筑藝術、火藥、指南針、活字印刷等先進科技藝術,以及政治體制、商貿方式、貨幣制度、風俗禮儀、醫學等社會管理和生活方式通過海陸絲綢之路、戰爭、使節往來、和親、旅游等多種途徑,陸續不斷傳入西域與歐洲。當時有書籍記載與中國通商的國家的情況,比如《嶺外代答》、《諸蕃志》等,但幾乎沒有向外介紹中華文化的書籍。中華文化的昌盛、繁榮和發達主要通過廣泛的物品交易和有限的人際交往來折射和傳遞,神秘的中華帝國不僅帶給世界高度的物質文明,也留給世界其他國家無窮的想象。
元代至明代(13-15世紀),除原有的物品貿易和文化交往活動之外,書籍出版開始在中國文化傳播中發揮重要的傳媒作用,中華文化的傳播變得全面、深入、廣泛。隨著海陸交通逐漸便利,元上都開始聚集來自阿拉伯、俄羅斯、英國、法國、德國等世界各地的使節、商人、旅游者、傳教士等,其中有學識的歐洲人撰寫了在華游記,向本國民眾介紹中國文化。這些游記從政治、社會、人文、地理、貿易、宗教、風俗等諸多方面介紹中國文化思想,引發了歐洲對中國的廣泛關注。著名的游記作品包括:馬可·波羅的《馬可·波羅游記》、魯布魯克的《東行記》、鄂多立克的《鄂多立克東游記》、柏朗嘉賓的《蒙古史》等。[1]
明末清初(16-18世紀),大量歐洲耶穌會士往來于中西之間,旨在向中國傳播宗教思想,擴大西方勢力,他們卻同時著迷于中國的哲學、藝術、政治等高度昌盛的精神文化思想,自覺不自覺地擔負起向自己的國家傳播中國文化的職責。當時的傳教士們人數眾多,在華活動時間長;來華之前大都是頗有造詣的學者,擅長用中西文著書立說;來華后遍布京城宮廷和國內重要城市,廣交中國的政界學界人士;可以說他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和理解是比較深入的。[2]他們不僅撰寫大量介紹和研究中國文化的書籍,而且翻譯大量中國重要典籍,全面激發了歐洲的“中國熱”。他們的譯介作品從多個層面影響并促進歐洲近代哲學、政治、文藝思想的形成,這些書籍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對中國文化的全面介紹。比如:利瑪竇的《基督教遠征中國史》,衛匡國的《中國新地圖志》,《中國上古歷史》,柏應理的《中華帝國年表》,門多薩的《大中華帝國史》,達克魯斯的《中國志》,曾德昭的《大中國志》,安文思的《中國新史》,約翰·巴羅的《中國旅行記》,李明的《中國現勢新志》等。
第二類是對中國哲學、語言、園林、建筑、醫學等學科的專題研究著作。比如:柏應理的《中國賢哲孔子》(第一部比較完整地向西方介紹中國傳統文化的書籍),衛匡國的《漢語語法》,曼策爾的《拉漢小辭典》,王志誠的《北京附近的皇室園亭》,威廉·錢伯斯的《論中國人的建筑、家具、服飾、機械和生活用具》、《論東方園林》,路德維希·翁則爾的《中國園林論》,卜彌格的《醫論》(第一部系統地向歐洲介紹中醫的著作)等。
第三類是中國經典著作翻譯。比如:利瑪竇翻譯了《四書》(拉丁文),柏應理《中國賢哲孔子》的第四部分是《大學》、《中庸》、《論語》的拉丁文譯文和注解,馮秉正翻譯了朱熹《通鑒綱目》,韓國英、宋君榮、劉應等翻譯了《四書》、《五經》(法文),錢德明翻譯了《古樂經傳》,赫蒼壁、白晉、宋君榮翻譯了《詩經》,儒蓮翻譯了《趙氏孤兒》、《西廂記》、《白蛇傳》,巴贊翻譯了《琵琶記》、《貨郎擔》、《竇娥冤》,昂特爾科爾翻譯了《今古奇觀》,威爾金森翻譯了《好逑傳》,韓國英翻譯了《醫宗金匱》等。
清朝中后期至今(19-20世紀),隨著西方政治經濟的日益強大和他們對清朝社會中各種弱勢的明察,歐洲的“中國熱”開始消退,但是歐洲各國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和吸收從未中斷。這一時期,除了傳教士繼續譯介和傳播中國文化之外,歐美各國出現了一批學術造詣頗高的漢學家和漢學研究機構,譯介中國文化的書籍大量出版,所涉領域更為寬泛,所作研究更為深入。
最具影響力的傳教士和漢學家當推衛禮賢,他在中國居住20余年,不僅在中國辦醫院、辦學校、建立東方學社,而且翻譯出版了《論語》、《道德經》、《列子》、《莊子》、《孟子》、《易經》、《呂氏春秋》、《禮記》等大量中國典籍,撰寫并出版《老子與道教》、《中國的精神》、《中國文化史》、《東方——中國文化的形成和變遷》、《中國哲學》等多部著作,發表大量關于中國問題的文章,是“中學西漸”進程中的一位功臣。
另一位著名漢學家是翟理斯,在中國居住20余年,致力于傳播中國文學、歷史、藝術、語言、文化習俗等,譯著豐碩,對中國文化的傳播貢獻巨大。他編纂《華英字典》,翻譯《三字經》、《聊齋志異》(選譯本)、《古文選珍》(節譯了老子、莊子、孟子、司馬遷、柳宗元、蘇東坡、梁啟超等89位中國思想家、作家的 186篇文章)、《古今詩選》、《莊子》(內含大量評注)、《中國繪畫史導論》(譯介自遠古至明末多位藝術評論家和畫家的著作和作品)、《中國神話故事》等,撰寫《中國概要》、《歷史上的中國及其概述》(概述中國各朝代、法律、教育、占卜、圍棋、姓氏等)、《中國文學史》、《中國的文明》、《中國古代宗教》、《古今姓氏族譜》、《中國札記》(內容涉及社會問題、文學、醫學、風水等諸多方面)等多部研究著作。
在漢學家和漢學機構的推動下,歐美各國不僅先后掀起老莊熱、易經熱、禪宗熱等,而且不斷推進中學西漸重要議題的研究,以法國研究為例,“中國文化西傳歐洲的過程”、“中國文化對法國重要哲學思想形成的影響”、“法國著名哲學家與中國文化的關系”、“西方哲學中的東方思想”等都是法國當代哲學的重要研究議題。[3]
二、對“中學西漸”出版傳播的反思
在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幾千年歷程中,書籍出版不僅使文化傳播的途徑由有限的、隱性的實物貿易和人際交往轉變為廣泛的、顯性的語言傳播和機構交流,而且將文化傳播的內涵從淺顯易懂的文化習俗層面推進到深入淺出的基本國情、價值觀念等精神思想層面。可以說,在中學西漸過程中,書籍出版在傳播中國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績是顯著的,但是它的局限也是明顯的。
“中學西漸”出版傳播所取得的成績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傳播過程的可行性和持久性、傳播者的主動性和可接受性、傳播效果的高效性和普及性。
傳播過程的可行性和持久性
中學西漸自元朝以后開啟的書籍傳播是以秦漢至唐宋1000多年的物品商貿和文化交往為基礎的,并始終與多渠道多層次的政治、經濟、文化交往并行不悖,這保證了出版傳播的可行性和持久性。換句話說,憑借物品貿易和文化交往活動,世界其他國家早已對中國高度昌盛的文明耳濡目染,神往已久,馬可·波羅等人的游記以及歷代傳教士、漢學家們對中國文化的不間斷的、主動的、廣泛的譯介成果極大地滿足了世界各國對中國文化的渴求,書籍傳播是順應時勢的自然之作,它的可行性與持久性的基礎是世界各國對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的內在需求。
世界對中國文明的內在需求是必然且持久的,因為東西方基本思維模式是互補的。誠如季羨林先生所言,“東方的思維模式是綜合的,它照顧了事物的整體……既見樹木,又見森林……而西方的思維模式則是分析性的……分析到極其細微的程度……只見樹木,不見森林。”[4]因而,當西方人發現他們的理論和思想發生內在困難和矛盾的時候,他們往往會轉向東方思想,特別是中國思想,以獲得超越困境的良方,也就是說,“為了解決現代西方思想內在矛盾的多元性,需要中國文化”。[5]
傳播者的主動性和可接受性
中學西漸自元朝以后的書籍傳播者主體是來華的歐洲旅行家、傳教士和漢學家,他們身為西方人士,在來華之前大都已經是富有學識和影響力的知識人士,他們對中國文化的主動選擇和悉心譯介是以他們的國家和人民對東方文化的興趣和內在需求為標桿的,因而他們的書籍對西方各階層讀者有著自然的感召力、影響力和親和力。再者,他們對中國文化的主動選擇和闡釋是基于西方文化的知識結構和思維模式的,他們多年在華的體驗和閱讀有益于消解兩種文化之間的巨大鴻溝,因而他們的著作十分有利于未曾接觸中國的西方人順利接受并吸收中國文化。
傳播效果的高效性和普及性
不論是來華的旅行者,還是來華的傳教士和漢學家,他們大都是經由宮廷、宗教團體、社會機構的篩選和資助而來到中國的,他們較高的學識和強烈的責任心使命感使他們不僅著述豐碩而且造詣頗高,他們的書籍出版往往獲得國內資助方的大力推薦,書籍的普及力和影響力巨大。同時他們在華期間也獲得中國官方和相關社會機構的重視,為他們提供良好的接觸中國文化的渠道和環境,確保他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有一定的廣度和深度。
出版傳播的局限性主要表現為傳播者的主觀性所帶來的傳播內涵和范圍的有限性。
已有的中學西漸是一種以西方傳播者為主體的傳播模式,其傳播內容、方式、目標均基于西方文化的興趣、知識體系和價值觀之上,不可避免地會對被傳播的中國文化進行想象性誤讀、文化性誤讀乃至政治性誤讀。就像現代主義詩人龐德對李白詩歌的翻譯一樣,其中既有李白詩句的原味,也流露著龐德本人的創作特性和他所根植的英美詩歌的韻味。中學西漸所闡釋的中國文化和所選擇翻譯的中國經典無疑帶著某種西方思維和西方文化的韻味。這雖有利于西方人的接受,卻可能將中國文化停滯于某一層面,局限于某一范圍,既不利于呈現中國文化的整體性,也不利于傳達中國思想原有的高深意蘊和蘊外之境。
三、新時期中華文化走出去的出版策略
在梳理和反思中學西漸的優勢和局限的基礎上,新時期中華文化走出去的出版策略應該具有綜合聯動性、中外合作性和世界性的策略。
首先,可以以中華文字、繪畫、書法、瓷器、武術等傳統大眾文化為傳播媒介,用多渠道多形式多層次的綜合聯動方式,向西方大眾普及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的表意性使各大眾文化類型如繪畫、絲織品、瓷器、書法、音樂、建筑等均能以直觀形式表現諸如“天人合一”等深刻思想內涵,這既是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最根本的不同之處,也是中華文化最具魅力和感召力的地方。許多西方思想家、藝術家正是因為被直觀意象打動而迷戀上了中國文化,比如美國詩人華萊士·斯蒂文斯就是因癡迷中國禪宗畫而開始大量閱讀中國禪宗、哲學和詩歌,喬伊斯《尤利西斯》的部分章節充分借鑒了中國傳統文字印刷不著標點垂直而行的特點。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易于感知的中國大眾文化是讓世界了解中國的良好起點,而我們要做的則是推出以圖片為主體的系列大眾文化出版物。我們既可以依托海外孔子學院和海外中國文化中心加以傳播,也可以讓它們伴隨各類文藝交流活動或海外機構走向觀眾,還可以與國外重要出版社聯合出版,充分依靠這些出版社對本國讀者的興趣和口味的了解和他們對讀者的親和力和影響力。
其次,以中華典籍為核心傳播載體,增強并提升西方世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推進中外文明對話。
無論是西方傳教士還是海外漢學家,他們傳播中華文化的核心始終是中華典籍。中華典籍是中華文明的瑰寶,是中華思想根本之所在,也是西方最渴望從中國文化中汲取的思想,是滿足西方內在需求最重要的部分。比如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海德格爾等諸多西方思想家在形成自己的理論之前均以各種方式閱讀過中國典籍。先前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雖然盡一己之力翻譯了部分中國典籍,但是大多數經典依然等待翻譯。
中國典籍正是中華文化提升自己在世界上地位的核心利器,也是開展并推進中外文明對話的重要基礎,而我們要做的則是系統翻譯最重要的文化經典。為了避免翻譯過于中國化或過于西方化,最佳的選擇依然是與國外出版社合作出版,翻譯者若能由中西學者合作組成,那是最佳選擇。
再次,建立國學與海外漢學之間的對話平臺,推進中華傳統文化的現代闡釋的世界化。
就如中國的國學研究一直向前推進一樣,海外漢學研究也從未中斷。由于語言不同,中國國學和海外漢學研究的交流和對話平臺需要建立并擴展。借助書籍出版,我們可以讓國學研究的重要成果在海外傳播,將海外漢學重要成果引入國內。中華傳統文化的現代闡釋將會在世界性的對話平臺上得到進一步的推進。
[1]馮國榮,侯德彤.中學西漸的歷史線索及其相關研究課題[J]. 東方論壇,2004,(5)
[2]項國雄,黃小琴. 傳播學視野下的“東學西漸”[J]. 新聞與傳播研究,2004,(4)
[3]耿昇. 十六——十八世紀的中學西漸和中國對法國哲學思想形成的影響[J]. 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6, (1)
[4]季羨林. 東學西漸與東化[J]. 東方論壇,2004, (5)
[5]成中英. 發揚中國哲學的融合力量與中國文化、哲學的現代化、世界化[J]. 東方論壇,2004,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