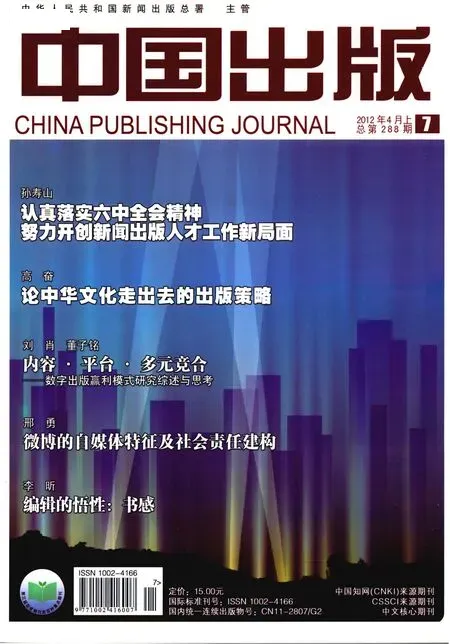編輯的悟性:書感
文/李 昕
不知道書感這個詞是不是通用詞,沒有見過別人使用這個概念。為了表述方便,筆者以為需要有這樣一個詞。什么叫書感?筆者認為書感是一種悟性,是對書的直覺判斷力,對書本質特征的感悟力。簡單來說,當一個編輯面對一堆文字和圖像材料,他應該懂得怎么編輯,怎么整理,怎么加工,才能使這些材料編得像一本書,一本令人喜歡的好書,一本符合讀者期待的書,具有這種能力的人就是書感良好的人。
從一個例子說起。1997年筆者在香港工作,當時香港剛剛回歸。香港三聯書店有一位很有才華的編輯,她今天已經是那家出版社的副總編了,這個人名叫李安,是女編輯。她告訴筆者要編一本書,這本書是她見到一個郵商產生的靈感,那郵商收藏了很多香港珍貴的明信片,有幾百上千張,其中不少甚至是孤品,有的是上百年前的,近期的也有幾十年了。李安說她想把這些明信片編起來,出一本《香港明信片精選1940~1970》。筆者當時剛剛到香港工作,不太了解香港,她的策劃筆者聽了以后很沒有把握和信心,但李安非常有策劃能力,過去已策劃過一些成功的選題,這一次她又非常自信,使筆者傾向于相信她的判斷,讓她試一試。可是那位郵商是無法獨立著書的,他文化程度很差,寫出的句子都不通,怎么辦?李安說,“沒關系,我讓他先寫出來,在每張明信片下加說明,然后我幫他改。”李安這個人極能吃苦,郵商作為作者,僅僅是提供了一些必要的素材,剩下的事全靠李安了,她親自動手完成了《香港名信片精選》這本書內容的定稿和整體結構的安排。從價格定位、市場和讀者對象定位,到開本、版式設計、使用材料、印制效果,具體到什么地方印雙色,什么地方印四色,用哪種紙效果最好,用什么形式的裝幀最討巧等,所有這些都由李安親自策劃,最后請陸智昌(阿智)先生來做設計(他現在是國內最著名的圖書裝幀設計師,當時他是香港三聯書店的美術編輯)。陸智昌在設計上又有新想法,新創意,他和李安的靈感一碰撞,精品就產生了:這本書出版了以后,獲得了香港圖書印制設計大獎。另一方面,書的銷售情況也很好,在香港三聯書店當年的新書中,這本書是相當暢銷的。
不過是一本明信片精選集,為什么會相當暢銷?筆者覺得這里有三個要素,第一是題材的稀缺性。它的內容具有獨占性。這個題材只有作者一個人有,別人沒有這個收藏;第二是裝幀設計形式上的獨特性。它是阿智設計的,阿智是非常有創意、才華很高的設計師,在設計中又把李安的策劃融入了他個人的風格;第三是對市場預測的準確性。怎么預測的呢?這里包含幾個讀者群。因為香港剛剛回歸,懷舊成為熱門題材,很多人這個時候會去買有關舊香港的書。這本書告訴你幾十年前香港的維多利亞港灣是什么樣,半島酒店是什么樣,加連威老道是什么樣,它激起了懷舊讀者的興趣。另外明信片本身是收藏品,會引起收藏市場的關注。還有一點我們起初并沒想到,這本書可以引起旅游者的興趣,特別是國外旅游者拿它當導游書。筆者有一次陪著上海來的攝影家,到尖沙咀海邊的天橋上散步,站在天橋向下看,有一個老外旅游團,穿著花花綠綠的服裝圍成一圈,中間站著導游,那導游手里拿的一本書就是這本,正翻開著給大家講解。原來這本書中有尖沙咀的舊照片和鐘樓的照片,導游根據這本書向游客介紹香港面貌的變遷。筆者馬上讓同行的攝影家把這個場景拍攝下來,后來放了一張好大的照片掛在三聯辦公室墻上。從這個小例子,筆者想說明,書感是對書的內容和形式獨特的把握,使特定的內容找到恰當的表達形式并使其成為有良好的市場表現的圖書。
筆者認為越是形式復雜的書,就越是要求編輯具有良好的書感。比如做大型叢書的時候要有很好的策劃,而策劃者的書感好與不好會使圖書的面貌乃至銷售業績有著天壤之別,所以出版社一定要用書感好的編輯策劃叢書、畫冊、圖文書。面對同一題材,同樣書稿,不同的編輯策劃出的圖書可能完全不同,原因在書感不同。
可能有人會問,是不是說形式越復雜,設計越繁難、越精細越好呢?不見得。有很多書在設計上外加元素非常多,但實際上是不好的。大量的圖片、圖板和插入文字把一本書弄得花里胡哨,不一定是好現象。筆者曾經看到過有一本《紅樓夢》的插圖本。開本蠻大,里面插了很多繡像,還插了很多小知識和注釋,都插在文中,左一個方塊、右一個方塊,版面上很破碎。《紅樓夢》本來就有100多萬字,再插這些東西篇幅就越發膨脹。出版者可能認為這樣的設計是一種形式創新。其實編輯的書感有問題,他沒有考慮到《紅樓夢》是需要連續閱讀的書,插入這么多的附加內容對閱讀有干擾。筆者認為這樣的設計在效果上是起了負面作用的。
并不是只有形式復雜的書才有書感的問題,一本很普通的文字書也有像不像書的問題,這也和書感有關。例如編一個作者若干篇文章的集結怎么編?筆者剛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當編輯時,老編輯親自帶,手把手教,告訴筆者怎么把一本書編得像本書,受益匪淺。現在很多青年編輯未必受過這樣的訓練,不知道集子應該怎樣編。一個顯而易見的規律就是不能把作品集編成大雜燴,各類文章不能簡單地混到一起。或者說各種不同主題的文章需要進行分類,各種不同形式的文章也需要進行分類。如何分,哪些文章和哪些文章分成一組?那么從目錄上應該如何表現?什么情況下要分輯,什么地方目錄上要空一行?還有要不要加前言,要不要加后記,要不要上附錄,要不要加注釋,要不要附參考書目,哪類書要,哪類書不要,哪類書在處理這類問題時的慣例是什么?這些問題全是書感的問題,當然這里講的書感是指書的編輯體例要符合一種規范,就是說這類書通常是這樣編的,有規律。現在筆者到書店去,發現很多出版物一打開目錄就能看出這個編輯沒受過訓練,他不知道文章該怎么分組,怎么分輯,不知道該加什么不該加什么,不知道什么東西要往前排,什么東西要往后排,所有這些都是因為書感不足。所以筆者建議各個出版社在這些方面應該請老編輯給年輕編輯介紹一下以往的編輯規范,這樣才不至于發生一些出版物編輯不符合規范的問題。
三聯最近出了一本《舅舅楊憲益的最后十年》。這本書是由楊憲益先生的外甥女趙蘅在陪伴舅舅的10年中,每天所寫的日記編輯而成的。趙蘅是畫家,素描畫得非常好,就在日記中插了很多素描,這很能增加書的人文情趣。書出得也很有特點,挺漂亮、很雅致。但書出來以后筆者發現,還是美中不足,在哪些方面呢?首先作者太喜歡那些素描了,所以一切都用素描,書中沒有照片。但對讀者來說,要看的是一本紀實性的書,需要加強現場感、真實感。例如,楊憲益先生最后10年住在小金絲胡同6號,這個小院是什么樣,但是書中沒有照片。因為作者就沒有想往書里插照片,而她素描也沒有畫到這個場景。還有就是書中內容非常簡略,因為作者是楊憲益先生的親戚,每天近距離觀察,她記下許多當日新發生的瑣事,但也有一些對她來說已經熟悉的事情,或許就不值得記在當天的日記里。但是當她出一本書的時候,光是把日記羅列在一起,很多背景就沒有交代,她沒有從讀者的角度想。比如說讀者希望更多地了解楊憲益先生的一生,而書中這樣的記述就不多。盡管這10年日記間或也涉及楊憲益先生回憶自己20世紀30年代怎么樣、40年代怎么樣,但這是不夠的。所以如果把這些日記編成圖書出版,使它能有回憶錄的閱讀效果,那就需要按照回憶錄的要求來補充,有些內容需要追憶,有些內容需要注釋,需要在作者的前言后記中交代。一些重要的內容因為寫日記的時候沒有想到出版的事,所以沒有記進去,但真要出版的時候就要從讀者的角度考慮。如果作者沒有意識到,編輯有責任提醒她。所以筆者認為這也是編輯的書感沒有到位。有時候書感意味著要使圖書符合讀者對內容和形式的期待,按照讀者的需要來做書。
也會有人問,你所謂的書感,要不要加入市場的考慮?筆者認為是需要的,因為書畢竟是商品,書要賣給讀者,市場的考慮實際上也是一種替讀者考慮。比如要出給小孩子看的童書,就不能做得太厚太重,讓小孩子拿著不方便。要做休閑類的書,就要讓讀者能看得很隨意,讓他能躺著看,就不適合做精裝。如果給老年人做書,字恐怕要大一點。所有這些既是人性化的考慮,也是市場化的考慮,同時是書感的反映。
筆者到香港三聯工作不久,正好趕上1998年香港金融危機,在那個時候香港書業一片凋零,銷售業績下降,市場萎縮了百分之三四十。出版社要生存,需要有一些應對措施。當時香港三聯的總經理叫趙斌,是從上海新聞出版局調過去的,有比較豐富的出版經驗。他跟筆者商量,提出要以螞蟻戰術應對,多出小書。因為小書制作相對容易,定價較低,品種多一些可以保持規模,但出版風險就被分散了。這種方式可以適應讀者購買力下降以后的圖書市場的新情況。要搞螞蟻戰術,自然也要考慮一些新的出版項目和出版形式。當時我們立即想到文庫本,想出一套三聯文庫。研究了日本的巖波文庫、講談社文庫,其特點是著眼于普及,定價都非常低。我們注意到現在國內出版界對文庫的理解似乎有偏差,很多出版社做的各種文庫都偏向收藏,書做的又大又重,這和日本人最初發明的文庫本不一樣。日本的文庫書開本很小,原來這些書在未收入文庫之前可能是大書,是精裝本,而文庫一律用簡本、口袋本,主要目的是普及。所以當時我們考慮搞一套三聯文庫。香港三聯當時也有一些多年積累的文學類圖書可以用這種方式出版,做成開本小、便于攜帶的形式。用什么樣的紙,做什么樣的開本就需要經過測算,也需要借鑒別人的經驗。到書店里看別人特別是日本人怎么做文庫,用什么開本,怎么設計,用什么材料。因為文庫在日本有一種專門的紙,紙的顏色微黃,他們甚至將這種顏色叫做文庫色,其實在我們看來就是米黃色的膠版紙,所以我們就在米黃膠版紙里面選擇,找到一種特別輕,但是很蓬松的優質紙張。這種紙因為蓬松而比較厚,如果排到200頁,看起來像300頁的書。因為開本很小,每面只排23行×24字,每頁552字,十幾萬字的書就可以排300頁,因為紙蓬松,看起來厚,拿起來輕,這正符合文庫的要求,讓讀者可以帶在身上,隨意閱讀。第一批18本三聯文庫,定價在20元~30元間。要知道在香港這是多么低的定價,因為香港圖書比大陸的圖書定價一般要高三四倍,這種書如果不用這種形式可能要賣到六七十元,但三聯二三十元就解決了,走低價路線。這套書出來蠻受歡迎,在市場上站住了。當時香港中聯辦的一位領導王鳳超同志說,“這套書太好了,每一本都是文學類和文化類圖書的經典,做得這么小巧,非常便于攜帶,我出差的時候都是放到口袋里,隨時可以拿出來看。”這套書出版的成功說明什么?筆者覺得可以說明書感正確,圖書定位就正確。這里的書感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要把握住文庫本的特點,借鑒人家成功的經驗;第二是圖書的整體策劃要符合讀者的期待,讀者期待這一類書要便于攜帶,那么設計時開本就要小,紙張材料就要選擇輕型的;第三是出版策劃也要符合出版社對經濟效益的預期,要好賣,這也需要使點巧勁兒,選擇蓬松紙張就是一個好主意。定價低,書仍然很厚,讀者就會覺得性價比高。
下面再說一下怎么培養書感。要為一本書找到恰當的表現形式,首先要研究書的形式,包括書的裝幀、設計、紙張材料、制作工藝,包括不同的內容在編輯上的形式要求,這些東西都要研究。所以,編輯要了解每類書的形式規范,知道各種不同類型的書別人都是怎么做的,去研究,去看,才能知道自己遇到這類書怎么編。
當然可以有創新,我們從來都是生活在創新中,所謂書感應該說也是允許創新的,但是也要依照規范,切忌出格,不能做完全違反規范的事。圖書的形式有一定的規范,要想研究這些規范,想學習別人在這方面的經驗,可以多從我國臺港地區和國外的圖書中借鑒,利用參加書展的機會。如果能參加法蘭克福書展最好,去不了的話,看看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也會有收獲。有很多國外以及我國臺港地區的出版商參加博覽會,通過這樣的機會以及和版權代理公司接觸,經常可以看到外國圖書的裝幀設計,這有助于編輯開闊眼界,增長見識。如果有機會參加海外書展,可以多帶一點國外出版社的目錄回來,從中可以借鑒到很多設計經驗。多研究別人的東西,多研究出版形式的創新會對自己培養書感有很大的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