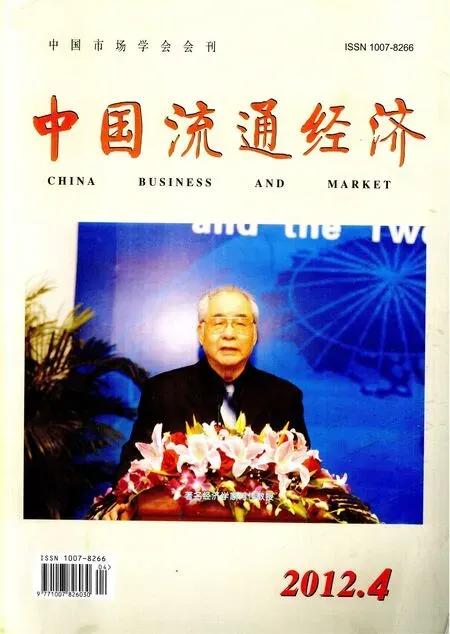略論澳大利亞早期產業政策
盛 浩
(北京物資學院經濟學院,北京市 101149)
從經濟總量和社會發展水平看,澳大利亞是一個發達國家,但一般認為,其經濟發展戰略和產業政策長期具有發展中國家的特點。伊恩·麥克萊和艾倫·泰勒指出:“在1900年以后直到20世紀70年代這段漫長的時間里,澳大利亞一直奉行不斷增強的干涉主義和內向型發展戰略”。[1]作為這種發展戰略的體現,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澳大利亞一直通過有針對性的保護政策促進制造業發展,即“通過關稅或配額,從需求方面保護個別的產業部門”。[2]綜觀澳大利亞的經濟發展戰略與產業政策工具,可以認為,澳大利亞的產業政策與實行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的某些拉丁美洲國家的產業政策較為相似。
20世紀60~70年代是發展中國家產業政策的全盛時期。實行進口替代工業化的拉丁美洲國家,通過產業政策推動了本國的工業化,但對制造業的過度保護,也造成這些國家制造業部門技術進步緩慢,效率低下。20世紀80年代之后的貿易開放,最終使其效率低下的制造業部門走向衰退,導致其經濟結構經歷了一個“去工業化”的過程,對本國經濟的長期發展造成不良影響。鑒于保護型的產業政策可能給經濟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曾有學者指出,1945年之后高貿易保護的澳大利亞經濟,將重蹈阿根廷的覆轍。[3]20世紀80年代之后,澳大利亞也開始推行經濟自由化改革,結果在經濟結構方面也出現了“去工業化”的情形。從統計數據看,其20世紀80~90年代制造業增加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明顯低于60年代。[4]但澳大利亞經濟并沒有出現拉美式的衰退,而是開始了長期的經濟強勁增長,甚至有學者認為澳大利亞80年代末期開始的經濟增長堪稱“奇跡”。[5]這與拉美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形成鮮明對比。經濟發展狀況的差異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產業政策的差異是一個重要方面。
一、政策背景
澳大利亞聯邦建立之前殖民地的經濟地位及豐富的自然資源,決定了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包括羊毛生產和金礦開采)成為其最主要的經濟活動。1890~1909年間,出口在澳大利亞GDP中的比重達到20%,其中有97%的出口產品為初級產品。[6]
與資源產業得天獨厚的發展條件相比,澳大利亞制造業的發展受到多方面因素尤其是市場因素的限制。地理上遠離世界主要制造業產品消費市場,貿易成本高昂;人口規模較小且比較分散。這都不利于企業獲得規模經濟效益,成為澳大利亞制造業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但澳大利亞的市場條件在制約其制造業發展的同時,又刺激了制造業的發展,因為當地市場對制造業產品有限的需求,不可能完全通過進口來滿足。因此,隨著居民人數的增加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澳大利亞面向內部市場的制造業也有所發展,1891年制造業產值按當年價格計算,在GDP中的比重達到了16.6%。[7]
1890年的經濟衰退之后,殖民地內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僅僅依賴大宗商品生產和出口的經濟,具有難以克服的不穩定性,城市制造業者發展當地制造業的要求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其結果是1901年澳大利亞聯邦成立之后,在經濟發展方面確立的“保護國內工業的模式”,又稱“澳洲聚落”(Australian Settlement)模式。這一模式的基本原則持續了70年,保護性的產業政策是這一模式的體現。[8]
二、政策內容
澳大利亞發展制造業,首先立足于滿足國內市場需求,因此其產業政策的主要內容就是通過一系列貿易政策工具,如提高關稅水平與執行差異化的關稅稅率,以及直接的進口數量限制等,保護與促進國內進口替代制造業部門的發展。
1907年,澳大利亞頒布了第一個保護主義的關稅法案。1921年的“格林關稅”(the Greene Tariff)將一般關稅水平提高了14%~26%。該法案規定,對汽車整車進口與零部件進口實施差別稅率,直接促進了澳大利亞本地汽車工業的發展。同年,澳大利亞關稅委員會成立,成為澳大利亞產業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機構,“任何一個擁有技術優勢的行業都可以得到關稅委員會為其‘量身定做’的保護”。[9]關稅保護下澳大利亞制造業的迅速發展,使20世紀20年代成為澳大利亞工業化開始的時期。
1921年之后,澳大利亞關稅水平仍持續提高,依據伊恩·麥克萊和艾倫·泰勒對歷史上澳大利亞制造業平均名義關稅進行指數測算的結果,可以計算出澳大利亞制造業平均名義關稅水平從1907年到1940年提高了156%,其中1929~1933年增幅超過了78%,1933年之后有所回落,但1940年仍比1929年提高了67%以上。[10]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澳大利亞開始通過進口商品許可證制度對進口商品進行直接的數量控制。60年代初大部分進口商品許可證被取消之后,關稅再度成為保護國內制造業最主要的工具。
三、政策特點
僅就通過貿易保護發展進口替代型工業的做法來看,澳大利亞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產業政策與拉丁美洲國家的產業政策確有相似之處。但不能僅就此認定二者屬于同樣的類型,甚至會導致相同的結果。澳大利亞與拉美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政策,在理論基礎、政策工具及重點產業選擇方面都存在著重大差別。
1.不以發展主義的經濟學理論為依據
拉美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政策深受發展主義經濟學理論的影響,因此,拉美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政策都強調政府“駕馭市場”,促進重點產業優先發展,從而帶動制造業的整體發展,實現工業化,改變本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戰后重建時期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澳大利亞國內也曾有過關于“結構政策”的主張,認為政府應當通過投資控制等手段直接干預產業結構,但在根深蒂固的經濟自由主義觀念的影響下,“結構政策”并未付諸實施。二戰后澳大利亞政府對制造業進行選擇性干預的做法,主要是出于促進就業和維持國際收支平衡的考慮,埃文·瓊斯指出,當時“人們普遍認為,使用選擇性的政策工具不僅是恰當的,而且是有效的宏觀政策措施不可分割的一個方面”。[11]因此,澳大利亞的產業政策所體現的經濟思想,不是發展主義的,而是凱恩斯主義的。
2.重點扶持的是消費品生產部門
在拉美發展中國家,不同歷史時期各國產業政策確定的重點產業并不相同,但總的來看,重點產業的范圍經過了從輕工業到重化工業過渡的過程,其中重化工業長期是產業政策保護與扶持的重點。在澳大利亞,雖然冶金、造船、印刷、制藥等產業部門都曾得到政府的保護,但以紡織品、服裝、鞋類(TCF)和載客汽車(PMV)為主。據統計,60年代末期政府對制造業的平均有效支持率為36%,而對紡織品、服裝與鞋類、載客汽車生產制造行業的有效支持率分別超過40%、90%和49%。[12]因此紡織品、服裝、鞋類和載客汽車產業被稱為澳大利亞“神圣的奶牛”。[13]盡管發展中國家重點產業的選擇標準不是單一的,但勞動生產率上升標準始終是一個重要的標準。澳大利亞的產業政策所選擇的重點產業,則包括了紡織品、服裝、鞋類這樣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這顯然更多地考慮了就業問題。
3.運用的政策工具較為單一,干預范圍有限
在發展中國家,產業政策的一個要點是政府干預下的重點產業的優先發展。促進重點產業優先發展的政策工具,包括政府直接投資建立國有企業,以及實施保護性貿易措施、壓低生產要素價格、提供財政補貼與優惠貸款、抑制重點產業產品市場競爭,以提高利潤水平等等。在澳大利亞,政府的產業政策工具主要就是通過關稅與非關稅壁壘,對國內制造業提供保護,而關稅委員會則成為澳大利亞早期產業政策的主要制定和實施機構。澳大利亞雖然也曾對國內基礎設施部門如航空、電信等實施國有化,但國有企業所占比重和涉及領域都極為有限,沒有改變私營企業在制造業中的主導地位。發展中國家通常采用的其他政策工具,如工資抑制及抑制市場競爭、人為促進國內個別企業擴張規模等,在澳大利亞完全沒有得到采用。
四、政策的評價
1.促進了制造業的發展
在產業政策的支持和保護之下,澳大利亞制造業加速發展。這首先表現為制造業產值的迅速增加,從1954~1955到1973~1974年,澳大利亞制造業增加值按2000~2001年價格計算,年均增幅為5.3%,高于澳大利亞歷史上的任何時期。1962~1963年,按當時價格計算,澳大利亞制造業產值在GDP中的比重達到了25.5%。[14]其次,制造業內部結構得到明顯改善。據統計,1968~1969年機械與裝備在全部制造業增加值中的比重為24.9%,雖然這一比重在1978~1979年下降到了22.5%,但仍然是最主要的制造業部門。[15]
2.對長期經濟增長起到了積極作用
對于產業政策促進下澳大利亞制造業的發展,澳大利亞政府與學術界均存在不同看法。由于澳大利亞制造業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產業政策的支持和保護,具有進口替代的特點,因此從靜態的角度分析,這很可能意味著資源錯配和效率損失,對收入水平的增長產生不利影響。但本文認為,以產業政策促進制造業的發展有其合理性,并對澳大利亞長期經濟增長起到了積極作用。這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分析。
(1)從當時澳大利亞經濟發展的客觀情況看,制造業的發展有助于實現充分就業和改善國際收支。從1901年到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澳大利亞制造業對于澳大利亞就業、GDP增長、出口的貢獻,總體上看都是不斷提高的。[16]而這段時間,包括小麥、焦煤、鐵礦石在內的國際大宗商品市場需求與市場價格,遠不能和80年代之后相比。澳大利亞學者麥克萊恩(Lan W.McLean)曾經指出:人們可能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制造業高保護時代,會在當時壓低澳大利亞的相對收入和勞動生產率……實際上,澳大利亞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20年中,受到保護的制造業部門在雇用人數和產出水平方面都達到了頂峰,其人均收入水平與美國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也越來越小。[17]因此,即使僅考慮靜態的資源配置效率和收入增長,也應當承認,澳大利亞制造業的發展有其歷史合理性。
(2)從發展的角度看,澳大利亞制造業因其較高的增長質量而為其他產業及總體經濟發展創造了條件。澳大利亞制造業中反映技術進步、且對勞動生產率有著很大影響的多要素生產率(MFP)上升速度較快。在20世紀60年代的10年中,澳大利亞制造業的多要素生產率年增幅不低于1.1%,從1969~1970年到1973~1974年,年增幅為0.9%,這雖然低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1.7%)的增長水平,但也表明澳大利亞制造業的產值增長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由技術進步推動的。[18]澳大利亞學者克拉克(Colin Clark)等人曾經論證制造業的地位和作用,認為制造業是資源部門和服務部門之間的紐帶,“顯然任何影響制造業的改變,都能夠直接或間接地對其他經濟活動產生影響”,而且“進一步說,制造業是高度可貿易的部門的事實,說明制造業能夠為總體經濟的健康發展提供一種視野或者說是一個窗口”。[19]因此制造業的技術進步與各種創新行為,必然為其他產業及總體經濟的長期增長創造條件。
澳大利亞早期產業政策的特點,決定了其雖然通過貿易保護機制促進了澳大利亞制造業的發展,但它不是發展主義的,不體現政府“駕馭市場”或“替代市場”的政策價值觀,而是從屬于宏觀經濟政策,是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經濟活動的有限干預。它在促進制造業發展的同時,不會造成市場機制的全面扭曲及普遍的尋租和結構性腐敗等問題,即產業政策的干預帶來的效率損失及總的政策成本較小。這就使澳大利亞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制造業發展與經濟增長具有較快的速度和較高的質量,也使澳大利亞20世紀80年代的產業政策改革能夠較為順利地完成,從產業基礎與政策兩個方面為長期經濟增長創造了條件,從而對澳大利亞長期經濟增長產生了積極影響。
[1]、[3]、[10]伊恩·麥克萊,艾倫·泰勒.澳大利亞的經濟增長[M]//丹尼·羅德里克.探索經濟繁榮.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25-56.
[2]Michael Emmery.Industry Policy in Australia[R].Research Paper No.3 1999-2000.Canberra:The Department of the Parliamentary Library,2010:4.
[4]Productivity Commission.Trends in Australian Manufacturing[R].Commission Research Paper,2003:18.
[5]森健.近年來澳大利亞的經濟形勢與存在問題[J].經濟資料譯叢,2002(3):1-7.
[6]Henry Willebald,Luis Bértola.Distribution,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Settler Societies,1870-2000[R].Paper Presented at Session 97"Settler Economies in World History"XIV 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2006:9.
[7]Bernard Attard.The Economic History of Australia from 1788:An Introduction[EB/OL].http://eh.net/encyclopedia/article/attard.australia,2010-02-04.
[8]Ray Broomhill.Australian Economic Boom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Australian Political Economy,2008(61):12-29.
[9]羅伯特·康倫.澳大利亞的產業政策[J].經濟資料譯叢,2002(3):103-116.
[11]Evan Jones.Macroeconomic Polic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Contested Parameters of Economic Policy in Post-World War II Australia[R].Report Number ECOP 2003-1,Sydney:Sydney University,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2003:12.
[12]Michael Emmery.Australian Manufacturing:A Brief History of Industry Policy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R].Research Paper No.7,1999-2000,2001:18.
[13]Evan Jones.The Evolution of Industry Policy under Howard,Australian Review of Public Affairs(Online)[EB/OL].http://www.australianreview.net/digest/2006/02/jones.html,2006-02-23.
[14]Productivity Commission.Trends in Australian Manufacturing[R].Commission Research Paper,2003:18.
[15]Productivity Commission.Trends in Australian Manufacturing[R].Commission Research Paper,2003:51.
[16]Productivity Commission.Australian Manufacturing:Today and Tomorrow[R].Commission Report,2007:10.
[17]Lan W.McLean.Why was Australia so Rich[R]?Working Paper 2005-11,University of Adelaide University,2005:23.
[18]Productivity Commission.Trends in Australian Manufacturing[R].Commission Research Paper,2003:65.
[19]Colin Clark,Timothy Geer,Barry Underhill.The Changing of Australian Manufacturing[R].Staff Information Paper of the Industry Commission,19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