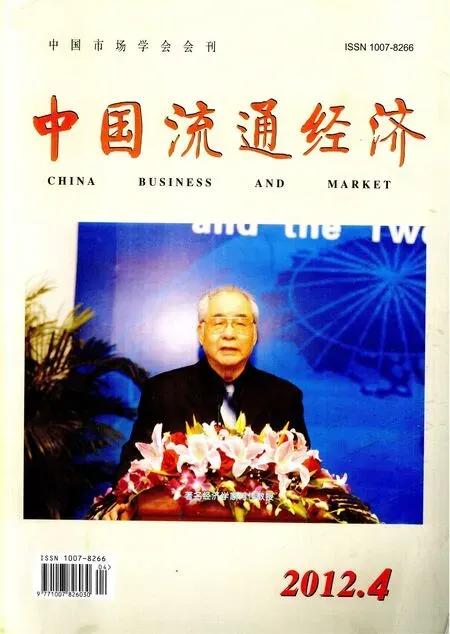知古鑒今 推動我國流通法制建設——《中國古代流通經濟法制史論》評介
石 橋
(北京物資學院,北京市101149)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尚琤博士的新著《中國古代流通經濟法制史論》(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年版),是一部深入研究中國古代流通法制史的學術專著。該書全面系統地探討了中國古代的流通經濟法制發展歷史,視角新穎獨特,結構嚴謹,史料豐富,條理清楚,梳理了中國歷史上流通法制理論和實踐的脈絡,并進行了深入的理論分析。總覽全書,大致有以下幾個特點。
1.初步確立了中國古代流通法制領域兩種治理思想體系
關于中國古代的流通思想,以往學者多從經濟史或者商業史角度進行研究。其實,即使從商業史角度研究時間也不是很長,從流通角度來研究的成果更是鮮見,該書可以說是從流通角度研究中國古代經濟或商業的開山之作。該書并未按照傳統經濟如農業、手工業和商業來劃分,拘泥于經濟史或商業史的編排體例,而是既包括傳統商業史中的貿易和市場,也涉及到了傳統農業中糧食的流通和儲存,還涉及到了手工業產品如鹽、鐵、酒、醋的專營專賣問題,甚至涉及到了交通道路和運輸機制的管理,特別對中國古代關于流通的思想進行了提煉和總結。作者將歷代流通經濟思想分為國家放任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兩大體系,因而具有一定的創新之處。如將西周的芮良夫、老子和黃老學派,春秋時的范蠡、白圭,漢代的司馬遷,宋代的蘇軾、葉適,明代的丘浚,都歸類于放任主義的陣營,將戰國的李悝、管子學派,漢代的桑弘羊,宋代的李覯、王安石都放在了國家干預主義陣營。作者對這些代表人物的思想進行了概括、提煉,并且對這兩大流通思想體系的具體實踐進行了客觀評價和總結。認為國家放任主義就是政府盡量不去干預商品流通,任其自由發展,其實踐帶來了漢初和唐初經濟的巨大成功,但并未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主流。而國家干預主義則強調國家積極主動地干預和調節商品流通,后者有西漢桑弘羊改革、王莽改革,唐代劉晏改革和宋代王安石改革等幾次重大實踐。這些改革在歷史上的作用是不同的,比如說劉晏的改革總體上是成功的,而王安石改革卻是失敗的。作者認為,古代在流通領域內干預主義成為主流,其特征是糧食的調劑和物價的平抑、重要商品專賣專營的實施、市場的管制和重征商稅以及對外貿易的嚴格管控。作者對于這些思想的評價是中肯貼切的。其實這兩種治理思想和理念在實際運行中各有所長、各有局限,很難籠統地說哪一種思想學說是完全正確的,關鍵在于這些思想運用到實踐中是否適時和得當,是否符合實際需要,這種關于流通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理論闡述和分析,對于理解我國歷史上流通領域的法制制度和政策措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2.深入探討了中國古代法制和流通的相互關系
該書不同于一般的流通經濟學著作,它不是泛泛地談流通經濟,而是重點談流通法制及治道。其法制色彩比較濃厚,搜集了非常豐富的相關法制史料,側重于從古代的法律政策來探討管理流通和干預流通的具體效果和作用。
該書側重研究古代法制在流通中的作用,研究各種法規和政策在管理經濟中所帶來的后果。其線索主要是圍繞“流通”和“國家法制”來展開的,并從這一角度來探討官商關系。古代官商關系直接影響著國家與商人或者政府與商業流通的關系。在中國古代,國家對于商品流通大致采取了兩種手段,一是放任主義,另一是干預主義。這兩種治理思想遠遠早于當代西方市場經濟國家運用的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政策。利用立法和行政的手段強化國家對于流通領域的介入,直接干預商品流通,甚至直接壟斷經營主要商品的生產和流通。總體來說,對流通領域實行國家干預原則往往成為歷代政府的首選。國家制定法律嚴格控制和管理商業流通,商事主體即商人往往沒有任何話語權,只能處于被動接受和服從管制的地位,商事主體沒有任何力量與國家抗衡,即使成立的各種商業行會組織也未能像西方國家那樣自主獨立,古代商業行會組織的主要功能是代替官府管理和征稅,少數情況下才充當了商人群體向官府訴求的渠道。作者認為,中國的歷史傳統即是國家習慣于運用行政權力強行干預商品流通,也曾起到過積極的作用,特別是在糧食的儲存、運輸和救災上,國家都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這種國家過度的干預也帶來嚴重的后果。特別是體制的腐敗嚴重影響了商品流通的發展,甚至造成商品流通的凋敝,大量史料都證明了這一點。比如唐代的借商令和宮市制度,明代的礦監稅使和皇店制度,清代商人也有輸納、過橋、過所、開江、關津、口岸等六苦。官員利用政治權力大肆盤剝和貪污,無視法紀,竭澤而漁,殺雞取卵,嚴重危害了正常的商品流通,甚至出現了“商賈斷絕,城市罷市”的局面。但是歷代統治者并未汲取這些歷史教訓,在流通領域幾乎沿襲了這一做法與制度。其重要的歷史教訓就是國家政治權力的肆意橫行,權大于法,無視法制,這是封建專制制度的痼疾,其結果是破壞商品流通的正常運行,造成“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的歷史老路。這也正是我國近代商品經濟不發達、資本主義萌芽屢遭扼殺的根本原因。該書正是通過闡釋我國古代法制與流通經濟的相互關系,揭示了古代法制制度與治理思想對商品經濟與商品流通的促進或抑制作用,從而進一步揭示了封建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對立以及資本主義取代封建制度的客觀必然性這一歷史規律。
3.采取了專題探討和史論相結合的著述方式
該書與同類著作如王文舉的《中國流通經濟發展概論》相比,在著述上也有著一些新的特點。作者并未完全按照朝代順序以編年體的方式著述,而是采用了專題分類的方式,分為六大專題進行梳理和探討。這六大專題即古代流通經濟思想、古代交通管理法制、古代糧食管理法制、古代專賣法制、古代市場管理法制、古代對外貿易管理法制。在每一專題內又將朝代納入其中,再按照朝代順序著述。在專題之下,將歷史劃分為先秦時期、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隋唐時期、宋代、元代、明代和清代七個較大的歷史階段,敘述這些歷史階段中重要的歷史事實,力避瑣細。還有一個比較值得肯定的地方,就是該書既有宏觀的視野,又有細節的論證;既有史料的敘述,又有適當的評論,史論結合,以論帶史,以史證論,相得益彰。其整個史料編排的合理性和有序性,表明了作者對于史料的掌握和駕馭能力,其在注釋上也比較周詳和規范,反映出作者嚴謹的治學態度。
綜上所述,尚琤博士的這部新著無疑是中國古代流通經濟法制研究中富有特色的一部力作。作者總結了中國歷史上各個時期涉及流通經濟的重要思想、重要法律制度和政策,較好地挖掘和整理了相關史料,并且對這些史料進行了深入分析,揭示出中國歷代不同時期流通法制的發展脈絡和進程,闡明了自己的觀點,形成了關于中國古代流通法制和流通經濟發展的規律性認識和研究成果,為中國古代流通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這些成果對于指導我國現代流通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對于通過流通法制促進流通產業發展,完善市場法制建設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流通是國民經濟的先導。但是長期以來形成的“重生產,輕流通”的局面并未徹底改變。當前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首先要深化流通體制改革,加強流通法制建設,規范流通市場秩序,只有知古鑒今,才能推動我國流通法制建設,這正是該書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