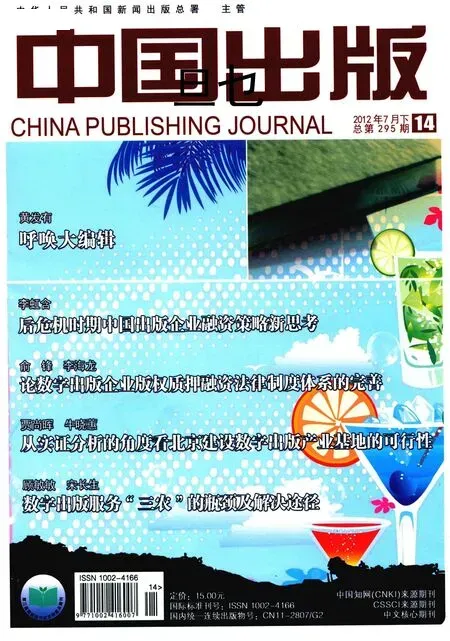《現代評論》與科學傳播*
文/沈 毅
《現代評論》(周刊)(以下稱周刊)創辦于1924年12月,存續四年后于1928年12月終刊。它是以北京大學教授為主體的一份綜合性周刊,標榜“精神是獨立的,不主附和”,“態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訐”,“言論趨重實際問題,不尚空談” 。[1]周刊是新文化運動之后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北京知識界一個很重要的媒體。周刊內容廣泛,包括時評、政論、小說、劇本、新詩、科技以及人文學術等,很多題材旨在繼承發揚《新青年》民主、科學精神。比較重要的撰稿人有胡適、徐志摩、聞一多、彭家沛、李四光、陶孟和、任鴻雋等。根據統計,周刊共發表與科學相關的文章約30篇,涉及的內容包括科學新知識、中國科學現狀、科學研究的地位以及對中西醫優劣的評價等。文章大多為國人所寫,少數為譯作。作者多為自然科學工作者,具有留學歐美、日本的經歷。他們學識淵博,平日里學術活動、社會活動均很活躍。
一、對中國科學現狀的認識
周刊的作者清醒地看到中國的科學發展水平的落后。如彭澤沛的連載文章《科學的流弊和中國》,介紹了大哲學家羅素對科學流弊的論述,作者不能原諒某些中國人借羅素批評歐洲科學流弊之機,興奮地尋找反對科學在中國落地生根的理由。他認為,中國還沒有資格去談論科學的流弊,因為中國的現狀是“沒有科學文明”。“現今中國最大的害惡,是軍閥的戰爭和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不是中國科學文明發達的結果。”中國科學還很落后,不配伴著羅素的節拍起舞,任何拒絕科學的借口都是錯誤的。[2]
署名滄生的文章《中國的科學》細數了中國科學落后的種種表現。作者認為,首先,中國專門的科學研究機構的極度匱乏,大學雖然也開設“物理化學一類的課程”,但僅僅是“一種教書的機關”,“研究自然無從說起”。其次,是社會上雖然有一些科學機構并辦有刊物,但數量很少,而且有一些還掌握在外國人手里。作者評論道,“我們雖然不敢附和說中國的科學還沒有萌芽,但是我們也沒有法子否認中國的科學程度,比人家差得還遠”。第三,一些科技類刊物的內容往往不屬于獨立研究的成果,“拾人唾余”,“東拉西扯,湊成篇幅”。第四,物理、化學類基礎學科的科研機構和刊物仍然闕如。[3]
科學的對立面是迷信,當時一般民眾對迷信的熱衷,反映出科學在中國的尷尬處境。楊幼炯在《民眾思想與社會科學》一文中指出:一方面百姓為戰亂和貧困生活所折磨,對未來沒有信心,聽天由命情緒泛濫;另一方面社會上的迷信組織如同善社、悟善社等又在傳播迷信,“妖言惑眾”,“報紙上關于‘降仙’、‘問卜’以及‘接神’、‘迎佛’的消息,差不多天天都有記載,甚而至于一省的長官,公然以命令行之”。作者感嘆道:“我們更不得不疑是置身中古的黑暗時代了。”
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現代評論》刊登的文章在新形勢下弘揚科學、掃除迷信,進一步揭示科學滯后、迷信猖獗的現實,對于警醒世人、認清社會改造的目標具有積極的意義。
二、對科學地位、科學精神的認識與呼吁
周刊的作者們從多個角度強調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國家和民族發展進程中的重要性。楊幼炯指出,“現在要推翻一般民眾的宗法思想,只有科學。因為科學是使人類思想進步的原動力,科學是研究物質實體,創造‘文明’;同時又利用這種系統的,創造新文化……我們就可以進而應用科學的法則,以解釋一切社會現象,使民眾對于環境生活有明白的認識。”作者對社會科學的社會改造功能表達得更為直接:“社會科學是根據科學的客觀性,考察社會現象,用歸納的方法,綜觀社會現象之公律,而求結論的。所以社會科學是推倒一切封建社會中神秘性文化的利器。”[4]
周刊作者比較多地談到了與科學精神有關的論斷,盡管他們并沒有直接使用“科學精神”的概念。陶孟和提出要正確地看待科學,科學是一個整體,不僅指自然科學,也應該包括社會科學。他認為時下片面為自然科學喝彩而冷落社會科學是很不正常的。他強調科學研究應“是指一切的科學研究,宇宙間一切的現象,自然的與人群的都包括在內”。他既否定傳統文化對自然科學的輕視,也否定近代以來把國運不昌狹隘地歸結為自然科學不發達。他在《社會科學的否運》認為“中國的前途,獨立的,光明的前途仍然與社會科學同命運”。他指出,凡涉及中國幾億民眾的社會組織、生產分配、權利義務,以及“實現社會的平和,與社會的公道”等問題,離開了社會科學是根本無法解決的。[5]
作者也探尋了中國科學長期落后、不成氣候的原因。滄生認為除了社會不良外,還在于國人目光短淺,對科學事業的重要性認識不足。[6]陶孟和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論題,統治者是不希望社會科學真正發展的,“軍閥的意志便是法律,槍刺的權威主持公道”。[7]“統治階級所最希望的是人民的愚魯,人民的馴服……他們所最不喜歡的是學生,尤其是學社會科學的學生”。陶孟和還指出,中國社會存在的浮躁風氣妨礙了正確的科學觀的建立。他感嘆很多中國人熱衷于表面上的大轟大嗡,滿足于淺薄的寫作,陶醉于廉價的吹捧。[8]任鴻雋同樣感嘆:“我們曉得在現在的社會中,要找飛揚浮躁的人才,可算是車載斗量,但是要找實心任事、不務虛名的人,卻好似鳳毛麟角。”[9]一個民族若不重視提倡和培養無條件的鉆研精神,每一位個體若達不到以無條件鉆研科學為樂趣的境界,真正的科學在這樣的國度里是不會扎根的,屬于全人類的創新和建樹也與其無緣。中國自科舉制度建立之后,讀書人的行為就打上了功名的標簽,對儒家思想的“信仰”也建立在功利基礎之上,所讀之書和科學也沒什么關系。在這樣的一種傳統文化的氛圍中若想培育起嚴謹、求真、心無旁騖的科學大樹,談何容易。
作者在撰文中提出了科學態度的問題。在他們看來,科學態度的樹立對個體、對國家都是非常重要的。這種科學態度,就是老老實實,實事求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夸大、諱言、矯飾是很突出的壞毛病,是科學特別是社會科學的死對頭,如同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一針見血指出的:“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圣賢禮儀之邦;明明是贓官污吏的政治,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都沒有!”[10]胡適一向提倡講老實話也正是基于這種認識。新文化運動時期任鴻雋也強調科學的本質在于承認事實:“我們要曉得科學的本質,是事實不是文字。”[11]周刊對科學態度的宣傳正與《新青年》精神一脈相承。楊幼炯在《民眾思想與社會科學》中批評說,中國社會科學界存在的諸多問題的實質,多為不尊重事實,不重視實際,主觀臆斷,投機取巧。他說有的學者“抄襲外國材料,以外國學者片面的理論作根據”;還有的學者把社會科學“當做哲學研究,不從事社會實地調查,對于民眾思想與社會現象,尤漠不關心,缺乏科學家實驗的精神造成‘閉門造車’的謬誤”。[12]
周刊刊載的文章有理有據,循循善誘,在揭示中國科學發展水平落后的基礎上系統闡釋科學地位、科學精神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關系,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其宗旨在于讓國人充分認識科學在國家現代化進程中舉足輕重的地位,讓國人摒棄妨礙科學發展的陳規陋見,推動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比翼齊飛。
三、科學知識宣傳與中西醫對比
《現代評論》(周刊)傳遞了中國科學活動的信息和科學研究的動態。如1925年1月24日刊登了李四光(署名仲揆)的《中國地質學會開會紀略》,記述了中國地質學會第三次年會的情況。該文特別提及了幾篇具有研究價值的、論述中國鄂西及甘肅、青海地質構造的論文,并特別指出科學論文能夠引起“普通社會”對科學探索的興趣,如古生物學與勘探的關系,《火星有人類居住么》等文章。[13]
對中西醫爭論是由署名西瀅(本名陳源)的一篇《閑話》引發。該文對協和醫院誤診梁啟超病情進行了言辭激烈的批評。由于在協和醫院的誤診,梁啟超在手術中被誤切除一側腎臟。陳源因此激烈地抨擊西醫。陳源是留學英國的博士,時為北京大學教授,大概是出于對他所崇拜的梁啟超遭遇不應有的醫療事故的憤慨,行文之間表現出明顯的情緒化。他認為協和醫院在拿病人“做試驗品”,“協和的醫生,在美國,也許最多是二三流”,“疑心就是西洋醫學也還在幼稚的時期,同中醫相比,也許只有百步和五十步的差異”。[14]
此后,周刊發表了支持和批評的稿件。前者指責協和醫院,言語之間激憤多于說理。后者指出所謂梁啟超被無端地拔了七顆牙屬于道聽途說,不滿意陳源作為熱心“提倡科學的人”,居然對中醫“大致其拳拳之意”。批評者希望國人能善待西醫:“科學在中國方是萌芽時代,愛護,培養,鼓吹,提倡,很為必要,不當于其破綻處加以宣傳,阻礙她的發展。”[15]
面對批評,陳源也做出了調整。陳源的變化顯然也與梁啟超本人對待協和醫院及科學的一番高姿態表態有關。梁啟超1926年6月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了《我的病與協和醫院》,專門澄清了對西醫的誤會。他說,“協和這回對于我的病,實在很用心……我真是出于至誠的感謝他們。協和組織完善,研究精神及方法,都是最進步的,他對于我們中國醫學的前途,負有極大的責任和希望……但是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智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16]
這場辯論的意義在于幫助人們理性地看待西醫和科學。辯論的效果或許令刊物和編輯們始料不及,陳源批評文章的刊發對發起辯論顯得有些倉促,險些演變成聲討科學的導火索。但對于提倡和捍衛科學這個大目標來說,這場辯論的結局還是理想的。
《現代評論》(周刊)的出版,在強化科學理念、營造科學氛圍、豐富科學知識和培養科學情趣方面,擴大了科學觀念的傳播,對驅除社會上彌漫的反科學的霧霾產生了積極作用。從報刊業務的角度審視,有的文章偏于專業化傾向,抽象理論闡述偏多,不免枯燥。對科學內容的定位尚不成熟,未能很好地解決專業、科普和輿論導向三者的關系。文章的學科分布也有些不平衡,地質、天文、生命科學等偏多,其他學科顯得薄弱。另外,周刊文章的轟動性少,沒有形成必要的“熱點”。相比之下,此前胡適主編的《努力周報》存續不過一年半,在科學傳播上曾發起過聲勢浩大的“科學玄學論戰”,對捍衛科學的神圣地位作用卓著。
注釋:
[1]現代評論(影印本)[M].長沙:岳麓書社,1999,第1卷,第1期,第2頁
[2]現代評論(影印本) [M] .長沙:岳麓書社,1999,第4卷,第89期,第5頁
[3]現代評論(影印本) [M] .長沙:岳麓書社,1999,第5卷,第118期,第4-6頁
[4]現代評論(影印本) [M] .長沙:岳麓書社,1999,,第3卷,第63期,第9頁
[5]現代評論(影印本) [M] .長沙:岳麓書社,1999,第4卷,第80期,第6頁
[6]現代評論(影印本) [M] .長沙:岳麓書社,1999,第5卷,第118期,第6頁
[7]現代評論(影印本) [M] .長沙:岳麓書社,1999,第4卷,第80期,第4頁
[8]現代評論(影印本)[M] .長沙:岳麓書社,1999,第4卷,第80期,第6-7頁
[9]現代評論(影印本)[M] .長沙:岳麓書社,1999,第6卷,第144期,第14頁
[10]《胡適文集》(2),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76頁
[11]袁偉時.告別中世紀:五四文獻選粹與解讀[M]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 373
[12]現代評論(影印本)[M].長沙:岳麓書社,1999,第3卷,第63期,第10頁
[13]現代評論(影印本) [M] .長沙:岳麓書社,1999,第2卷,第47期,第18-19頁
[14]現代評論(影印本)[M].長沙:岳麓書社,1999,第3卷,第75期,第9-10頁
[15]現代評論(影印本)[M].長沙:岳麓書社,1999,第5卷,第114期,第18頁
[16]夏曉紅.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中)[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