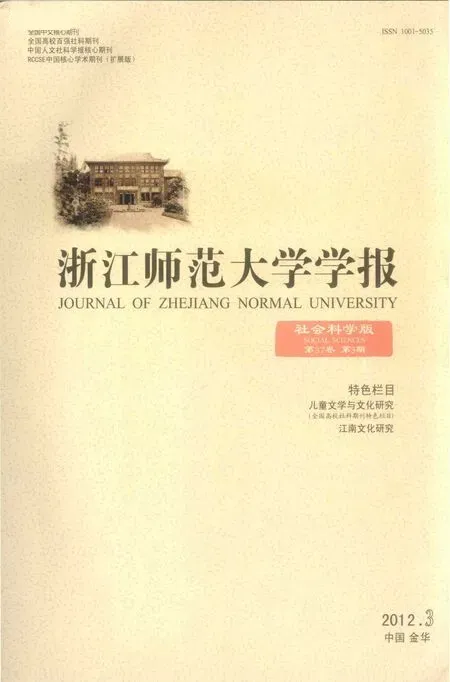論兒童漢字習得的美育功能*
章 輝
(浙江大學 美學與批評理論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28)
丁海東等將兒童精神的基本特質總結為“自我中心化、整體性混沌、潛意識化和詩性的邏輯”。[1]的確,兒童精神雖尚未發育成熟,理性尚未發達,然而在他們身上卻潛藏著成年以后復雜的意識形態的始基。因此,抓住兒童階段精神的特點,通過美育誘發兒童的詩性邏輯,促使其健康成長,為日后理性的發展和成熟創造互補的土壤,是非常必要的。但在歷來的兒童美育中,一個很大的失誤在于僅僅把美育等同于讓孩子學習歌舞、繪畫等藝術,而忽略了母語習得中的美育功能。這種美育上的忽略,遺忘了漢字本身的審美建構。馬克思曾普泛性地斷言“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2]事實上,人也遵循美的原則來建構語言。換言之,語言本身也是由人的審美意識和詩性思維所創造的。卡西爾曾指出:“我們日常的語詞并非純屬語義的記號,而且還充滿了形象和具體情感——它們是詩意的和喻意的表達,而非僅僅是邏輯或‘推論性’的表達。”[3]131漢字是建立在象形基礎上的音義結合的語言系統,卡氏這一論斷用漢字系統來加以印證尤其具有說服力。
人生識字始于兒童時期。19世紀德國教育家第斯多惠說:“教育的藝術不在于傳授的本領,而在于激勵、喚醒和鼓舞。”[4]同樣,對于兒童漢字教學,不應簡單地將其視為認字的過程,而應使其成為喚醒學生美感和道德感,激發鼓舞他們人文精神的契機。兒童精神是潛意識化的,特別是在兒童早期表現尤為顯著。如能在兒童階段結合漢字中的審美因素來進行審美教育,將能起到潛移默化的良好效果,在他們將來美好性格的形成上發揮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構建審美形態,啟迪審美意識
歷史上,漢民族獨特的審美心理和取向產生了豐富的審美特質。筆者認為,作為審美建構的漢字系統至少具有以下四種傳統審美形態:簡約、中和、神妙、氣韻。
(一)漢字的“簡約”之美
中國傳統美學歷來崇尚簡約。縱觀傳統藝術構造,無不極為簡約。比如二胡僅有兩根琴弦,水墨畫僅有黑白二色。漢字字形的建構也完全體現了簡約之美。漢字不是拼音文字,但筆者認為,每個漢字都無非是由橫、豎、撇、捺、點組合而成的,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認為,這五種基本筆畫是漢字的字母,漢字是它們用“拼”出來的。對比其他語言,英語有26個字母,俄語有33個字母,而且每個字母還有大小寫的不同,因此每個漢字的組合部件是極為簡約的。不但書寫結構簡約,字音也同樣如此。每個漢字的發音只有一個音節,且多為單輔音+單元音式,沒有歐洲語言那樣復雜的復輔音,非常清晰。對于心智尚未成熟的兒童來說,漢字這種簡單的構造元素更易于他們掌握。
史文霞認為:“從中國古典美學的角度來看,語言藝術美的實質在于簡約之美。”[5]漢字的簡約美無疑是一種很好的例證。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漢字簡約而不簡單。正如二胡雖僅有兩根琴弦,卻五音齊備;水墨畫雖僅黑白二色,卻氣象萬千一樣,在二維空間里,五種基本筆畫卻可以根據需要構建出幾萬個不同的漢字來,可謂潛藏著無限變化的空間。17世紀的萊布尼茲早已看到這一點,指出漢字“根據事物的可變性呈現無限多樣的筆劃”。[6]116此外,從字義來說,雖然書寫、讀音建構簡約,但每個漢字卻都蘊含著豐富的意義和強大的構詞潛能,這是其他文字很難做到的。所以這樣看來,“語言的簡約美……是語言發展過程中一種更高層次的追求。”[5]
因此在漢字教學中,教師可以因勢利導,就漢字的簡約之美啟發兒童以少馭多的審美思維,提高他們掌握外部世界的能力和水平。
(二)漢字的“中和”之美
儒家美學尤其推崇中和,可以認為,中和是儒家哲學為靈魂的審美形態。“中和”即中正、平和,它首先基于這樣的認識:承認對立,但更主張對立的統一、世界的多元化和思想多元化,學會包容正反兩面意見加以融合,使事物始終處于合作、和諧狀態。對此,抽象能力較弱的兒童是很難加以理性掌握的。而在漢字習得中,他們則能較容易地從感性上理解這種哲學關系。例如教師可以提示他們,漢字的基本筆畫都是對立的,如橫與豎、撇與捺、勾與提,都呈對立狀態,而每個漢字卻是由這些對立元素所和諧統一而成。這樣解說,對立統一關系這個復雜抽象的概念就在童心的土壤里得到了感性的播種。
中正還含有節制、秩序、規范、對稱等美學含義。漢字字形向來講究布局控制、書寫秩序與對稱、呼應等關系。萊布尼茲認為,一種完美的文字應該以漢字為藍本來創造,使它“具有漢字優點”,即“根據事物的秩序與聯系將筆劃完美地聯系起來”。[6]116在書字教學中,教育者可以引導孩子發現漢字規范字形控制(每個字都呈方塊形,并占據大小一致的空間),嚴格講究筆順等特點,以及明顯的對稱美,筆畫的呼應關系,讓他們在幼小的心靈深處體會儒家美學的感性特征。
中和強調和諧,追求人與自然的“天人合一”狀態。這一點在漢字里有鮮明的反映。卡西爾認為語言中具有一種直觀的性質和意蘊,不過這種直觀性在西語中并不明顯。而漢字里大量的象形字,就是對自然萬物形狀的詩意欣賞與直觀摹寫。除了象形字以外,還有大量以象形字為部首的形聲字(如大量以口、宀、山、日、水、火、田、石、禾、糸、月、舟、車、門、阜、雨等為偏旁的漢字),讓人既知聲又見形,從字形中見到自然萬物。教師引導兒童發現這一特點,不僅能讓孩子懂得漢字造型的理據,也有利于兒童理解中國傳統審美形態中效法天地、崇尚自然的重要思想。
(三)漢字的“神妙”之美
在視覺形象的“形”、“神”關系上,傳統美學重“神”而輕“形”。漢字作為詩意的語言系統,本身就是顯現事物靈魂的藝術品。它在描摹事物自然形狀的同時,更重視對其內在精神本質的勾勒,因此,它超越了形,達到了“離形得似”、“形神兼備”的境界。
例如,“悅”的本字“兌”,縮小簡化了人的軀體和四肢,而突出了其上翹的嘴和嘴角的笑紋,將喜悅的神態描繪得淋漓盡致。“見”字的原始形象忽略了人體的上半身,讓人看到的只是行走的兩腿上一只張望著的碩大眼睛的形象,突出了人的探索、發現之神情。而“聽”字的原始形象更只繪出了一只大耳朵和一張(或兩張)說話的嘴。同樣,動物字也貫徹了重神的思維,“虎”字突出其威嚴的身軀和大口,“兔”字突出了其長耳和短尾,而“牛”、“羊”字更加離形得似,造型干脆不繪身軀和四肢,只展現其頭部,注意以其獸角的上彎和下彎特征來加以區別。《淮南子·說林訓》提出,失敗的造型藝術是“謹毛而失貌”,即小心地繪出了細微而無關緊要之處,卻忽略了整體特征,也喪失了美感和意蘊。正如顏翔林先生所言:“如果符號形式直接簡單地呈現藝術文本的意蘊,兩者距離過于靠近,使欣賞者一目了然,就缺乏從容品味的余韻,造成藝術趣味的淡然枯燥;反之,如果符號形式和文本前者意義存在遙遠的距離,使人在兩者之間尋找不到任何邏輯聯系,滋生不知所云的淡漠感覺,也是失敗的藝術創造。”[7]歷史上許多象形文字系統,因過于求形似而繁復、僵化,最終都被廢棄。而拼音文字的符號和意義無任何理據聯系,難以產生美感。只有漢字象形而離形、重神,其生命活力與美感保持至今。
蘇軾有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這恰好說明了兒童在審美認知中重形似的局限性。席勒說:“一切的關鍵在于把形式從內容中解放出來,使必然不沾染任何偶然。”[8]67筆者認為,漢字的重“神”,就是一種發現必然,不為偶然所拘束的表現。抽象思維是兒童缺乏的能力,所以,在漢字習得中為兒童辨析出漢字重“神”的建構思維,能啟迪兒童在認識事物中抓住本質特征,破除偶然揭示必然,提高其通過形體展示精神的哲學思辨能力。
(四)漢字的“氣韻”之美
“氣韻”形態中的“氣”指的是一股生命的活力。馬大康認為:“如果說,口頭語言更直接地歸屬于感性生命,它原本即生命的吶喊,那么,書寫則更多地與理性、邏輯思維聯系在一起,并因其媒介的間接性,在開拓了形上思考空間的同時,總難免與感性生命隔著一層。”[9]不過,馬先生在張揚口語生命感的同時卻忽視了漢字書寫建構的生命特征。事實上,在漢字里充滿了生命的跡象,呈現著普遍存在的萬物生命。成千上萬的漢字以艸、禾、木、竹、麥、麻、羽、鳥、隹、牛、羊、豕、馬、鹿、兔、犬、犭、虎、象、魚、豸、蟲等象形字為偏旁,因此在閱讀漢語時,字里行間處處可見草木鳥獸的感性生命。此外,傳統美學的五行相生觀和天人合一觀,使我們傾向于對風、雷、雨、雪、天、日、月、星、水、火、電、土等自然物、自然元素和自然現象也賦予生命力的想象,認為它們也和人類一樣有生命活力和自行主宰并生發化育他物的能力,由此在造字過程中大量以這些形象作為漢字偏旁。這樣一來,整個漢字系統就流動著一股生命氣息。
劉文典先生曾在教學中特意利用到這一點。據其學生記載:“當他解說《海賦》時,不但形容大海的驚濤駭浪,洶涌如山,而且叫我們特別注意到講義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滿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師說姑不論文章好壞,光是看這一篇許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濤澎湃瀚海無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10]因此,教師如能在漢字習得中結合相關教育內容啟發兒童體會漢字的生命美學意識,將會使兒童的身心和漢字的靈魂一樣生氣勃勃。
“氣韻”的“韻”意味著一種類似于音樂的節奏性和規律性。語言的“韻”之美,首先訴諸于聽覺。聽覺美是東方語言的特質。盧梭在《音樂辭典》里贊美說,“東方語言如此響亮、如此富于樂感”,[6]309并將這種美歸因于音調:“東方的語言……一切效果都表現在音調上。”[6]331漢字發音之美的確很大程度上來自抑揚頓挫的聲調。不過,漢語的聽覺美不僅僅表現在音調上,它還有更多獨特之處。由于漢語長期以來以單個漢字為本位而不以詞為本位,故而這里需通過詞的層面來展示漢字的聲韻之美。我們發現,漢語非常善于運用重疊的手段來造成節奏感。更為重要的是,漢字的音節簡單,沒有復輔音,使得雙聲詞(如參差)、疊韻詞(如從容)等形式易于形成,這樣就使重疊不至于單調,使聽覺美豐富而富于變化。筆者還認為,節奏是廣義的,它主要訴諸聽覺,而又不局限于聽覺。從字音上看有雙聲詞、疊韻詞,而從字形上看我們也發現有雙形詞(即形旁相同,如絡繹、驚慌)。它們造成一種視覺上的節奏感,使人體驗到類于聲韻的審美通感。更有趣味的是,雙聲、疊韻詞大部分又同時是雙形詞(如澎湃、招搖),給我們帶來一種視聽覺雙重審美意蘊。卡西爾說得好,語言活動“總是浸潤著主體的、人格的生命之整體。言語的節奏和分寸、聲調、抑揚、節律,皆為這種人格生命的不可避免的和清楚明白的暗示——都是我們的情感、感受、旨趣的暗示”。[3]138我們正應該好好利用“氣韻”這種其他文字所罕有的美學特質,通過文本認讀、書寫、朗誦等形式,激發兒童的美感和樂感。
二、培養道德情懷,啟思倫理自律
(一)漢字的道德培育功能
古代哲學家們高度重視美與倫理道德的聯系。如我國儒家美學的“比德說”積極將自然美與道德美加以比附,而古希臘的柏拉圖則強烈反對摹仿壞人壞事的戲劇和詩歌。康德則最終做出“美是道德的象征”[11]這一明確論斷,深刻地指出審美活動的客觀目的就是通過無利害關系的自由和愉快的實現,將主體引渡到善的境界,從而實現審美和道德的精神合流。
我們發現,漢字的字形里傳達著豐富的道德教訓。比如“孝”字,從原始字形看,就是一個小孩攙扶或背負著一個頭發稀疏的老人走路的形象,生動直接地體現了我國古代的倫理觀念。再如“悌”字,意為敬愛兄弟,而字形從心從弟,即指明心懷兄弟為悌。又如“信”,人言為信的會意傳達著言談需要講究誠信的道德教訓。“崇高”的美學范疇源自西方,而在古代漢語里,則有“大、崇、巍巍、蕩蕩、湯湯、浩然”等概念與之大體相當。這里就充分反映出儒家“比德說”的審美思維了:“大”字讓我們從人體的巨大去聯想人格的偉大,“崇、巍”等字,讓我們從山嶺的巍峨中去體會人格的崇高,而“蕩蕩、湯湯、浩然”則從水域的巨大廣闊里讓人領悟崇高不可抗拒的力量。
當前的美育常常忽略了美與倫理道德的溝通,把美育簡單地等同于形式美的教育。而童年正是一個人形成道德觀念的最重要時期,如果教師能在漢字教學中點出其倫理美學意味,則兒童的德育無疑可以自然滲透,達到潤物無聲的效果。就如席勒所言:“審美趣味對義務有利地調整我們的感性本能,使意志能夠以比較輕松的道德努力來履行道德的命令。”[8]250
(二)漢字的倫理啟思功能
古代倫理學基本等同于道德、品性之學。從伊壁鳩魯學派的觀點出發,近代倫理學突破了道德學的藩籬,把倫理學看作研究人生目的和生活方式的學問。正如伯納德·威廉姆斯所言,倫理學是研究“我應該怎樣生活”的學問。它關注的不僅僅是人類的責任、義務,還更關注人生的目的、意義、價值和生活態度、自律規范等問題。對于有著未來人生無限可能性的兒童來說,倫理啟思是極為必要的。大量的漢字從字形上就有著倫理的啟思,即對“我應該怎樣生活”的啟思。例如,教師可利用“信”字“人言為信”的含義,啟示兒童講誠信,重口頭承諾;可利用“武”字“止戈為武”的造型寓意來教育兒童反對暴力、愛好和平;又可利用“臭”字,啟示兒童不可驕傲自大的倫理品行。這對于兒童今后倫理自律能力的形成,將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倫理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人文精神。在當今技術壓倒人文,工具理性侵占精神家園的時代,兒童倫理教育中的人文思想內容尤其顯得迫切,而漢字習得恰可助其一臂之力。人文精神思潮來自西方文藝復興時期,它是一種普遍的人類自我關懷,表現為對自身生命、尊嚴和價值的關切和追求。事實上,近世所談論的“人體美學”和“身體美學”,就是人文精神在美學領域的顯現,而漢字系統里就早已內涵有這種人文思維。漢字處處凸顯了人的形象,表現了存在的自我意識,并把這種自身的存在當作最根本的審美觀照對象。例如,漢字人旁(包括單人旁亻、雙人旁彳,以及女字旁、子字旁)字很多,還常把人體構成部分的形象作為偏旁,如身、肉(包括月)、頁(頭的形象)、首、面、手(包括扌、又)、足(包括止)、口、耳、心(包括忄)等等。萊布尼茲甚至認為,幾乎大部分漢字的結構都很像人體。
雅斯貝爾斯指出:“所謂教育,不過是人對人的主體間靈肉交流活動,包括知識內容的傳授、生命內涵的領悟、意志行為的規范,并通過文化傳遞功能,將文化遺產教給年輕一代,使他們自由地生成。”[12]作為一種文化遺產,漢字正可以啟思這種“生命內涵的領悟、意志行為的規范”。在兒童漢字教學中,教師要能認識到這種漢字建構中的道德象征與人文內涵,在我國目前大力發展經濟、科技,道德水準滑坡,物質欲望膨脹而生命內涵遭到壓抑的今天,這種教育將十分必要。
三、促進創造性思維,激發想象能力
(一)漢字建構與創造能力
創造力和想象力是我國兒童最缺乏,也最需要培養的能力。漢字的審美建構能激發他們的創造性思維和想象能力。
首先談創造性思維。漢字習得,除了音義的掌握而外,還包括字形的辨識和書寫。不難發現,拼音文字書寫較為簡單。以英文為例,只要掌握了26個字母的寫法,書寫習得即告成功。而漢字書寫卻遠非如此,它是一個從兒童開始卻近乎需要用一生去習得與提高的技藝。為何會有這樣的特點呢?這是由漢字的形體結構決定的。
前文提到,漢字結構有中和之美,書寫講究秩序和規范。但同時,又可以有間架結構和布局的變化和創造,給個人書寫的創造性留下巨大的空間。正如李運富所言:“漢字的筆畫和構件擺布在兩維平面的方塊內,每個字的空間相同,整齊,……便于匠心布局和變異書寫,從而具有藝術審美價值。”[13]這種在規范與限制中的自由發揮余地,乃是書法藝術所得以產生的原因。它使書寫能夠承載和涵括豐富的個人風格,使得“字如其人”成為可能。在書寫教學中,教師若能點出這一層面,讓兒童的個性在書寫結構和布局上適當有所發揮,可以培養他們的美學創造能力,避免千人一面的印刷字體和僵化思維。
(二)漢字意象與想象能力
漢字習得能養成兒童運用想象力的習慣。這是因為,漢字系統充滿審美意象,而審美意象的生成需要想象力的發揮。
審美意象必然要具有一定的象征性和哲理性,而這些都是漢字形體所具備的。M·V·大衛在1636年就指出,象形文字“是更優美更莊重的書寫符號,比較接近抽象的東西。它們通過對符號或相當于符號的東西的巧妙結合,而將復雜的推理、嚴肅的概念或隱藏在自然或上帝心中的某種神秘徽章一下子展現在學者的理智面前。”[6]118這一論斷用來詮釋漢字的審美意象性極為恰當。漢字具有明顯的象征性。莊義友認為:“漢字本質上是一套象征性符號系統。”[14]例如“尹”字,用手執權杖的形象來象征管理百姓的權力。又如“義”字(“義”的本字),用羊頭掛在長柄的三叉武器上面,象征皇帝或貴族的威儀。黑格爾說:“真正的象征本身就帶有謎語的性質,……(謎語)屬于有意識的象征。”[15]謎語式的求解性是漢字的獨特魅力。很多漢字看起來就像謎語,引起人們的好奇和猜測。例如“彳亍”一詞甚為怪異,有人通過它和“行”字字形的關系來推測其義。而如“滅、忍、攀”等字,不少教師也常在教學中發揮想象力,從字形上為兒童做出拆分式解讀。同時,漢字字形本身還表達著一定的哲學思想。這一點也早就得到了國外學者的承認,萊布尼茲就指出漢字更具有哲學特點并且基于更多的理性考慮。如“魯”字,本義是“美好”,它用嘴里吃到魚的美味的形象傳達了這樣的藝術哲學觀念:美首先是物質的感性存在,與人的感官享受不可分離。再如“福”字,是雙手捧著大酒壇在祭臺前求神賜福的形象,它表現了這樣的人類信仰:幸福來自上天的賜予。
獲取漢字的意象之美需要想象力。康德早就界定說,審美意象是指想象力所形成的某種形象呈現。其后黑格爾斷言:“最杰出的藝術本領就是想象。……想象是創造性的。”[16]而薩特更主張用想象來界定美的本質。他說:“美是一種只適合于想象的東西的價值。”[17]292又說“審美的對象是某種非現實的東西”,“我所稱之為美的,正是那些非現實對象的具象化”。[17]285-287即美不是客觀實體,而是通過想象力產生的審美意象。
意象并非實在形象,而存在于想象之中。只有發揮想象才能領略漢字的意象之美。現代兒童教育學認為,兒童精神的感性成分占絕對優勢,而感性精神成分是審美的、幻想的、直覺的、感悟的、模糊的、沖動的、熱情的。故而,好的教師應當利用漢字的哲理性和象征性,積極激發兒童的想象力,達到美育的效果。
四、結 論
我國當前教育界已經達成這樣的共識:“教師在教學實踐中,要善于發現教學內容的美,開掘出這些美,并在教學中顯現這些美,在此基礎上來創造美。”[18]對于兒童來說,發現適合教學內容的美并以此構思美育教學尤其是教師需要思索的問題。象形基礎上的音義結合的漢字系統,是按照漢民族審美心理來建造的恢弘的藝術體系。美國詩人龐德曾感嘆說:用象形構成的中文永遠是詩的,情不自禁的是詩的,相反,一大行的英語字卻不易成為詩。誠然,形簡意豐、中正平和、蘊涵生命、流動韻律、培育道德、啟思人文、便于創造、激發想象的漢字系統,是一種充滿詩意的高級審美形態。因此,漢字習得是從感性層面上接受美育的最佳途徑之一。對于兒童來說,他們將在認字中逐步開始生活于語言文字的符號世界。因此,要抓住漢字習得的機會,讓兒童們感受美的熏陶,潛移默化地接受美育。要讓他們的詩性邏輯在漢字習得中獲得養料,以期為兒童未來理性的發展插上審美與想象的翅膀。
因此,本文熱烈呼吁,將兒童時期的漢字習得作為全新的美育道路。“童年不僅是人的根基,而且是人的核心。如同樹木一樣,那最初的年月被記錄在年輪中最核心處,盡管它已被后來的歲月所包圍,但那最初的年月仍然發揮著核心作用。童年,就是人這棵樹最中心的年輪,它是人這棵樹的樹心,仍然在默默地滋養人這棵樹木。”[19]教師要善于開動腦筋,發現漢字系統的審美特質。在人的一生的核心階段——兒童時期——這段可塑性極強的頭腦中,構建審美形態,啟迪他們的審美意識;培養其道德情懷,啟思其倫理自律;促進其創造性思維,激發其想象能力;讓兒童精神從一開始就得到最健康完美的滋養。
[1]丁海東,杜傳坤.兒童教育的人文解讀[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8:26.
[2]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中央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8.
[3]恩斯特·卡西爾.符號·神話·文化[M].李小兵,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
[4]袁銳鍔,張季娟.外國教育史綱[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265.
[5]史文霞.中國古典美學思想與語言的簡約美[J].外語藝術教育研究,2008(2):85-86.
[6]雅克·德里達.論文字學[M].汪堂家,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7]顏翔林.懷疑論美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63.
[8]席勒.審美教育書簡[M].馮至,范大燦,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
[9]馬大康.詩性語言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194.
[10]勵志.國學大師劉文典師[J].中國人才,2010(17):45.
[11]康德.判斷力批判上卷[M].宗白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201.
[12]雅斯貝爾斯.什么是教育[M].鄒進,譯.上海:三聯書店,1991:3.
[13]李運富.漢字構形原理與中小學漢字教學[M].長春:長春出版社,2001:6.
[14]莊義友.漢字符號象征性探解[J].語文研究,2000(1):23.
[15]黑格爾.美學:第一卷[M].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357.
[16]黑格爾.美學:第二卷[M].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120.
[17]薩特.想象心理學[M].褚朔維,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
[18]周施清編.小學美育化教學與兒童創造性發展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24.
[19]劉曉東.兒童精神哲學[M].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