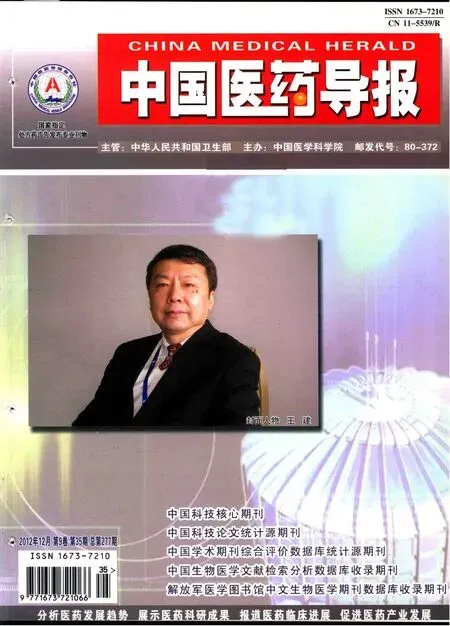高等醫藥院校如何傳承中醫藥文化
單寶珍 陳吉炎 王雪芹 馬豐懿
湖北醫藥學院附屬太和醫院,湖北十堰 442000
“文化”是一個常用詞。《周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有了文化可以變鄙俗為文明。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民眾的精神家園。中華文化為中華民族發展壯大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決定)。中醫藥文化是以哲學的辨證觀、宇宙觀、生命觀、價值觀(審美觀、是非觀、善惡觀)為基礎,探討生命與疾病防治的認知文化,注重發揮機體自身的抵御疾病能力,是中華民族數千年積累形成的防治疾病、保健養生等理論和方法的總和。傳承文化是大學的四大職能之一,高等醫藥院校不僅是培養優秀醫藥人才的搖籃,也是傳承醫藥文明的主戰場,不僅要培育和傳播追求真理、大膽創新、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現代大學文化,還應該借鑒和傳承中醫藥文化中科學的思維方式和預防為主的健康養生理念,學會應用中醫藥文化中的“仁、和、精、誠”去詮釋和傳播“真、善、美”。
1 以“仁、和、精、誠”彰顯“真、善、美”的醫德觀
中醫藥文化核心內容體現在對人們生命觀、價值觀、道德觀的影響和對生命與疾病防治的認知方式,以“仁、和、精、誠”來詮釋和傳承“真、善、美”。
1.1 以“仁”為本的道德觀
孫思邈倡尋公正、無私的醫者的醫道,是第一個完整論述醫德的人。孫思邈在《大醫精誠》中說:“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蚩,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仁”即“醫乃仁術”是醫學倫理道德的總原則。醫者必須具備仁者愛人、生命至上的倫理思想。“仁”一是指醫者之仁,即“不得瞻前顧后,自慮吉兇,護惜身命”,以救死扶傷、濟世活人的宗旨,宣染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愛護生命,崇尚不計個人得失安危的仁愛和奉獻精神;二是指醫術之仁,即醫術要精[1]。
“仁”,還體現在同行之間應道謙和,不得在背后無根據的詆毀他人,抬高自己。正如孫思邈所言,“夫為醫之法,不得多語調笑,談謔喧嘩,道說是非,議論人物,衒耀聲名,訾毀諸醫,自矜己德,偶然治差一病(注:‘差’通‘瘥’,治愈。)則昂頭戴面,而有自許之貌,謂天下無雙,此醫人之膏肓也”。做醫生的標準,不可以多言取樂,高聲談笑,說長道短,非議他人,炫耀聲名,誹謗其他醫生而夸耀自己的德行,偶然治愈一病,就趾高氣揚,認為天下無雙,這是為醫者的惡習。
1.2 以“和”為貴的生命觀
繁體字“藥”,由“樂”加“艸”字頭組成,意為選用藥物(本草)來糾正偏盛偏衰的病理現象,使機體功能恢復和諧,猶如美麗和諧的音樂。和諧既包括機體內部各臟腑功能的和諧,還包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環境的和諧。“和”是中醫藥文化的核心和靈魂,體現中醫崇尚和諧的價值取向,概況出診療應遵循的原則。即人與自然相適應,“天人合一”的整體觀,陰陽平和的健康觀,調和致中的診療觀,醫患信和、同道謙和的倫理觀等。疾病診療過程中以“和”為原則,辨證求本,四診合參,標本兼顧。在身心修養上,要澄神守中,涵養品性;對待患者要言語溫和、待患若親,動須禮節、舉乃和柔,勿自妄尊、不可矯飾,誠信篤實、普同一等。“和”在治療原則上的體現最為直接。當臟腑間偶有失和,及時用藥物的偏性糾正臟腑功能的偏勝和偏衰,使機體恢復陰陽平衡、臟腑平衡和機體內外平衡。
1.3 以“精”為榮的價值觀
“精”要求行醫者應博極醫源,精勤不倦,精研醫道、醫術精湛。切不可浮躁偏執,一知半解,淺嘗輒止。只有專心醫道,尋思妙理,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持之以恒,方能臨證不惑,救死扶傷。在藥物制備和炮制方面,一藥一術,皆至誠懇,遵法炮制,不得省人工;剔除偽劣,確保質量。
1.4 以“誠”為本的處事觀
“誠”是學醫者必備的醫學信念和道德修養境界,即醫德要高尚。只有“心地誠謹,術業精能者,庶可奏功”。“誠”體現行醫者人格修養的最高境界。“誠”要求在為人處事、治學診療、著述立說、科學研究等方面,心懷至誠,誠信待人,言行誠謹,誠篤端方;要“膽愈大而心愈小,智愈圓而行愈方”;要力戒誑語妄言、弄虛作假。正如孫思邈在《大醫精誠》中所說:“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含靈之苦。”
中醫藥文化中“誠”,既有助于塑造良好的價值觀、道德觀,又是一種寶貴的精神財富和彌足珍貴的隱性教育資源。如果將中醫藥文化與地方人文景觀和校園人文景觀相結合,將會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藥王孫思邈所著的《千金方》、《大醫精誠》對祖國醫藥學、醫學廉政建設以及武當道教醫藥的貢獻和影響巨大。在武當山的紫霄宮,至今仍供奉著藥王孫思邈的神像。湖北醫藥學院還將《大醫精誠》作為學校醫學廉政建設的典范。在湖北醫藥學院學子會館的右側墻壁上,以線雕石刻的方式展現著一代大醫孫思邈的人物形象和《大醫精誠》的文字,以此鞭策和激勵學醫者應具備高超的醫術和高尚的醫德。
2 以哲學思維來認知生命和疾病的方法論
中醫藥學的哲學思維貫穿于認知生命和疾病的全過程,包括“整體觀念”、“辨證論治”、“審證求因”和“預防為主”,也是中醫藥學理論體系的基本特點,也是中醫藥文化中認知生命現象、診治疾病的思維方式和方法。
2.1 “天人合一”的整體觀
2.1.1 “天人合一”的整體觀 祖國醫學認為,天、地、人是一個有機整體,人對自然環境具有依存性,人的活動則必須遵循自然規律。例如地理環境、四時氣候、晝夜之別,都會對人體的生理、病理產生重要影響,倡導人們應該順應四時晝夜的變化,動靜和宜,衣著適當,飲食調配合理,體現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的原則。即“善言天者,必驗于人;善言古者,必驗于今;善言氣者,必彰于物;善言應者,同天地之造化;善言變者,通神明之理”。應該“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
2.1.2 臟腑功能活動的協調性 構成人體的各臟腑功能之間通過經絡組成有機的整體。在生理上,人體四肢百骸,五臟六腑,借助于經絡系統連接成一個以五臟為中心的密不可分的整體,結構上不可分割,功能上互相協調,生理、病理上相互影響。一臟有病,可以影響他臟,故應治其未病之臟腑,以防止疾病之傳變。如見肝之病,應該認識到肝病最易傳脾,在治肝的同時,當先調補脾。《黃帝內經》中有“病在頭者取之足”的論述。為上病治下、下病治上、左病治右、右病治左、內病治外、表病治里等治法提供了整體治療的依據。
2.1.3 “形神共養”的整體觀 “形神失養”或稱“形神合一”或“形與神俱”的理論來自《黃帝內經》。“神”是指人的思想、思維;“形”即形體。廣義的神是指人體生命活動外在表現的總稱,包括生理性或病理性外露的特征;狹義的神是指精神意識思維活動[2]。形神合一,則身體健康,精力充沛。反之,則容易患病。
2.2 “辨證論治”診療觀
辨證論治是中醫認識疾病和治療疾病的基本原則。辨證是將四診(望、聞、問、切)所收集的各種病情資料進行分析綜合,辨清其病因、病位、病性及邪正之間的關系,以便概括判斷出某種性質的“證候”。論治,是根據辨證的結果,選擇和確定相應的治療原則和治療方法的過程。辨證是決定治療的前提和依據,論治是治療疾病的具體手段和方法,治療效果又是對辨證是否正確的檢驗。因此,辨證和論治,是診治疾病過程中相互關聯、不可分割的兩個環節,是理論和實踐的有機結合,是中醫理、法、方、藥在臨床診療中的具體體現。
2.3 “審證求因”辨證觀
審證求因又稱治病求本,是在診斷過程中辨明導致疾病產生的根本原因,針對病因進行治療。
2.3.1 治病必求本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治病必求于本。”是在治病求本的基本原則指導下,針對疾病本質與現象是否一致而采取的兩種不同的治療原則,故又稱“逆者正治,從者反治”。治病求本的原則,體現在正治與反治、治標與治本兩個方面。
2.3.2 正治與反治 正治是指逆其證候性質而治的一種常用治療方法,又稱逆治。正治適用于病證的觀象與本質一致。如寒證見寒象,熱證見熱象,虛證見虛象,實證見實象,治療時宜分別采取寒者熱之(針對寒證,采用溫熱性質方藥進行治療)、熱者寒之(針對熱證,采用具有寒涼性質方藥治療)、虛者補之(針對虛弱病證,采用具有補虛作用的方藥治療)、實則瀉之(針對邪氣已亢盛而正氣未衰的病證,采用攻逐邪氣的方藥治療)等治法。反治是指順從疾病證候表面假象而治,又稱從治。究其實質,反治仍是在治病求本的原則指導下,針對疾病本質進行的治療。如寒證表面見熱象,熱證表面見寒象,虛證表面見實象,實證表面見虛象。治療時,又分別采用熱因熱用,即針對真寒假熱證,采用溫熱性質的方藥治療具有似熱癥狀的治法;寒因寒用,即針對真熱假寒證,采用寒涼性質的方藥治療具有假寒癥狀的治法;塞因塞用,即以補開塞,是針對因虛而閉塞的真虛假實證,采用補益方藥治療具有閉塞癥狀的治法;通因通用,是指采用具有通利瀉下作用的方藥治療具有通泄假象的病證,適用于熱結旁流,食積泄瀉,瘀血崩漏,濕熱淋證。反治法仍然針對病因進行治療的法則。
2.3.3 標本兼治 治病求本,是尋找出疾病的根本原因,并針對病因進行治療。故《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說:“治病必求于本。”在治療復雜或特殊疾病時,還需分清疾病的標本先后與緩急,分別采取“急則治其標,緩者治其本”的法則。上述哲學的思維方法對培養大學生的創新思維均將產生重要影響。
3 倡導“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預防觀
《黃帝內經》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后藥之,亂已成而后治之,譬猶渴而穿井,斗而鑄錐,不亦晚乎?”強調“上工救其萌芽”,“務在先安未受邪之地”。
3.1 “未病先防”的預防觀
“未病”不等于“無病”。“未病”通常指患病的因素已經存在或即將生病只是尚未出現癥狀。高明的“上工”,能夠預見和分析出“將病”的各方面因素,從而防疾病出現,故將“治未病”中“未病”二字,應理解為“病將作”或“病將至”比較確切。故“上醫”屬于的養生醫學或稱早期進行干預的預防醫學;“下醫”是針對疾病的治療醫學。
“欲求最上之道,莫妙于治其未病”(《證治心傳·證治總綱》)。如《丹溪心法·不治已病治未病》指出:“與其救療于有疾之后,不若攝養于無疾之先。蓋疾成而后藥者,徒勞而已。是故已病而后治,所以為醫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攝生之理。”治“未病”體現在未病先防、既病防變、起居養生和藥食同源等方面。
3.2 “即病防變”的治療觀
“即病防變”是指防止輕病向重病轉變。一方面要辨別主要病因與次要病因,注重先急后緩,防治結合。如“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這是“上工治未病”原文治法的舉例。治病要做到“見微得過,用之不殆”。是指在疾病初起的時候,便能知道病邪之所在,及時進行治療,就不致使病情發展到嚴重或危險的境地。另一方面藥避免因飲食不節、起居無常、情志不遂、勞逸無度、年老體衰等引起的臟腑氣血陰陽失調(不平衡),或內生五邪,或耗傷正氣,從而導致機體處于亞健康狀態,甚至產生疾病。
3.3 “起居有常,藥食同源”的養生觀
3.3.1 起居飲食調攝于未病(清)曹庭棟指出:“以方藥治已病,不若以起居飲食調攝于未病。”(《老老恒言·防疾》)以此強調預防疾病、強健身體、延年益壽之重要,堪稱是養生大智慧。主要表現在起居養生和飲食養生兩方面。食療就是食物療養,通過飲食的調養,以補益精氣,達到健體益壽、防病治病的目的。起居養生,是指人的生活起居應培養良好的習慣,形成規律才有利于健康。
3.3.2 起居有常,不妄作勞 由于人的生命活動具有周期性和節律性,在安排生活起居和作息規律時,盡量使工作、學習、休息、睡眠等起居習慣順應宇宙天體的運動規律,避免或減少持續性的精神緊張以及情緒波動。如果違反了陰陽消長的規律,就會對人體造成傷害。古人觀察認為,日月江河之所以能長久,是因為“天行有常”。人欲長壽,就應“法則大地,象似日月”。以此告誡人們生活起居應有規律,方能“生氣不竭”。《素問·上古天真論》曰:“起居有常,不妄作勞”。又云:“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以竭欲為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勿快其心,逆與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
《素問·生氣通天論》將勞作歇息區分為平旦、日中、日西將暮三時。“起居有常”,“天人合一”,旨在強調生活起居應與天地陰陽保持協調統一。例如,白天陽氣主事之時人要勞作,夜間陰氣用事之時人應休息,提醒人們安排起居作息應順從這些生命節律。只有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和行動方式,方可朝氣蓬勃,生機盎然。
3.3.3 飲食養生,吃出健康 《淮南子·修務訓》有“神農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宋代劉恕《資治通鑒外記》載:“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嘗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由此可見,人類最先對藥物的發現是親身品嘗出來的,在嘗百草尋找食物的過程中,也逐漸發現某些植物對疾病的治療作用,而用之于藥[3]。中醫學在長期的醫療實踐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食療藥療理論體系,通過食療、藥膳調理消除亞健康狀態,恢復正常健康狀態具有潛在優勢。據《素問·生氣通天論》中記載:“毒藥攻邪,五谷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合而服之,以益精氣。”又說:“夫為醫者,當須先洞曉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療不愈,然后命藥。”唐代編撰完成我國第一部食療專著——《食療本草》,對當時的飲食方式作了歸納,敘述了多種食物藥的性味、產地、鑒別和調制方法。食療是指在中醫理論指導下,按照中藥的性味功能不同針對不同的亞健康人群、不同體質類型調制相應的食物。食療的特點是通過人們進食各種膳食,使人體的氣血陰陽、臟腑偏盛偏衰、寒熱虛實偏頗等亞健康狀態得以調理,克服了“良藥苦口”的弊端。藥膳是指以藥配膳,含有藥物、食物、調料。是在食療的基礎上以中醫理論為基礎,將藥物和食物相配合,通過烹調加工而成的一種防病治病、保健強身的特殊食物。讓人們在享受食膳的同時,身體不適的感覺得以消除,“吃出健康”。
中醫藥文化是在長期的醫藥學實踐中建立起來的認知生命與疾病防治理論和方法,具有完整的理論體系。學習傳播中醫藥學文化所蘊含的哲學思想和人文精神,領會天地一體、天人合一、天地人和、和而不同的哲學思想,傳承以人為本、大醫精誠的道德準則,彰顯“重貴人生”的價值取向和文化精髓,凝煉高等醫藥院校固有的文化特色,對于培養和造就高素質的醫藥人才,意義重大。
[1]段逸山.醫古文[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156-162.
[2]印會河.中醫基礎理論[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15,820,826.
[3]李碩,鞠寶兆.《黃帝內經》藥食氣味理論發生學思考[J].遼寧中醫藥大學學報,2009,11(3):14-15.
[4]尤舒徹,王曉鶴.《素問》醫德思想初探[J].山西中醫,1995,11(6):40-41.
[5]馬有度.感悟中醫[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7:148-150.
[6](明)李時珍.本草綱目(上冊)[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15,833,1070.
[7]馬列光.養生之道,貴在持恒[J].環球中醫藥,2008,1(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