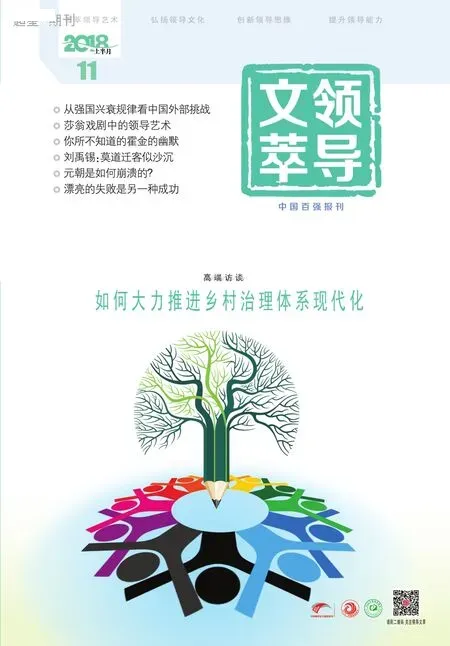政治家的“胡子問題”
宿亮
胡須與人類政治史緊密相連,留不留胡須,已經成為特定歷史時期政治舞臺上的標志性裝飾。
1860年10月,在美國總統選舉前夕,家住紐約州北部的小女孩格雷斯·貝戴爾給林肯寫了一封信。
在信中,11歲的格雷斯寫道:“我有4個哥哥,他們中有兩人已經決定投您的票,另兩人不投給您。如果您讓您的胡子長起來,我會盡力讓不投您票的兩個哥哥改投您的票。所有的女士都喜歡胡子,她們會叫她們的丈夫投票給您,您就能當上總統了。”
林肯馬上給小女孩回信說:“我從沒有留過胡子,如果突然開始留胡子的話,難道你不覺得人們會說那是件愚蠢做作的事嗎?”
不過,不久后,林肯還是下了決心,他對理發師說:“比爾,讓我們給胡子一個長出來的機會吧。”
最后,林肯贏了選舉,成為美國第16任總統。
林肯留胡子的決定,開始了美國政治史上的“胡子時代”,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中,登上總統寶座的都留有胡子,僅有一人例外。如果你放眼全球,便會發現,拿破侖三世、卡爾·馬克思等很多政要或思想家在同一時期也不約而同地留著胡子。
留不留胡須,僅僅是個人喜好問題嗎?至少對于政治家而言,答案是否定的。
隱喻背后
事實上,胡須本身在西方政治語境中包含著多種象征意義,但這些“隱喻”有時也促使一些現代政治家遠離胡須。
在拉丁語中,“胡須”(Bart)一詞是現代英語中“野蠻”(Barbarous)、法語中“野蠻人”(barbare)以及德語中“野蠻人”(Barbaren)的詞根。在古羅馬人眼中,留著長長胡須的人,就是當年拿著斧子在歐洲燒殺搶掠的野蠻人。
在近現代政治中,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獨裁者阿道夫·希特勒的“仁丹胡”頗為有名。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仁丹胡”成為這個瘋狂獨裁者的標志。美國好萊塢著名影星卓別林就是帶著這樣的胡子飾演了希特勒,并用這樣的形象發出“我們希望所有人幸福共存,而非痛苦”的宣誓,諷刺這個制造屠殺、征服的獨裁者。
2000年,奧地利行為藝術家胡普西·克拉馬爾為諷刺當時新成立的右翼政府,在維也納劇院社交圈中蓄起“仁丹胡”,身上掛滿納粹勛章,公開嘲諷政府的不民主政策。
除希特勒的“仁丹胡”之外,八字胡會讓人聯想到好大喜功的獨裁者拿破侖三世;而在西方社會,濃重的大胡子還會讓人聯想到前蘇聯領導人斯大林。所以,拒絕蓄須已成西方從政者牢記的“政治正確”。
政治時尚
除了胡子所伴隨的隱喻之外,現在的很多政治家留不留胡須、留什么樣的胡須,有時也是一個時尚問題。而在時尚被傳媒蜂擁的時代,政治家的胡須自然就成了一種政治時尚。
目前當政的這一代西方國家領導人,有著共同的代際特征。當奧巴馬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時候,羅納德·里根是美國的政治偶像。里根從演藝時期到總統任內,都以無須的形象出現,顯得精神矍鑠、有活力。
而當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從牛津大學畢業進入政府服務時,他的“老板”約翰·梅杰那副無須、大邊框眼鏡的專業形象也廣為英國人所接受。
有人說,放棄蓄須是政治家們在新傳媒時代“進化”的產物。美國作家威廉·曼徹斯特在《光榮與夢想》中描述1960年美國首次總統選舉電視辯論的場景時分析,約翰·肯尼迪年輕小生的形象完勝老邁虛弱的理查德·尼克松,正是從那時開始,政治家的胡須、頭發以及穿著色調等成為競選團隊的頭等大事之一。
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年輕時曾留著一撮山羊胡,參加競選時他把胡子刮掉,顯示出“干凈”的笑容,被認為“征服了選民”。而美國前副總統艾伯特·戈爾2001年在總統選舉中敗給小布什后,留起了一茬短短的絡腮胡,被《紐約時報》描述成“通緝在逃的會計師”。這一正一反的例子充分說明在當代西方政治中,胡須發揮著“翻云覆雨”的作用。
等待“輪回”
為什么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政壇的“胡子”風潮,之后就一蹶不振了?實際上,政治家對于胡子的態度不止經歷過一次轉變。
幾千年前,尼羅河畔的埃及法老就用山羊胡來昭示自己的權威地位。在古埃及,只有法老才能夠蓄須,而且法老必須蓄須,才能體現出尊嚴和威懾力。那些臉上胡須不夠的法老,只能通過粘貼假胡須來確保權威形象,甚至幾位女法老也在臉上裝飾假胡須,象征神和統治者。
可在中世紀的歐洲,羅馬教廷卻明確禁止普通僧侶留胡須。原因是在當時的歐洲,男子只有長出胡須才算成年,才能接觸女人。久而久之,胡須成了性啟蒙、開放的象征,與教會所奉行的禁欲主義背道而馳。
1699年,俄國沙皇彼得一世從西歐“游學”回國,把胡子看成是俄羅斯保守觀念的標志,為與西方現代文明“接軌”,下令征收“胡須稅”,對拒絕剃掉傳統的哥薩克大胡子的俄羅斯人進行高額征稅,直接導致一部分堅持舊禮儀的宗教人士從國教中分離出去;無獨有偶,“土耳其之父”凱末爾在建立宗教與世俗分立的現代政府過程中,同樣禁止公職人員和大學生蓄起象征宗教的絡腮胡。
從這個意義上講,胡須與人類政治史緊密相連,留不留胡須已經成為特定歷史時期政治舞臺上的標志性裝飾。
(摘自《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