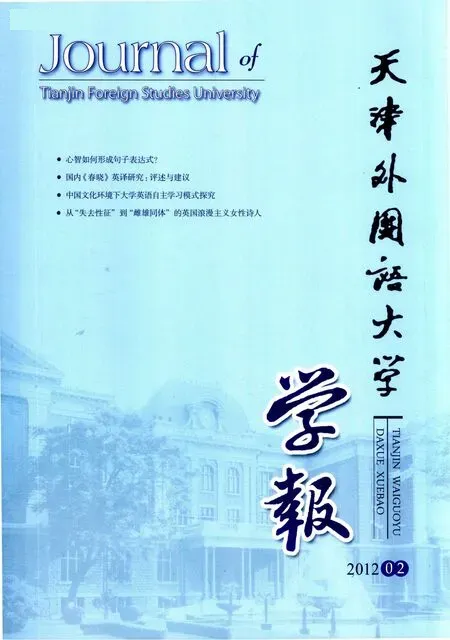從“失去性征”到“雌雄同體”的英國浪漫主義女性詩人
王 欣
(上海外國語大學 英語學院,上海 200083)
一、引言
英國浪漫主義女性詩歌的再解讀與再接受是當代西方新浪漫主義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發展的產物,也是解構主義思潮影響下對文學“經典”問題重新審視的結果。實際上,很多浪漫主義女性詩人,在詩藝上都可以稱得上是男性詩人的前輩。夏洛特·史密斯(Charlotte Smith)引領了英國浪漫主義時代的十四行詩創作,影響了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堪稱名副其實的英國浪漫主義先驅。瑪麗 · 羅賓森 (Mary Robinson)和安娜 ·芭波德(Anna Barbauld)不但是卓有成就的詩人,還身兼文學編輯之職,在當時的文學圈里頗有名氣。弗雷西亞·海曼斯(Felicia Hemans)和利蒂希婭 ·蘭登(L.E.Landon)是19世紀二三十年代最受歡迎的女詩人,她們在濟慈、雪萊和拜倫去世后活躍在浪漫主義詩壇。應該說正是女性詩人開啟了浪漫主義時代,又是女性詩人圓滿地結束了浪漫主義時代,實現了從浪漫主義詩歌到維多利亞時代文學創作的銜接與過渡。
這些女性詩人在浪漫主義時代取得了卓著的成就,當時的評論界對此既有褒揚和肯定,也有頗帶酸味的諷刺和挖苦,將她們稱為“失去性征的女性”。而這些女性之所以失去女性性征,不過是因為她們有了獨立的思想,涉足了男權主導的文學創作領域。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些女性詩人在文學創作中,是否真的有意識地融入一些男性特征的元素呢?她們在創作的時候是否處于柯勒律治所說的“半雌半雄”的狀態呢?
二、“失去性征”的英國浪漫主義女性詩人
“失去性征的女性”是18世紀末男性評論家對于當時女性作家的諷刺之詞,1797年由馬賽厄斯(T.J.Mathias)在其《文學的追求:一首對話體的諷刺詩》(The Pursuits of Literature: A Satirical Poem in Dialogue)的前言中首次使用。“失去性征的女性”指的是不具備柔美、溫順、矜持等女性特質的女性,那么,這些女性文人為什么會被稱為“失去性征的女性”呢?
18世紀中后期的西方社會,處于傳統向現代更替的交接階段,政治上革命頻發,思想上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的啟蒙主義引領了整個意識形態,文學創作上求新求變、回歸自然的創作理念開始滋生發展。可以說,18世紀末期正處于歷史的某種臨界點,新的事物通過各種變革而對舊的事物進行沖擊、實現超越,這個時期人們的思想意識也在經歷一場裂變,男女兩性之間的社會差異開始被關注、被強調。
進步的啟蒙思想家盧梭對當時社會不平等現象的深刻分析與揭露,對于當時人們,尤其是女性的覺醒有著一定的啟蒙作用,但其對女性的態度依然是傳統的、男權思想的。其教育學名著《愛彌兒:論教育》(1762)中“歸于自然”的教育思想帶有新興資產階級的先進性,但作者在第五卷談到女性教育問題時,卻流露出了男權的思想,他說:“我們確切知道的唯一的一件事情是:男人和女人共同的地方在于他們都具有人類的特點,他們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們的性……所有這些相同和相異的地方,對人的精神道德是有影響的……每一種性別的人在按照他或她特有的方向奔赴大自然的目的地時,要是同另一種性別的人再相像一點的話,那反而不能像現在這樣完善了!”(盧梭,2009:579)而對于男女性別之間究竟有什么差異,盧梭是這樣闡述的:“一個是積極主動和身強力壯的,而另一個則是消極被動和身體柔弱的……女人是特地為了使男人感到喜悅而生成這個樣子的。”(同上: 580)盧梭這樣的論述,無疑暗示出女性由于其性別的差異,無論在體格力量上還是在精神道德上都弱于男性,而且這種男女性別的優劣是自然的法令,是合乎自然規律的,這就有意無意地維護了父權社會的男性權威。
盧梭在性別差異的論調上受到了以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為代表的女性文人、女性思想家的抨擊,促使她們開始對女性的主體性進行深入思考,引領了女性意識的覺醒。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其《女性權利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792)中就批判了盧梭的女性教育觀,強烈呼吁對女性的教育進行改革。針對盧梭的性別差異論,當時的女歷史學家格雷厄姆(Catharine Macaulay Graham)也反駁說,不存在實質上的性別差異,所謂的差異,也即女性在身體與智力上都弱于男性的差異,實際上都是教育的結果。
在盧梭的《愛彌兒:論教育》之后,對女性行為規范進行規誡的書主要是詹姆斯·福代斯(James Fordyce)的《對年輕女性的勸誡》(Sermons to Young Women)(1765)以及約翰·格雷戈里(John Gregory)的《一位父親留給其女兒的遺產》(A Father’s Legacy to his Daughters)(1774),這兩本書都代表了父權社會中男性對女性的要求與束縛,具有強烈的男權色彩。福代斯(Fordyce,2008:90)說:“帶有男人味的女性在本質上一定是不和藹的動物,我承認每當我看到性別被混淆的時候我都極度震驚。”這里福代斯將不合乎當時女性行為規范、侵犯了男性行為范疇的女性稱為“帶有男人味的女性”,也就是沒有女人味、不具備女性美的女性,毫不掩飾地對其進行抨擊和挖苦。格雷戈里(Gregory,2008: 92)對女性美的總結則是“女性所具有的美主要是謙虛的保守,是含蓄的優雅,要避開公眾的眼睛,即使是在崇敬的注視中也應感到不安”。
為什么這些男性突然對女性的行為規范如此敏感呢?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在這段時期,教育水平的提高、流通圖書館的出現以及出版業的蓬勃發展,促使女性作家作品風起云涌。她們“作為小說家、詩人及社會評論員,開始在數量上、作品的銷量上、文學聲譽上與男性競爭匹敵;僅僅在詩歌領域,大約有900名女性被列入到了杰克遜 (J.R.de J.Jackson)最近的研究書目《女性創作的浪漫主義詩歌》之中”(Abrams,2000:4-5)。她們沒有“避開公眾的眼睛”,在文學市場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這些才華橫溢的女性詩人卻受到了男權社會的輿論抨擊,“當時的雜志抨擊女性作家和知識分子為‘失去性征的女性’(unsexed females)或 ‘裝作有學問的女人’(bluestockings)”(Bainbridge,2008:89),女性涉足一向被認為是男性領域的文學自然會招來男性“正當防衛”式的抨擊。這些女性由于撰寫詩歌、發表詩歌而進入了公眾的視野,由此失去了女性該有的優良品質。其二,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等人的影響下,女性詩人在作品中表達女性的呼聲,積極參與為女性爭取權益的運動。正如戴維·辛普森(Simpson,2009: 406)所總結的那樣,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性權力辯護》“對于理解同時代的諸如史密斯、羅賓森……等許多女性作家的小說和詩歌,可謂是一個批評準繩”。史密斯政治觀點激進,通常被認為是18世紀90年代與沃斯通克拉夫特同道的女性雅各賓派作家(Vermeule,2009:29)。羅賓森在1799年發表其《就智力劣等問題的不公平性致英格蘭女性書》(A Letter to the Women of England on the Injustice of Mental Subordination)表達了她的女性觀,勇敢而又直接地對男權社會的傳統發出挑戰和抗議。對此,艾德里安娜·克勒瓊(Craciun,2009: 382)總結道:“羅賓森努力在其作品中將政治激進性、理性、情感和戲劇風格融合在一起,這對我們理解浪漫主義文學和政治傳統以及理解早期的女性主義都有著獨特的價值。”可以說,女性詩人作品中所體現出的女性主義萌芽,使得更多的女性開始質疑自己的性別身份與社會角色,挑戰并動搖了父權文化。
理查德·波爾威爾(Richard Polwhele)在1798年撰詩攻擊女性文人,題名即為《失去性征的女性》(The Unsex’d Females)。作者在詩中公然提到了大量同時代女性文人的名字,而其 “對安娜·芭波德、瑪麗·羅賓森及夏洛特·史密斯的蔑視性評論,則源于她們成功表現為沃斯通克拉夫特式的理想女性:所謂理想女性就是要用自己的才智去挑戰不公平的社會規范 ”(Pascoe,2004: 212)。對此,帕斯科 (Judith Pascoe)總結說:“在波爾威爾看來,沃斯通克拉夫特及她的追隨者們是沒有性別的,或者說是由于她們激進的情感而失去了令人稱道的、女性必需的性別特質。”(ibid.: 212)而這些女性之所以失去女性性征,不過是因為她們涉足了男權主導的文學創作領域,并通過文學創作來表達女性的呼聲。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些女性作家們在文學創作中,是否真的有意識地融入一些男性特征的元素呢?如果真是這樣,就可以升華為“雌雄同體”的創作論了。
三、從“失去性征的女性”到“雌雄同體”
如同新批評的課堂一樣,加拿大達爾豪斯大學的教授朱莉婭·瑞特(Julia M.Wright)也在文學課堂上做了有趣的實驗,她將詩歌的作者隱去,只讓學生專注于詩歌文本自身。朱莉婭在課堂上分別將雪萊的《幽靈騎手》(The Spectral Horseman)、羅賓森的《1795年的1月》(January,1795)及布萊克的《歌》(Song)這三首詩歌隱去作者,告訴學生一首詩的作者來自下層百姓,一首詩的作者是貴族,而另一首詩的作者則是一位女性。有趣的是,幾乎所有的學生都會給出同樣的答案:“政治詩是貴族寫的,哥特風格的詩是下層詩人所作,而唯一的女性所寫的則是抒情詩,一首他們認為是以女性的口吻所寫的抒情詩。”(Wright,2007:271) 而實際的情況是,貴族雪萊寫了哥特風格的《幽靈騎手》,來自社會下層的布萊克寫的是抒情詩,而唯一的女性羅賓森寫的則是政治歌謠《1795年的1月》。這個實例說明,好的詩歌應該是超越性別、超越階級的,文本與作者之間并沒有必然的、唯一的、固定的聯系,詩人通過自己非凡的想象力和高于常人的感悟力,男性詩人可以寫出具有女性特質的詩歌,女性詩人也可以在詩歌中暢談政治。因此,很難說女性文學是截然不同于男性文學的。實際上,正如浪漫主義詩人、文論家柯勒律治所認為的那樣,偉大作家的大腦應該是“半雌半雄”的,偉大的詩人在寫作時并不總是因循自己的性別感悟,而是有所兼顧,著力表現作品的完整性與統一性。這體現出浪漫主義詩學的有機整體論思想,也被視作當代女性主義批評理論中“雌雄同體”創作論的前身。
“雌雄同體”(androgyny)源于希臘語,指的是兼具男性和女性特點的人,在20世紀女性主義批評理論體系中,“雌雄同體”被弗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闡發為“藝術創作的一種最佳狀態,而在這種狀態下創作的作品也是最好的”(沈建青,2007: 205)。她說:“如果一個人是男性,他頭腦中那部分女性因素必定仍然在發揮作用;如果是個女性,她也必須和頭腦中的男性因素溝通對話”(伍爾芙,2001: 578),這是一種心理狀態,正如潘健所總結的那樣,“伍爾夫的‘雌雄同體’不是生物學上的概念,而是指某種精神狀態:‘大腦統一’和‘自然的融合’,它不是簡單的一元狀態,而是由異質構成的‘整體’”(潘建,2008:102)。伍爾芙的這種觀點承襲了柯勒律治的“半雌半雄”論和有機整體論,而之前她所提出的“一個作家是沒有性別的”之說(伍爾芙,2001:195),也與濟慈的“消極感受力”頗為相似,都談及作家的創作心理,只不過前者是以男性與女性的關系為核心,而后者是以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系為核心。因此,從內因來看,無論是基于浪漫主義詩學的創作論,還是基于女性主義批評理論的創作論,英國浪漫主義女性詩人就應該是“失去性征的”,因為只有這樣,她們才能處于最佳的藝術創作狀態,也即處于“沒有性別的”、“雌雄同體”的創作狀態。
而英國浪漫主義女性詩人“雌雄同體”創作論的形成至少還有兩方面的外因。一方面,許多女性詩人進行文學創作的初衷是賺錢謀生,這就要求她們不僅在創作中表達女性的呼聲,還要兼顧主流男權文化的接受。史密斯15歲就被迫出嫁,夫家雖家境殷實,但丈夫是個游手好閑的敗家子,使得史密斯始終掙扎在貧困的邊緣。為了撫育十個孩子,史密斯不得不寫作賺錢。羅賓森16歲結婚,婚后不久便發現丈夫深陷債務糾紛,為了替夫還債羅賓森不得不在陪伴丈夫的獄中開始寫作,并且不久開始登臺演出舞臺劇賺錢。海曼斯和蘭登是19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流行女性詩人,寫作已然成為一種職業,她們的詩作要迎合大眾的欣賞品位。在這些情況下,女性詩人在創作中就必須要避棄過分女性特質的東西,而將自己的女性視野放到一個更為廣闊的社會視野之中,這就在客觀上驅使女性詩人在創作中要“雌雄同體”。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女性詩人可以接觸到當時先進的啟蒙思想,也能夠認真思考女性自身的社會角色與主體地位。女性是社會不公平的多重受害者,她們在政治上沒有話語權,在情感上被動、順從,在經濟上依賴男性,是男性的附庸。對于這樣的生存現狀,女性文人自然通過創作來表達訴求,用 “自己的才智去挑戰不公平的社會規范”:文學創作上的成功使她們獲得了一定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使她們因而能夠表達也勇于表達自己的見解。反過來,她們視野的開闊與觀點的進步又通過作品表達出來,使她們的聲音能夠成為公開的、公共的聲音。關注政治、渴求平等使她們站在了一定的高度上,使她們擁有了男性權威的氣勢,在作品中便也反映出這種“雌雄同體”式的創作來。
在浪漫主義時期,由于啟蒙主義思想的影響,不公平的社會狀況或者說社會性的差異,在女性文人那里突出表現為性別差異,她們通過創作中“雌雄同體”的自我否定與自我肯定,表達出一定的女性主義意識以及消除社會不公的美好愿望,同時也體現出詩歌美學意義上的完整性以及對狹隘視野的超越。
四、浪漫主義女性詩人的“雌雄同體”創作
在浪漫主義時代,男性詩人的繆斯多為女性,好比華茲華斯的妹妹多蘿西,好比《忽必烈汗》中阿比西尼亞的少女,使其作品中自然帶有女性特質的東西。多考 (Dokou,1997: 3)在其研究中就肯定了當代女性主義者的論斷,也認為“將女性特質的因素移入男性意識之中實際上是浪漫主義的根深蒂固的傳統主題”。而對于浪漫主義女性詩人來講,也同樣有男性特質的因素移入女性意識之中,女性詩歌作品的“雌雄同體”也可以理解為浪漫主義女性詩歌的一個創作原則、一個傳統主題。
海曼斯是一位多產的女性詩人,也擁有很大的讀者群,她為《愛丁堡月刊》(EdinburghMonthly Magazine)和《新月刊雜志》(New Monthly Magazine)等有影響的雜志撰稿,享有很高的聲譽,“但是,對于究竟該如何對待這樣一位天才的女性詩人,評論家們頗感尷尬。《評論月刊》(Monthly Review)將她對于某些場景的描繪稱為‘大師級的’(masterly),但又在腳注中質疑說‘我們可以將這個詞應用到一位女性身上嗎?’”(Kennedy,1992:259)這是當時評論界對海曼斯的肯定,但又似乎在百般挑剔,原因更多的是由其女性的性別身份所引起的。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樣的評論也說明了海曼斯創作的“雌雄同體”,單純從詩歌文本來看,并沒有突出的女性特質的痕跡,而是體現了一種更為開闊的、完整的表達視野,而也正是這種視野成就了海曼斯詩歌創作生涯的成功。
《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1826)是海曼斯非常著名的一首詩歌,描繪的是1798年發生在埃及的英法之間的尼羅河戰役。卡薩布蘭卡是一位法國艦隊司令的兒子,年僅13歲,在尼羅河戰役中他一直堅守在船上,在堅定與忠誠中與船只同歸于盡。海曼斯作為一個愛國的女性詩人,她居然在謳歌法軍將領的孩子,這是一種悖論式的表述。對這首詩的解讀有著不同的觀點,有人認為,這是對敵軍男孩的熱情贊美,還有人認為,謳歌與贊美只是表面現象,其真實意圖是對卡薩布蘭卡的譴責和嘲諷,因為他的忠誠實則是一種愚鈍、無知的順從。
在這首詩歌中,詩人將歷史上的一次戰役與一個小男孩聯系在一起,通過一個天真的孩子來描寫這次戰役,更透過這次戰役來描寫戰爭。卡薩布蘭卡孤身堅守在炮火紛飛的戰船中,他身體里流的是“英雄的血液”(heroic blood),盡管有著一副“孩子的身形”(child-like form),但卻表現出凜然的傲氣,他一遍遍喊著他的父親,追問“我的任務是否已完成?”(If yet my task is done?)“我是否可以走開!”(If I may yet be gone!)第一次追問時還是問句,在沒有得到父親的回答后,第二次追問已然變成了嘆句,以嘆句來表達自己的吶喊。這表現出了孩子的茫然與惶然,這時的他已經陷入到了“勇敢的絕望”(brave despair)之中。在這里,詩人用一種悖論式的語言暗示出了對男孩勇敢行為的批判,這種勇敢注定是絕望的,是魯莽的,是天真的。在詩歌的結尾部分詩人寫到:
忽來一陣雷聲響——
那男孩——哦!他身在何處?
試問狂風在遠方
紛飛碎片海面露!——
男孩最終為自己的勇敢和忠誠付出了代價,可憐他也在炮火聲中灰飛煙滅。在最后兩句詩行中詩人寫到:
只是消失彼處的最珍之物
是那年輕的忠效之心!
忠誠是一種寶貴的品質,但若忠誠失去了方向,是一種孩子所有的天真的忠誠,它就會成為毀滅的導索。詩人一次鞭撻戰爭的殘酷,戰爭毀滅的不僅是年輕的生命,還有一顆忠效之心。
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海曼斯作為一名女性詩人,能夠以這樣的氣魄、這樣的視野來描寫戰爭,已然完全超越了父權社會對女性的界定。實際上,“在海曼斯作品眾多的主題中,愛國主義和軍事行動頻繁再現”(Abrams,2000: 812)。不僅如此,她的許多詩歌的主題都是歐洲文化與歷史,如《藝術作品的意式回歸》(The Restoration of the Works of Art to Italy)(1816)、《現代希臘》(Modern Greece)(1817)以及《故事與歷史場景》(Tales and Historic Scenes)(1819)。1826 年,海曼斯寫出了21首詩歌的集子《多國敘事詩》(Lays of Many Lands),對各國的事件進行評論,這些都說明了海曼斯“雌雄同體”式的創作主題。
從“雌雄同體”創作的角度來看,芭波德也得到了當時評論界的肯定。《威斯敏斯特雜志》在1776年的一篇文章對芭波德的詩歌贊譽有加,但這種贊美是基于男權審美觀的,芭波德的詩歌之所以好是因為具有“男性的力量”:“實際上,她詩歌中除了表達之優雅外,毫無女性特質的東西,而表明這些詩歌是出自女性之筆的標志也就是優雅的表達了。”(Pascoe,2004: 216)這說明芭波德的詩歌創作具有男性特質,其偉大之處正在于恰當地結合了女性的優雅和“男性的力量”,是一種“雌雄同體”的表達。此外,在芭波德詩歌中還有一個較為常見的主題,就是 “可見的”(visible)和“不可見的”(invisible)之間的對照,“可見的”只是表象,“不可見的”才是本質。人們應該透過現象看本質,這和其詩歌創作也不謀而合,她發表詩歌作品或匿名、或以簡稱、或以“一位女士”(A Lady)自稱,這也是在呼吁人們透過這樣的現象去挖掘詩人的真實身份,而這種情況下再現的詩人之女性身份,無疑有著更為強烈的沖擊力和震撼力。
應該說,“雌雄同體”這一概念本身就表達了一種矛盾的統一,體現了浪漫主義的辯證觀、有機論。在浪漫主義詩人藝術創作的層面,“雌雄同體”是一種創作心理,在中性的狀態下能夠創作出偉大的作品,但“雌雄同體”不僅僅體現出有機的、融合的、偉大的創作思想,而且不同的性別主體會體現出不同的主體意識與主體認同。男性詩人的“雌雄同體”更多反映出的是情感主義意識、是一種自我否定。比如,多考(Dokou,1997:10)在分析拜倫的 《唐璜》時認為, 《唐璜》所體現的“雌雄同體”并不是對男性英雄主義的歌詠,而是對男性權威的一種批判,也即“雌雄同體的聲音在挑戰父權文化時與女性的聲音同樣有效”。男性權威是當時現實社會的真實寫照,敏感的男性詩人們也深切感受到了這一點,他們對社會的失望、無奈和抗議似乎通過這個可以抒發表達出來。
相比之下,女性詩人的“雌雄同體”更多反映出的是女性主義意識、是一種自我肯定,這在女性詩人有關薩福(Sappho)之主題的詩歌創作中有所體現。古希臘女詩人薩福可謂是“失去性征的”英國浪漫主義女性詩人心中的先驅,是她們的繆斯女神,但這位繆斯復雜的性別認同傳說使其在個人形象上更偏向于中性的“雌雄同體”:薩福身邊圍擁著眾多年輕美麗的女子,她們崇拜薩福、奉薩福為師,薩福也毫不掩飾地表露對這些女子的愛慕之情、同性之戀。甚至在薩福的詩歌作品中,也有似乎從男性心理視角的對女性之美的觀察與歌詠,這些都賦予了薩福以 “雌雄同體”的意味。浪漫主義女性詩人們在作品中或直接、或間接地提及薩福,有的詩歌直接以薩福命名:海曼斯的《薩福的最后一歌》(The Last Song of Sappho);蘭登的《薩福》(Sappho)和《薩福之歌》(Sappho’s Song)、羅賓森的《薩福與法翁》(Sappho and Phaon)等等。薩福作為一名女性詩人,表達了一種女性的欲望,這種女性的欲望又帶有陽剛之氣的霸道,正如文森特(Vincent,2004:54)所總結的那樣,“海曼斯、蘭登……的薩福詩歌有意識地重構了一個‘自身情欲能自我滿足的’薩福”,對女性欲望的直接表達是女性意識的體現。薩福身邊的眾多少女以及薩福詩歌中若隱若現的性愛描繪,暗示出一種女性欲望的自足,這是女性獨立于男性、解放于男性的體現。英國浪漫主義女性詩人希望通過薩福來獲得“對她們自身倫理道德的認同”,也是通過在作品中對薩福的詮釋,女性詩人“建構了一種同時具有自我否定和自我肯定意味的主體身份”(ibid.: xix)。 通過這樣一種建構,浪漫主義女性詩人筆下的薩福實際上成了她們的代言人,不僅傳達出強烈的女性意識,同時也是“雌雄同體”的化身,是女性詩人“雌雄同體”式創作的繆斯。
五、結語
英國浪漫主義女性詩人通過“雌雄同體”那既矛盾又統一的自我肯定與自我否定,反映了時代精神、抒發了女性意識,既有對不平現實的否定與批判,也有對美好世界的追求與向往。她們從“失去性征的女性”到“雌雄同體”,實現了詩歌創作的升華和文學生涯的成功,也成就了浪漫主義女性詩歌在當代的再解讀與再接受。
[1]Abrams,M.H.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C].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2000.
[2]Bainbridge,S.Romanticism: A Sourcebook[C].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8.
[3]Craciun,A.Mary Robinson[A].In D.S.Kastan(ed.)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British Literature[C].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9.
[4]Dokou,C.Androgyny’s Challenge to theLaw of the Father: Don Juan as Epic in Reverse [J].Mosaic,1997,(30): 3.
[5]Fordyce,J.Sermons to Young Women [A].In S.Bainbridge(ed.)Romanticism: A Sourcebook[C].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8.
[6]Gregory,J.A Father’s Legacy to His Daughters [A].In S.Bainbridge(ed.)Romanticism: A Sourcebook[C].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8.
[7]Kennedy,D.Hemans,Felicia[A].In L.Dabundo(ed.)Encyclopedia of Romanticism: Culture in Britain,1780s-1830s[C].London: Routledge,1992.
[8]Pascoe,J.Unsex’d Females: Barbauld,Robinson,and Smith [A].In T.Keymer & J.Mee(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1740-1830[C].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9]Simpson,D.Romanticism[A].In D.S.Kastan (ed.)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British Literature[C].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9.
[10]Vermeule,B.Charlotte Smith[A].In D.S.Kastan(ed.)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British Literature[C].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9.
[11]Vincent,P.H.The Romantic Poetess: European Culture,Politics,and Gender,1820-1840[M].Hanover: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2004.
[12]Wright,J.M.Baillie and Blake: At the Intersection of Allegory and Drama[A].In H.P.Bruder (ed.)Women Reading William Blake[C].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7.
[13]陳璟霞.勞倫斯的女性意識和雙性主題[J].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2005,(2): 76-80.
[14]弗吉尼亞·伍爾芙.伍爾芙隨筆全集[M].張學軍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15]盧梭.愛彌兒:論教育[M].李平漚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16]潘建.弗吉尼亞·伍爾夫的“雌雄同體”觀與文學創作[J].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2): 96-102.
[17]沈建青.雙性同體[A].柏棣.西方女性主義文學理論[C].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18]張智義.生態女性主義視野中的華氏兄妹創作[J].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2009,(3): 5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