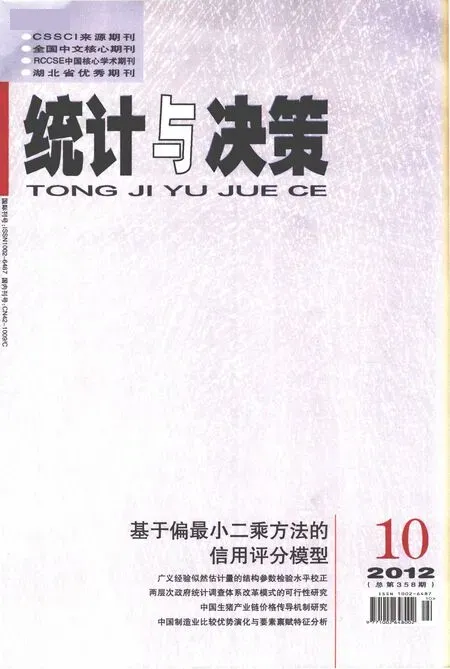貧困的多維測度研究述評
劉澤琴
(中央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 統(tǒng)計(jì)學(xué)院,北京100081)
0 引言
2010年6月,聯(lián)合國發(fā)展計(jì)劃署(UNDP)發(fā)布了名為《千年發(fā)展目標(biāo)(MDG)如何實(shí)現(xiàn)?》的報(bào)告,該報(bào)告?zhèn)鬟f出的主要信息之一便是,有必要對那些令人們陷入貧困的剝奪進(jìn)行整體考量,因?yàn)檫@些剝奪是彼此密切聯(lián)系著的,“一個(gè)目標(biāo)的加速往往促使其他指標(biāo)也加速……考慮到這種協(xié)同作用和乘數(shù)效應(yīng),所有目標(biāo)均應(yīng)得到同等的重視,且必須同時(shí)實(shí)現(xiàn)”。藉此筆者認(rèn)為,對于研究貧困、福利以及平等等領(lǐng)域的學(xué)者尤其是國內(nèi)研究者而言,該報(bào)告在三個(gè)方面給予我們有益的啟示:(1)研究視角的轉(zhuǎn)變,即通過“可行能力的剝奪”體現(xiàn)人們生活中重要功能性活動(dòng)的不完善情況;(2)研究方法的更新,即以綜合指數(shù)或其他類似性質(zhì)的數(shù)學(xué)模型測算貧困程度或福利水平;(3)研究數(shù)據(jù)(指標(biāo))的擴(kuò)充,即將貨幣收入之外更廣泛的指標(biāo)納入考察范圍。以下分別從這三個(gè)方面對近年來學(xué)界的研究成果作一簡要綜述。
1 “可行能力”概念的引入與詮釋
1998年諾貝爾經(jīng)濟(jì)學(xué)獎(jiǎng)獲得者Sen的主要學(xué)術(shù)成就在于他對人類發(fā)展的概念與測量方法領(lǐng)域的卓越貢獻(xiàn)。其實(shí)在他之前,人們對貧困和福利以及平等等課題的研究由來已久,其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以怎樣的平等觀作為考量的標(biāo)準(zhǔn),早期比較盛行的觀點(diǎn)主要有三種:(1)功利主義的平等;(2)完全效用的平等;(3)羅爾斯主義的平等。功利主義平等觀是由功利主義優(yōu)度概念導(dǎo)出的平等觀,該概念用于討論分配問題。功利主義的目標(biāo)是將效用總合最大化,而不管如何分配,這要求每個(gè)人的邊際效用相等。……但是,這就意外地成為了平均主義:只是“總和”這條狗身后恰巧搖著一條“邊際”的尾巴而已。更重要的是,該假設(shè)是常常被違反的,因?yàn)槿伺c人之間存在著顯著差異。完全效用平等觀認(rèn)為,某種情況的優(yōu)度可以完全按照該情況下效用的優(yōu)度來判定。與功利主義的觀點(diǎn)相比,這一觀點(diǎn)的要求不那么苛刻——不額外要求效用優(yōu)度必須按照總和來判定。在這個(gè)意義上來說,功利主義是福利主義的一個(gè)特例。羅爾斯的“正義二原則”用他稱為“首要的社會(huì)優(yōu)度”來描述平等的特征。他要求效率與平等,以基本物質(zhì)指數(shù)來衡量優(yōu)勢大小。實(shí)際上,可以認(rèn)為在羅爾斯主義的框架內(nèi)存在著一種“拜物主義”特征。羅爾斯將基本物質(zhì)看作優(yōu)勢的化身,而不是將優(yōu)勢看作人與物之間的一種關(guān)系。效用主義,或者——更一般地說——福利主義沒有這種拜物主義,因?yàn)樾в檬菍θ撕臀镏g關(guān)系的一種反映。
在此背景之下,Sen首創(chuàng)了“可行能力”的概念。藉由道德哲學(xué)領(lǐng)域的問題——“什么樣的平等”——Sen論述了在之前的研究中廣受關(guān)注的三種平等觀都存在嚴(yán)重的局限性,盡管它們在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缺陷,但是無法通過將三者相結(jié)合的方式構(gòu)造出一個(gè)完備的理論。之后他提出了另一個(gè)平等構(gòu)想,即“基本可行能力”的平等,并指出“在我看來,這種構(gòu)想值得引起更多的關(guān)注,我會(huì)代為鼓與呼”。他認(rèn)為基本可行能力是“一個(gè)人有能力去做某些基本的事情。行動(dòng)能力是其中一部分,但是還可以考慮其他的,比如滿足營養(yǎng)需求的能力,有穿衣和居住的必要資金,參與社區(qū)的社會(huì)生活的能力”(Sen,1983)。
Sen認(rèn)為,可行能力不僅顯然地區(qū)別于實(shí)現(xiàn)該能力的具體物品及其使用價(jià)值,而且有別于使用該物品產(chǎn)生的效用,又不同于可行能力的實(shí)現(xiàn)所帶來的心理滿足。他論述道:擁有自行車——或者其他具有某種使用價(jià)值的東西——可以創(chuàng)造改善生活狀況的基本條件,但是它本身并不是生活水平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雖然效用反映了自行車的使用價(jià)值,但是效用并不強(qiáng)調(diào)使用價(jià)值本身,而是強(qiáng)調(diào)這種使用價(jià)值的心理反應(yīng)。……生活狀況的比較不是效用的比較。所以構(gòu)成生活水平的不是貨物(物品),也不是它的特征,而是利用這個(gè)物品或者那些特征達(dá)成某事的能力。按照這種觀點(diǎn),反映生活水平的是這種能力,而不是表現(xiàn)為幸福感的對這種能力的心理反應(yīng)。
可行能力方法將個(gè)體福利描述為某個(gè)人實(shí)際可以做什么或可以成為什么(見 Sen,1987,1992,1993,1994,1997)。以這種觀點(diǎn)來看,生活可以看作是一系列相互聯(lián)系的功能性活動(dòng),而對福利的概括評價(jià)必須表現(xiàn)為對這些組成要素的評價(jià)的形式。與功能性活動(dòng)這一概念緊密相連的是功能性活動(dòng)的可行能力,即某人可以獲得的“做”與“成為”的不同組合。因此,可行能力集合是一個(gè)功能性活動(dòng)的向量集,它反映了一個(gè)人選擇如何生活的自由。所以,如果所獲得的功能構(gòu)成了一個(gè)人的福利,那么可行能力反映了一個(gè)人擁有福利的實(shí)際機(jī)會(huì),其中也包括選擇已選組合之外的其他組合的自由。
在開創(chuàng)性的工作之后,Sen進(jìn)而在后續(xù)的著作中大大深化了研究者對標(biāo)準(zhǔn)模型的理解,在這個(gè)范疇內(nèi)深入討論了人類福利、生活質(zhì)量、發(fā)展以及貧困(見Sen,1983,1984,1985,1987,1993,1996,2000)。可行能力方法被公認(rèn)為福利分析中比較完備且綜合性強(qiáng)的方法之一(Martinetti,2000)。
可行能力方法提出的理念是全新的,其中結(jié)合了經(jīng)濟(jì)學(xué)和哲學(xué)的工具,在重大經(jīng)濟(jì)學(xué)問題的討論中重建了倫理層面。但是在肯定這些積極意義的同時(shí),必須注意到,可行能力方法的實(shí)際應(yīng)用仍面臨諸多現(xiàn)實(shí)問題。正如Martinetti所評論的:如果拿來與更標(biāo)準(zhǔn)化的福利方法(即以收入或財(cái)富為核心的分析)相比,可行能力方法肯定在信息和方法論的層面上更為苛刻;……這些困難可以部分地解釋為何迄今為止盡管許多福利分析在概念上援引自這一理論,但是能夠抓住該角度的豐富性的經(jīng)驗(yàn)研究應(yīng)用卻相對較少(Martinetti,2000)。
2 多維方法的發(fā)展
在Sen之前,已有研究者注意到,貧困和福利問題遠(yuǎn)非以貨幣表示的經(jīng)濟(jì)指標(biāo)能夠輕松描述并解決的。福利經(jīng)濟(jì)學(xué)領(lǐng)域的早期研究者Cannan曾經(jīng)非常明確地指出,我們必須面對、并且是勇敢地面對這樣一個(gè)事實(shí),在經(jīng)濟(jì)滿足和非經(jīng)濟(jì)滿足之間并不存在一條明確的界限,……我們可以從顯然是經(jīng)濟(jì)學(xué)的一端走向顯然是非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另一端(Cannan,1914)。Pigou也指出,經(jīng)濟(jì)福利不能作為總福利的晴雨表或指數(shù)。……絕不可能由任何一個(gè)部分的變化來測度整體的變化,但這一部分的變化卻總是可以通過自身對整體的變化產(chǎn)生影響。……真正的異議所在,并不是經(jīng)濟(jì)福利是總福利的不良指數(shù),而在于經(jīng)濟(jì)原因可能對非經(jīng)濟(jì)福利產(chǎn)生影響,從而抵消它對經(jīng)濟(jì)福利的影響(Pigou,1920)。
從人類發(fā)展的視角分析貧困問題,Sen是較早明確提出主張從多維角度來認(rèn)識貧困與發(fā)展問題的學(xué)者,他認(rèn)為,人類生活在諸多不同領(lǐng)域遭到踐踏和貶損,首要任務(wù)……是承認(rèn)不同領(lǐng)域的剝奪必須匯集在一個(gè)概括性的框架之內(nèi)來認(rèn)識(Sen,2000)。在近20年來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學(xué)術(shù)研究中,這一觀點(diǎn)已被許多學(xué)者所認(rèn)同并接受,主要表現(xiàn)在許多文獻(xiàn)所采用的方法都引入了大量變量,這些變量不僅包括傳統(tǒng)研究中常用的貨幣性收入及其他類似的貨幣性指標(biāo),而且廣泛地涉及諸多非貨幣性指標(biāo)(關(guān)于指標(biāo)選取的問題將在下一部分詳細(xì)闡述,本部分只關(guān)注指標(biāo)的處理方法),對這些指標(biāo)的處理方法基本可歸入“多維”一類。在已有的研究中,多維方法多用于對貧困的分析(如Cheli和 Lemmi,1995;Betti和 Verma,1999,2008;Bourguignon 和 Chakravarty,2003;Benhabib et al.,2007;Alkire和Santos,2010),也用于對福利的評價(jià)(如 Erikson,1993;Martinetti,2000;高進(jìn)云等,2007)和對公平的研究(如Basu,1987;Bradurd和Ross,1988;Ok,1996)。
在各位研究者的著述中,雖然認(rèn)同了前文所述Sen提出的“概括性的框架”,但是對如何處理這個(gè)“框架”內(nèi)的數(shù)據(jù),卻呈現(xiàn)出鮮明的特色。
有些學(xué)者主張采用編制指數(shù)的方法測量貧困的大小,如Sen和Anand在較早的一篇文獻(xiàn)中曾有比較明確的意見:有必要采用多維觀點(diǎn)看待貧困與剝奪,這種觀點(diǎn)指導(dǎo)我們尋求一個(gè)人類貧困狀況的充分指數(shù)(Sen和Anand,1997)。這種指數(shù)方法也得到了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jì)劃署的支持,其自1997年起編制的人類貧困指數(shù)(HDI)就是對這一思想的集中體現(xiàn),該指數(shù)從剝奪的視角看待人類發(fā)展,并且還可以評價(jià)人類發(fā)展成就(以HDI衡量)的分配狀況。最近,Alkire和Santos提出編制一個(gè)多維貧困指數(shù)(MPI),以綜合地反映“人們在基本服務(wù)和人類核心功能方面受到的剝奪”(Alkire和Santos,2010)。他們的指數(shù)與HDI的維度設(shè)置相同,但指標(biāo)略有差別,也得到了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jì)劃署的認(rèn)可。
而另一派學(xué)者主張借鑒模糊數(shù)學(xué)中模糊集的處理方法對貧困進(jìn)行多維測量,如Cerioli和Zani(1990),Cheli和Lemmi(1995),Martinetti(2000),Benhabib et al.(2007),Betti和Verma(2008)。其實(shí)Sen已經(jīng)關(guān)注到諸如貧困和福利一類概念的不精確性和模糊性,他指出,“一個(gè)規(guī)范的表達(dá)可能是非常精確的,但是未必是對所要描述概念本質(zhì)的確切反映。實(shí)際上,如果這個(gè)概念本質(zhì)上是模糊的,那么對確切反映的需要就要求描述那種模糊性,而不是用某種其他想法取代它——形式上精確但是在表述所要表述的事物方面不確切。”(Sen,1989)。但是Sen并未給出處理這種模糊性的數(shù)學(xué)方法。這里所說的模糊集方法的數(shù)學(xué)基礎(chǔ)是Zadeh(1965)提出的模糊集理論。對于那些明顯帶有模糊色彩的變量尤其是自然語言變量,其類屬邊界帶有明顯的不確定性,不宜采用經(jīng)典的統(tǒng)計(jì)模型加以描述,即將變量值簡單地區(qū)分為“屬于”或“不屬于”某個(gè)類別,或者嚴(yán)格地將人口分為貧困的和非貧困的兩類并不符合實(shí)際(Cerioli和Zani,1990)。而模糊集理論在此方面具有獨(dú)特的優(yōu)勢,因而有利于處理調(diào)查問卷中涉及的主觀評價(jià)類的指標(biāo)值。利用模糊集理論中的隸屬函數(shù),“將各個(gè)維度處理為‘程度’,則不同指標(biāo)的歸總以及貨幣性與非貨幣性指標(biāo)的結(jié)合會(huì)大大便利”(Betti和Verma,2008)。根據(jù)Zadeh的理論,隸屬函數(shù)可以有一系列的類型備選(三角形,L函數(shù),Γ函數(shù),梯形等),模糊分析的目的在于表現(xiàn)增加、減少和近似的想法,每種想法對應(yīng)著一種特定的類型,因此實(shí)證研究中采用的隸屬函數(shù)形式還是有差別的。但是無論隸屬函數(shù)形式怎樣變化,就本質(zhì)上來看,模糊集方法其實(shí)是指數(shù)方法的一個(gè)變種,獨(dú)特性在于它對模糊變量的處理優(yōu)于一般的指數(shù)方法,而且對維度和維度內(nèi)指標(biāo)的權(quán)數(shù)確定是依據(jù)模糊評價(jià)值計(jì)算從而客觀確定的。
雖然同樣承認(rèn)貧困問題的模糊屬性,但是針對已有的模糊集理論測量難以進(jìn)行直觀解釋的問題,Qizilbash(2003)建立了處理貧困模糊性問題的“過度評價(jià)主義”方法,并且論證,該方法有許多值得推薦之處,某些模糊測量指標(biāo)可以在這個(gè)范疇里直觀地解釋為脆弱性。該研究的主要特色是深入分析了“高階模糊性”問題,并定義了“核心維度”,從而進(jìn)一步發(fā)展出“核心貧困(core poor)”的概念。
無論是指數(shù)方法還是模糊集方法,在確定了維度及內(nèi)部的指標(biāo)構(gòu)成之后,關(guān)鍵的問題是權(quán)數(shù)的合理確定,這也是學(xué)界莫衷一是的熱點(diǎn)問題。Alkire和Santos編制的MPI,其數(shù)學(xué)結(jié)構(gòu)屬于Alkire和Foster(2007,2009)提出的多維貧困指標(biāo)族,他們主張采用“嵌套賦權(quán)”法,即“每個(gè)維度都是等權(quán)的;每個(gè)維度內(nèi)的每個(gè)指標(biāo)也是等權(quán)的”(Alkire and Santos,2010)。當(dāng)然,這種處理最顯著的優(yōu)勢在于簡便性,可是其處理方法似乎缺乏必要的理論依據(jù),因而說服力不足。上文提到的模糊集方法的提倡者又有不同的觀點(diǎn)。如果認(rèn)為每個(gè)維度的重要性或者在每一個(gè)維度上各個(gè)具體指標(biāo)的重要性難分伯仲,那么可以選用Martinetti(2000)提出的方法確定綜合測度值。Cerioli and Zani(1990)建議將權(quán)數(shù)處理為被訪者相應(yīng)的效用均值倒數(shù)的對數(shù)。該權(quán)重確定方法的優(yōu)勢在于,給予隸屬度較低的變量以較高的權(quán)重,在評價(jià)過程中更加關(guān)注感知程度較低的維度和指標(biāo)。而在滿意度評價(jià)等研究領(lǐng)域應(yīng)用廣泛的Fuzzy AHP模型,在權(quán)數(shù)的處理上采用了Saaty(1977)的層次分析法,其基本思路是通過對考察指標(biāo)之間進(jìn)行兩兩比較,得到判斷矩陣,然后計(jì)算判斷矩陣的特征向量和最大特征根,接下來對判斷矩陣作一致性檢驗(yàn),以得到各指標(biāo)的權(quán)重值。由于層次分析法涉及對指標(biāo)重要性的比較問題,因此不可避免地要采用問卷調(diào)查的方式得到這部分評價(jià)信息。無論是對專家作調(diào)查,還是對貧困調(diào)查問卷的受訪者同時(shí)做這個(gè)調(diào)查,都無法回避主觀性問題。
3 指標(biāo)的泛化與細(xì)化
根據(jù)Sen的可行能力構(gòu)造的框架內(nèi)運(yùn)用多維方法分析貧困或福利問題,必然要考慮:需要將哪些維度納入可行能力的分析視野,各個(gè)維度應(yīng)包含哪些具體的指標(biāo)。在多年的研究中,學(xué)術(shù)文獻(xiàn)在這個(gè)問題上逐漸呈現(xiàn)出兩個(gè)傾向:(1)指標(biāo)的泛化——維度愈來愈多;(2)指標(biāo)的細(xì)化——指標(biāo)愈來愈具體。這兩個(gè)傾向的積極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即考慮問題的全面性、綜合性及可操作性的增強(qiáng)。但是由此滋生的一系列問題也不容忽視。正如Sen曾闡述的,“為人和貧困指標(biāo)選擇相關(guān)的功能與可行能力都是一個(gè)價(jià)值判斷而不是技術(shù)的運(yùn)用”(Sen,2008),因此有些維度顯然具有道德評價(jià)的色彩,這些維度及其中的指標(biāo)是否應(yīng)列入考察范疇面臨著激烈的爭論,學(xué)者之間的分歧很大;各國的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庫無論在指標(biāo)設(shè)置還是數(shù)據(jù)質(zhì)量方面均存在顯著差別,因而對國家之間的情況進(jìn)行比較的研究往往面臨著可用數(shù)據(jù)不足的尷尬;隨著指標(biāo)的增加,開展調(diào)查的難度愈來愈大,其中既有成本的原因,又有調(diào)查中固有的技術(shù)問題(如調(diào)查員的工作量顯著增加,問卷過長會(huì)導(dǎo)致受訪者由于疲勞而不配合或拒答);有些問題涉及隱私或其他敏感性話題,容易引發(fā)受訪者的抵觸情緒;對調(diào)查員的培訓(xùn)難度加大,從而致使調(diào)查質(zhì)量難以控制,更難準(zhǔn)確估計(jì)。在實(shí)證研究中,許多學(xué)者已對以上所述的積極性和消極性有清醒的認(rèn)識,并對指標(biāo)體系的構(gòu)建原則提出了自己的觀點(diǎn)。如Whelan(1993)指出,剝奪指標(biāo)的選擇與四個(gè)基本問題相關(guān):(1)文化相關(guān)性;(2)時(shí)間相關(guān)性;(3)考慮主觀方面的適當(dāng)性;(4)物質(zhì)的和非物質(zhì)的生活條件之間的合理關(guān)系是怎樣的。又如Alkire和Santos在闡述其維度選擇的正當(dāng)性時(shí),曾列舉了以下幾個(gè)論點(diǎn):簡化,共識,可解讀性,數(shù)據(jù),涵蓋性(inclusivity)(Alkire and Santos,2010)。此外,Cheli和Lemmi指出:在討論某個(gè)社會(huì)現(xiàn)象的指標(biāo)的時(shí)候,必須對可能導(dǎo)致該現(xiàn)象的原因指標(biāo)和該現(xiàn)象可能導(dǎo)致的結(jié)果指標(biāo)作出區(qū)分(Cheli and Lemmi,1995)。他們的觀點(diǎn)雖然是關(guān)于指標(biāo)選擇問題的,但是有些類似于前面所述Sen(1983)對可行能力的闡釋。
在選擇那些具有類似于人權(quán)的道德力量的可行能力時(shí),Sen(2008)給出了基調(diào),他建議著重于以下維度:(1)對所研究的社會(huì)或民族具有特別的重要意義;(2)具有社會(huì)影響力——即這些維度是公共政策的合理關(guān)注點(diǎn),而不是某一種私有物品或可行能力。在之前的一部著重討論自由與發(fā)展問題的著作中,Sen提出從“工具性”視角看待的五種不同形式的自由,即政治自由,經(jīng)濟(jì)條件,社會(huì)機(jī)會(huì),透明性保證,防護(hù)性保障。這五種自由也可看作是他對維度設(shè)置的基本構(gòu)想。
梳理近年來的研究成果可以發(fā)現(xiàn),大部分文獻(xiàn)的思路都秉承了上述Sen的基調(diào)。在維度的設(shè)計(jì)方面,雖然表述方式有些差異,但是常見維度可基可列舉如下:(1)貨幣性維度:收入,消費(fèi)支出(總支出以及分項(xiàng)支出);(2)非貨幣性維度:飲食/營養(yǎng),健康/醫(yī)療,公用事業(yè)服務(wù)的可獲得性,居住條件,某些耐用品的擁有情況,教育/知識,失業(yè),休息/休假,社會(huì)關(guān)系,心理狀態(tài),其他社會(huì)人口因素(家庭的以及家庭所處周邊環(huán)境的)。當(dāng)然,在某一項(xiàng)研究中,不可能包括上述全部維度,由于有些維度之間顯然存在著理論上的某種不和諧,例如,不宜將貨幣性維度與非貨幣性維度聯(lián)立,因?yàn)樨泿攀杖肟梢杂脕頋M足多種非貨幣性需求,即Pigou(1920)所說的“收入支出方式很可能會(huì)改變非經(jīng)濟(jì)福利”;又如失業(yè)者未必缺乏資源(所以將其判定為貧困未必恰當(dāng)),因?yàn)樗赡軗碛胸?cái)產(chǎn)或提供給他所需的其他收入來源(Cheli and Lemmi,1995)。
牛津大學(xué)貧困與人類發(fā)展研究中心(OPHI)對貧困的多維測量曾做過高質(zhì)量且極具啟發(fā)性的系統(tǒng)研究,提出在既往的研究中被忽視但應(yīng)予關(guān)注的一系列“缺失維度”,建議圍繞核心領(lǐng)域搜集更多更好的數(shù)據(jù)。這些核心領(lǐng)域包括:(1)就業(yè),尤其是非正式就業(yè),特別關(guān)注就業(yè)的質(zhì)量;(2)賦權(quán)或主體性,個(gè)體推進(jìn)其珍視或有理由珍視的目標(biāo)的能力;(3)安全,主要關(guān)注遠(yuǎn)離財(cái)產(chǎn)暴力和人身暴力的安全,以及對暴力的感知;(4)體面出門的能力,強(qiáng)調(diào)尊嚴(yán)、尊敬和脫離羞辱的重要性;(5)心理和主觀福祉,強(qiáng)調(diào)生存的意義,以及它的決定因素和滿意程度(Alkire,2007)。
綜上所述,多維方法已愈來愈廣泛地應(yīng)用于貧困和福利問題的研究,而基于Sen的可行能力理論構(gòu)造合理的維度及內(nèi)部指標(biāo)體系,是近期學(xué)界研究的熱點(diǎn)。就未來的研究趨勢為:(1)理論基礎(chǔ)基本定型,關(guān)鍵問題是如何將Sen的理念有效地與現(xiàn)實(shí)世界的統(tǒng)計(jì)指標(biāo)聯(lián)系起來;(2)多維方法的總體目標(biāo)是以綜合指數(shù)的形式反映貧困或福利水平,但是對具體模型形式的選擇仍有很多疑難問題亟待解決,如維度設(shè)置的依據(jù),對Zadeh模糊集方法的批判繼承,以及如何合理地確定權(quán)數(shù);(3)圍繞聯(lián)合國的有關(guān)統(tǒng)計(jì)調(diào)查標(biāo)準(zhǔn)開展指標(biāo)體系的設(shè)計(jì)會(huì)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雖然仍有廣闊的維度和指標(biāo)空間有待開發(fā)。
[1]阿瑪?shù)賮啞ど⊿en,A.).以自由看待發(fā)展[M].任賾,于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2.
[2]庇古(Pigou,A.C.).福利經(jīng)濟(jì)學(xué)[M].朱泱,張勝紀(jì),吳良健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9.
[3]高進(jìn)云,喬榮鋒,張安錄.“農(nóng)地城市流轉(zhuǎn)前后農(nóng)戶福利變化的模糊評價(jià)——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論”[J].管理世界,2007,(6).
[4]薩比娜·阿爾基爾(Alkire,S.)等著.貧困的缺失維度[M].劉民權(quán),韓華為譯.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2010.
[5]Alkire,S.The Missing Dimensions of Poverty Data:An Introduction[J].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2007,35(4).
[6]Alkire,S.,Foster,J.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C].Oxford Pover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Working Paper No.7,2007.
[7]Alkire,S.,Foster,J.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A].In Von Braun J.(ed.)The Poorest and Hungry:Assessment,Analysis and Ac?tions[C].Washington D.C.: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2009.
[8]Alkire,S.,Santos,M.E.Acut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A New Index forDevelopingCountries[C].Working Paper of OPHI,2010,(7).
[9]Basu,K.Axioms for Fuzzy Measures of Inequality[J].Mathematical So?cial Sciences,1987,(14).
[10]Benhabib,A.,Ziani,T.,Bettahar,S.,Maliki,S.The Analysis of Pov?erty Dynamics in Algeria: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J].Topics in Middle Eastern and North African Economies,2007,(9).
[11]Betti,G.,Verma,V.Measuring the Degree of Poverty in a Dynamic and Comparative Context: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Using Fuzzy Set Theory[J].Proceedings of the ICCS-VI,Lahore,Pakistan,1999,(11).
[12]Betti,G.,Verma,V.Fuzzy Measures of the Incidence of Relative Pov?erty and Deprivation: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J].Statistical Methods&Applications,2008,(17).
[13]Bourguignon,F.,Chakravarty,S.R.The Measurement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J].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2003,(1).
[14]Bradurd,R.M.,Ross,D.R.A General Measures of Multidimensional Inequality[J].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Statistics,1988,(50).
[15]Cannan,E.Wealth[M].London:P.S.King,1914.
[16]Cerioli,A.,Zani,S.A Fuzzy Approach to the Measurement of Poverty[A].in Dagum,C.,Zenga,M.(eds.),Income and Wealth Distribution,Inequality and Poverty,Studies in Contemporary Economics,Berlin:Springer Verlag,1990.
[17]Cheli,B.,Lemmi,A.A“Totally”Fuzzy and Relative Approach to the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Poverty[J].Economic Notes,1995,24(1~1995).
[18]Erikson R.,Goldthorpe,J.H.The Constant Flux[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
[19]Martinetti,E.C.A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of Well-being Based on Sen's Functioning Approach[J].Rivista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ociali,2000,108(2).
[20]Ok,E.A.Fuzzy Measurement of Income Inequality:Some Possibility Results on the Fuzzification of the Lorenz Ordering[J].Economic The?ory,1996,(7).
[21]Qizilbash,M.Vague Language and Precise Measurement:the Case of Poverty[J].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2003,10(1).
[22]Saaty,T.L.A Scaling Method for Priorities in Hierarchical Structures[J].Journal of Mathematical Psychology,1977,(15).
[23]Sen,A.Equality of What?[A].In McMurrin,S.(ed.),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24]Sen,A.Poor,Relatively Speaking[C].Economic Papers,1983.
[25]Sen,A.The Living Standard[C].Oxford Economic Papers,1984.
[26]Sen,A.Well-being,Agency and Freedom:the Dewey Lectures 1984[J].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1985,82(4).
[27]Sen,A.The Standard of Living[A].In Hawthorn,G.(ed.),The Stan?dard of Living[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28]Sen,A.Economic Methodology:Heterogeneity and Relevance[J].So?cial Research,1989,(56).
[29]Sen,A.Inequality Re-examined[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
[30]Sen,A.Capability and Well-being[A].In Nussbaum,M.&Sen,A.(eds.),The Quality of Life[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
[31]Sen,A.On the Foundations of Welfare Economics:Utility,Capability and Practical Reason[A].In Farina,F.,Hahn,F.,Vannucci,S.(eds.),Ethics,Rationality,and Economic Behaviour[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
[32]Sen,A.A Decade of Human Development[J].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2000,1(1).
[33]Sen,A.The Economics of Happiness and Capability[A].In Bruni,L.,Comim,F.,Pugno,M.(eds.),Capability and Happines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34]Sen,A.,Anand,S.Concepts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Poverty: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In Human Development Papers 1997:Poverty and Human Development[M].New York: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1997.
[35]Zadeh,L.A.Fuzzy Sets[J].Information and Control,19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