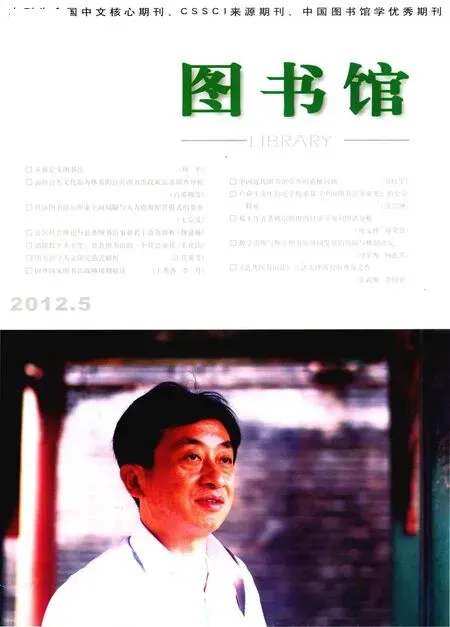公民社會理論與公共圖書館事業若干命題辨析
(西安文理學院圖書館 陜西西安 710065)
1 引言
上世紀80年代,隨著當代自由主義的崛起,“公民社會理論”成為西方學術界研究的熱門話題,甚至將之看做是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希望。在我國,隨著各類思潮的推介與爭鳴,“公民社會”成了一個流行詞語。特別是十七大以來,官方文件頻頻出現相關概念,使人們對“建設公民社會”有了更多的期待。
公共圖書館事業是一項社會性事業,它服務于社會,亦受社會環境的制約,更會受其影響。因此,“公民社會理論”是公共圖書館事業研究一個必須面對、無法回避的話題。
當前的公共圖書館理論研究已涉及公民社會理論,但在廣度與深度上差強人意,且模糊混淆的認識盲點頗多。因而,就目前而言,任何短淺之見,謬誤之論都會對認識的澄清與實踐的借鑒有所裨益。“江海不棄涓流故能成其大,高山不舍微塵方可現其高”,在此不顧愚魯,拋磚引玉,陳述一點困惑與思考,冀望專家同行指點迷津,不吝賜教。
2 公民社會理論與公共圖書館事業若干命題辨析
依據常識,對一種現象或理論的研究,首先必須要清楚是什么?概念、范疇與性質。之后是為什么?它的價值、意義。在此基礎上再探究怎么做?以及會遇到哪些問題,如何解決?因此,對公民社會理論的探究亦可大體劃分為概念命題、價值命題與實踐命題。相對應,作為子命題亦可分為公共圖書館事業視野下之公民社會概念命題、價值命題與實踐命題。下面擬在此框架內,做一點嘗試性思考與解讀。
2.1 公共圖書館事業視野下之公民社會概念命題辨析
必須承認一個現實,公民社會理論一直存在著極大的爭議。各國學者構建了不同的理論體系,給公民社會賦予了不同的內涵。各類理論存在著不小的差異,有的甚至相互沖突。〔1〕“公民社會”概念孕生并演進于西方社會,它在不同的時代、以不同的理性結構出現在社會理論中,既體現著時代進步中社會自組織的痕跡,又帶有公民個人理性建構的傾向,它是一個體系極富開放性、內涵極富衍變性的概念。當代公民社會理論,既作為基于民主憲政的一種政治哲學,成為一種政治口號;又作為一種社會研究范式,在理念、價值與信仰層面為人類共同體成員提供一幅美好生活畫卷;還作為一種社會組織方式,嘗試在一種介于政府和企業間的“第三部門”實現公民自治;各種各樣的詮釋林林總總。〔2〕這就產生了一種現象,“公民社會理論”浩如煙波,每一個團體、每一個行業,甚至每一個個人都會對其建構、解讀。雖然似乎都在說“公民社會”,但卻是各說各話。
“公民社會理論”有一個核心價值,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正義的普世理想。因而,“公民社會理論”可以廣義地概括為對民主、自由、平等、正義之普世理想的各種憧憬、設計與實踐。正是因其廣泛的參與性、廣泛的包容性,公共圖書館事業視野下之公民社會概念內涵也可以廣義地概括為“公共圖書館事業中對民主、自由、平等、正義之普世理想的各種憧憬、設計與實踐”;它有廣闊的外延,既包括形而上的“知識自由”、“圖書館權利”探討,也包括形而下的“圖書館公共治理”研究、“社會力量辦館”實踐等等。
總之,當前社會化背景下圍繞“公共圖書館”的各類探討都可以納入公民社會理論之命題范疇。
2.2 公民社會理論對于公共圖書館事業之意義命題辨析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對于公民社會理論的價值意義,亦可以大體歸納為理論認識意義和實踐指導意義兩個層面。在理論認識層面,梁燦興先生提出了“公民社會是公共圖書館事業產生和健康發展的社會基礎”的命題〔3〕。梁燦興先生提出的命題,是探究“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元命題,是探究公共圖書館的本質、過去、現在與將來,應該說是圖書館理論的基礎性研究。以下筆者將圍繞此命題的思考做一陳述。
“公民社會是公共圖書館事業產生和健康發展的社會基礎”可以分解為兩個小命題:“公共圖書館產生于公民社會”和“公共圖書館健康發展必須依賴公民社會”。
關于“公共圖書館產生于公民社會”。“老槐也博客”曾轉載臺灣圖書館學者賴鼎銘先生的一篇文章《美國公共圖書館為何興起?》〔4〕,可惜筆者未找到原文。賴先生認為西方的公共圖書館是由下往上自主發展出來的機構,是市民社會(公民社會)的產物〔5〕。梁燦興先生通過對西方圖書館史的回顧與梳理,認為“會員圖書館是近代公眾(公共)圖書館之母”,“會員圖書館是近代公民社會的自治體”〔6〕,“后來由于會員圖書館受眾的局限性和資金來源僅僅依靠捐助的不穩定性,才上升為一種制度,由政府財政來支持”〔7〕,它仍然“是對公民信息自治的延續”〔8〕。關于“公共圖書館健康發展必須依賴公民社會”,對此命題梁燦興等先生的論證比較含糊。“西方公共圖書館在管理體制上,更多地體現了公民自治的特點……這也是西方公共圖書館為什么能夠一直獲得社會認可,政府不能不支持的原因……一個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公民社會是近代公共圖書館勃興的社會基礎。”〔9〕
筆者對此存在一些理解困惑,因而,將“公共圖書館產生于公民社會”這一命題,解讀為:近代公共圖書館事業產生于西方社會,誕生于西方的公共圖書館自然也帶有西方社會的印記。它在價值取向上推崇權利平等、知識自由,在制度安排上體現公民自治。這些正是絕大多數“公民社會理論”的邏輯起點與核心價值,故而說“公共圖書館產生于公民社會”。
對“公共圖書館健康發展必須依賴公民社會”這一命題,筆者亦在西方制度文化的語境下加以理解。西方社會有民主政治的傳統。民主政治的一大突出特征是“以議會為核心的代議制度”,即公民選舉產生本階層、本利益團體的代言人組成議會,民眾的各種訴求通過代言人(議員)提交議會討論,然后表決,如果表決通過則形成“法案”,“法案”具有強制政府、相關機構以及個人執行的效力。公共圖書館的建立產生于此種民主機制,它的健康發展也依賴于此種民主機制。除了制度層面的保障,西方民主政治還有一種“權力制衡”的架構,它是政府有限權力管理與公民自治結合的管理模式,有向下負責的機制,有公民參與的途徑。理論上講,只要公共圖書館事業是真實民意的體現,就一定會獲得正常發展的必要保障。
筆者認同西方社會“公民社會是公共圖書館事業產生和健康發展的社會基礎”之命題。但是,筆者困惑:中國的公共圖書館是否也產生于公民社會?其健康發展是否也有對公民社會的必然依賴?
中國歷史上是否存在“公民社會”?當前仍在爭議。但是,無可爭議的是“中國公共圖書館事業誕生于清朝末年”,其社會主體特征是“臣民社會”。即使社會力量是近現代圖書館事業的啟動者,社會力量也只是將其作為“推行新政、作育人才”的一種手段〔10〕,其信奉之價值觀是“臣民盡忠”,依賴之制度安排是“允許臣民上書言事”。這與公民社會“公民自治、權利意識、平等自由”之核心理念南轅北轍。基于上述認識,并參閱相關史料,筆者以為,中國公共圖書館是學習西方的產物。由于中國“公民自治”的文化傳統與制度安排先天不足,公共圖書館事業在中國發生了變異,并非公民社會信息資源自治的社會運動,而是一個統治階級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刻意規劃的結果。它是統治階級所推行“新政”的一部分,是政治的附屬品。
顯然,中國公共圖書館沒有產生于公民社會。如果此命題成立,那么公民社會理論對于中國公共圖書館事業之意義而言就不是“失落的脊骨”,而是“全新的命題”。
對于“全新的命題”的價值意義的認識不能脫離現實語境,決不能簡單化、概念化、機械化、教條化。筆者以為當前的探究剛剛起步,遠未畫上句號,更未告一段落。
筆者以為當前需要探究的首要命題是:中國公共圖書館事業需不需要依賴公民社會?如果需要,為什么?
欲回答此問題,需要先明確:沒有產生于公民社會的“公共圖書館”是不是公共圖書館?如果是,就存在一個選言判斷,沒有公民社會的公共圖書館能夠健康發展,還是不能?對于現實與未來,中國公共圖書館事業究竟如何走出?有“依靠政府說”、有“市場經營說”,也有“民間內生說”。而各種說法都涉及“公民社會理論”。這就是公民社會理論對于公共圖書館事業之意義所在。
2.3 公民社會理論與公共圖書館事業實踐命題辨析
公民社會理論與公共圖書館事業實踐之命題可歸為兩類范疇:一類為公共圖書館事業影響公民社會,如“中山大學公民公共圖書館治理社會中心”、“湖南望城縣楊利君公民圖書館”等,其實質是發揮圖書館教育職能,為公民社會以及社會發展議題提供學習、交流、傳播空間,傳播公民知識、培育公民意識。由于公共圖書館的社會教育職能已是業界常識,故在此不多重復。另一類是公民社會理論影響公共圖書館事業,影響公共圖書館事業的外在形態、運作流程乃至本質屬性。下面筆者將圍繞運作流程中公共圖書館公共治理探索相關命題之思考,做一敘述。
上世紀80年代,西方各國掀起一股行政改革浪潮,與之相應的是意識形態領域的“公共管理理論”中的“善治理論”。由于有相同之背景,“善治理論”與“公民社會理論”幾乎涉及同一命題。如“善治理論”強調“公共治理轉型”,其價值導向之一是政府由過去“以公共權力為核心”向“以公共服務為核心”轉變;其實質就是“公民社會理論”所主張的“社會基本結構由政府——單位——(作為單位人的)個人的單向、單維的關系,轉變為多元、互動、社會參與和自組織形式的結構,政府不再是一個全能的部門,它行使國家安全、公共政策、宏觀調控等有限職能……社會的組織結構以大量的公民自組織形式為基礎,個人作為具有公民意識的公民社會成員,形成廣泛的自組織形式,構成政府和企業之外的第三部門,它們是大量具體社會功能的直接承擔者。”〔11〕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小政府,大社會”。因此,“公共治理轉型”可以說是“公民社會理論”的實踐,也可以說是“公民社會理論”之實踐子命題。
回顧百年歷史,中國公共圖書館事業興起于“官辦”;民國時期有“新圖書館運動”〔12〕,亦有“無產階級宣傳陣地”;新中國成立后,公共圖書館成為政府直接管轄下的事業機構,職業活動由行政指令推動,以政治需要來規定其運作方式、社會職能及社會價值。全能政府完全掌控下的公共圖書館治理模式,有利有弊。“利”在發展運作有了依靠,有了保障;“弊”在“放棄了職業話語權而成為一種政治的附屬品”。〔13〕改革開放后,社會轉型,政府逐步從經濟、文化領域“后撤”,失去政府全力扶持的中國公共圖書館事業隨之陷入困境。面對現實困境,業界有主張“市場化”、“產業化”,實行“有償服務,以文養文”,〔14〕但實行效果卻遭致廣泛詬病。蔣永福等先生曾論證“公共圖書館發展中的政府責任”〔15〕主張“堅決依靠政府”,并針對“人治”的不確定,呼吁“法律保障”。但是回顧建國以來的公共圖書館發展史,卻不能不讓人心生疑慮。“堅決依靠政府”,政府不重視,則出現發展困境、生存危機;政府重視,則存在資源空耗、低效腐敗。建國后,公共圖書館事業起起伏伏,究其原因應該在于以行政之手段從事不同性質之文化事業。因為“行政化管理”下存在人浮于事、低效腐敗的原生缺陷。王子舟等先生主張“社會力量辦館助館”,因為社會力量“屬于內生的、自下而上的力量,是推動基層圖書館建設的一種原動力,最能體現創新精神”〔16〕。但是各類民辦圖書館發展中遭遇的各類困境又明示:中國目前沒有“圖書館事業自下而上內生發展”的社會環境。所有以上種種原因催生出一類新命題:公共圖書館治理。
公共圖書館治理屬于公民社會理論影響下的公共圖書館事業實踐命題。顧燁青先生針對當前政府所提供的公共圖書館效率低下的弊端,認為由構建公民社會的民間組織來提供圖書館公益是最理想的選擇,提出了“凸顯民主,強調自治(公民社會理論之精髓)是貫穿中國圖書館管理體制創新和理念創新的一條主線”的命題〔17〕。曾主張“堅決依靠政府”的蔣永福先生開始探究“公共圖書館治理中的政府責任”〔18〕、“公共圖書館治理結構及其優化策略”〔19〕等命題。李忠昊、趙紅川回顧公共圖書館百年治理的歷程,認為“圖書館善治就是使圖書館的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公共圖書館離不開公共管理,公共圖書館必然走向公共管理”〔20〕……在圖書館研究領域,“公共圖書館治理”已悄然形成熱點,換句話說,就是公民社會理論與公共圖書館事業實踐之命題探究已成熱點。
對于公民社會理論與公共圖書館事業實踐之命題探究,筆者滿懷期待,并初步理解:公民社會理論在公共圖書館事業中之實踐,不是簡單地“引入社會資金,鼓勵社會力量辦館助館”,不是公共圖書館事業“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傳統原則的延續,而是以公民為本位,政府與社會關系重新調整思想主導下公共圖書館事業領域的具體實踐;其目的在于實現公共圖書館應真實民意而產生,滿足公民的真實需求,依靠公民稅收維持運轉,形成具體高效的向公民負責的體制制度。總之,實現“公民社會是公共圖書館事業產生和健康發展的社會基礎”,可將中國公共圖書館事業引入健康發展的良性軌道。
3 結語
鑒于公民社會理論與公共圖書館事業命題研究初興未艾,許多命題尚不明確,故筆者拋磚引玉、斗膽辨析。公共圖書館是一種社會現象,社會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社會就是社會,公民社會是人們針對現實社會特征的一種特定視角的概括性認識。公民社會是一個仍在爭議,體系極富開放性、內涵極富衍變性的概念,如果不加辨析,籠統地以“公共圖書館與公民社會”為命題,在探究中容易掉入偷換概念的陷阱,亦容易將命題抽象化,口號化以及空洞化,最終會將“真命題”演變為“偽命題”。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長青!真理蘊含在現實之中,真理會在探索中明晰。衷心祝愿中國公民社會健康發展、中國公共圖書館事業健康發展!
1.楊建偉,張平.公民社會理論之困境.學術月刊,2007(7):18-25
2.周國文.“公民社會”概念溯源及研究述評.哲學動態,2006(3):58-66
3,7,9.梁燦興.尋找圖書館失落的脊骨——公民社會:近代圖書館發生和發展的基石.圖書館,2005(2):16-18
4,5,17.顧燁青.試論公共圖書館管理體制與管理理念的創新.圖書館,2007(6):1 -6,12
6,8.梁燦興.公眾圖書館是公民社會的產物——圖書館事業是公民社會信息資源自治的社會運動.圖書館,2006(2):8-12
10.張樹華.我國圖書館觀念的變遷和發展.圖書館,2006(3):1-5
11.李熠煜.當代中國公民社會問題研究評述.理論參考,2006(2):56-58
12.王旭明.二十世紀“新圖書館運動”述評.圖書館,2006(2):22-25
13.李超平.我國公共圖書館歷史定位之反思.圖書館,2006(2):1 -4,18
14.黃本華.90年代圖書館有償服務理論研究綜述.圖書館理論與實踐,1997(3):30-33
15.蔣永福.發展公共圖書館事業的政府責任.圖書館論壇,2006(6):85-88
16.王子舟.偉大的力量來自于哪里——解讀社會力量辦館助館.中國圖書館學報,2010(3):26-33
18.蔣永福.公共圖書館治理中的政府責任.圖書館論壇,2009(6):79 -82,53
19.蔣永福.公共圖書館治理結構及其優化策略——針對我國公共圖書館管理體制改革重點的分析.圖書與情報,2010(5):18-22
20.李忠昊,趙紅川.百年治理的歷程——公共領域的發展與公共圖書館的未來.圖書情報論壇,2005(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