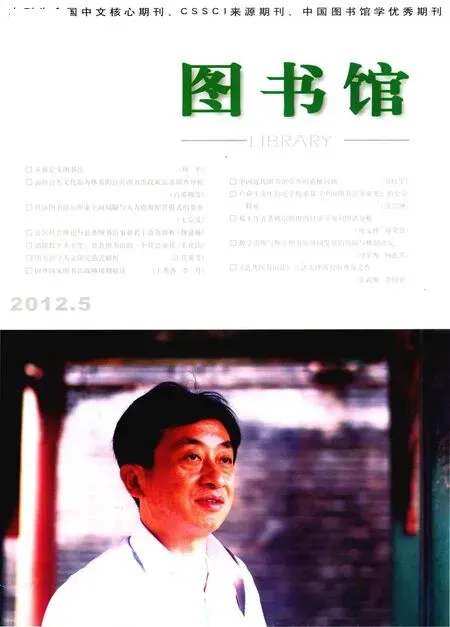圖書館社會責任的合理性證明
(黑龍江大學信息管理學院 黑龍江哈爾濱 150080)
自1969年美國圖書館協會(ALA)成立“圖書館社會責任圓桌會議”以來,圖書館社會責任的合理性問題一直受到廣泛的關注。1972年,時任ALA知識自由委員會主席的伯寧豪森撰文批評圖書館社會責任觀,認為圖書館承擔社會責任違背了《圖書館權利法案》所倡導的知識自由理念。很多人不同意伯寧豪森的觀點,紛紛發文駁斥伯寧豪森,認為圖書館承擔社會責任不僅不違背知識自由理念,反而有利于維護弱勢群體的知識自由。由此出現了ALA歷史上著名的“伯寧豪森論爭”〔1〕。2010年,中國圖書館學會年會設立“圖書館社會責任”分主題,在征文過程中,人們圍繞圖書館社會責任的概念及其內涵的界定問題也展開了熱烈的討論〔2-3〕。筆者認為,圖書館承擔社會責任有其合理性依據,本文將從“圖書館公民”、社會利益觀、義務論、信息政治經濟學、利益相關者理論論證圖書館社會責任的合理性。
1 “圖書館公民”
“圖書館公民”一詞來源于“企業公民”概念。按照英國“企業公民公社”對企業公民內涵的解釋,企業應是作為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從而有權利、也有責任為社會的發展做出貢獻的國家公民之一。〔4〕企業公民理論認為,社會的健康和福利與企業密切相關,因此企業應全面考慮其對所有利益相關人的影響,包括對雇員、客戶、社區、供應商和自然環境的影響。一些企業意識到:在自身的經營戰略中主動納入社會的訴求,采取某些回饋社會、創造公共價值的舉措,也能為自身謀得利益。此時企業的行為就不僅是“有道德的自利行為”,同時也是“自利性的道德行為”。〔5〕
毫無疑問,圖書館是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圖書館也是國家的公民之一,即“圖書館公民”。圖書館作為有別于自然人的組織體,其是否具有公民主體資格可能招致人們的爭議。“法人實在說”代表人物德國學者倍斯勒爾(Beseler)和基爾克(Gierke)等人認為,團體始終與個人并存于人類社會,自然人為自然的有機體,有其個人意志;團體則為社會的有機體,有其團體意志;對于社會有機體賦予法律的人格,使之成為權利義務的主體,即所謂法人。〔6〕這說明,圖書館作為既享有權利又履行相應義務的團體,具有人格化的法人資格,可被當做“公民”看待。那么,身為“公民”的圖書館“有責任為增進社會的公益做出貢獻”〔7〕。
2 “社會利益觀”依據
社會利益是區別于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的特殊利益,它指通過促進社會合作、恪守公序良德而實現的利益。社會利益觀堅持社會利益的獨立性,倡導社會本位,強調社會連帶和社會合作,同時又不把社會本位推向極端,而是將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和協調發展作為終極目標。這種思想同圖書館社會責任觀是完全契合的。一方面,以“圖書館公民”身份存在的圖書館,始終處于社會的種種關系之中,甚至有時直接處于圖書館的自身權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關系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圖書館必須處理好與其他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和利益失衡問題,才能既保證自身的正當權益,也能保證促進社會利益。因此,圖書館為了更好地實現自身權益,倡導社會利益本位就成為應然和必然。另一方面,在當代信息社會,計算機技術、信息技術、網絡技術在給人們帶來諸多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數字鴻溝、信息分化、信息歧視、知識貧困等社會問題,其實質是利益的分化與失衡,集中表現為“信息強者”和“信息弱者”的普遍存在。面對這一社會問題,以維護社會的信息公平為使命之一的圖書館,就不能不承擔彌合數字鴻溝、信息分化的社會責任。
3 “義務論”依據
規范倫理學中,一直存在著“義務論”和“目的論”兩種流派。“目的論”認為,應以目的為依據解釋事物的特性或行為。目的論的極端可能走向完全“以目的證明手段”的非道德主義。“義務論”則認為,善惡的價值判斷最終要歸結為行為的正當與否,而行為的正當與否,則要看該行為本身所固有的特性或者行為準則的性質是什么。戴伊(Dye)等人所認為的社會責任最基本的內涵——在不同個體之間就哪些行為能夠為人接受以及行為者使用何種方式為其行為辯護達成共識〔8〕,就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的。義務論為圖書館社會責任提供了倫理學依據:圖書館有義務考量自身行為是否具有正當性——圖書館的某種行為無論出于什么目的,都要考慮是否具有正當性的問題。〔9〕社會責任不是簡單的責任,它要求圖書館要充分認識和預判行為的結果,把可能帶來的“負外部性”降低到最低限度,而且還要把這種認識用于指導實踐,力求達到“正外部性”的效果。所謂“負外部性”,是指給他者造成不利影響且不為其承擔責任的行為屬性,而“正外部性”是指能夠給他者帶來有利或有益結果的行為屬性。顯而易見,圖書館作為公益性社會組織,應該承擔使自己的行為具有“正外部性”的義務。
4 “信息政治經濟學”依據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后,很多西方學者開始運用政治經濟學的概念體系和方法剖析信息生產、交換和使用過程中體現的社會關系,并把這種研究視角及由此形成的對當今社會的分析稱作“信息政治經濟學”。信息政治經濟學比其他研究視角(如純經濟學視角、后現代主義視角等)更關注信息社會中的階級關系和信息平等;關注市場機制對信息公共品的侵蝕以及由此帶來的負面社會影響;關注政府以及社會的強勢階層通過信息流通而實施的社會控制;關注全球范圍內日益拉大的信息鴻溝對發展中國家利益的損害;關注信息帝國主義或文化帝國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的文化侵略。〔10〕信息政治經濟學學者們認為,在當代信息社會,市場機制“具有把信息把公共品轉化為商品、把信息交流關系轉化為商業化的社會關系的內在傾向”,而“信息的商品化使公共信息機構(公共圖書館是其最典型的代表)和社會的貧弱階層都蒙受損失:公共信息機構被迫降低其公益性程度,而貧弱階層則成為信息貧窮者”。這就是信息分化現象。信息政治經濟學學者們普遍把建立更為公平的信息生產和流通關系視作信息政治經濟學的最高實踐目標。〔11〕正是這一目標使得信息政治經濟學學者們成為圖書館社會責任倡導者的志同道合者。信息時代最值得關注的社會問題之一,就是日益加劇的信息分化所導致的信息不公平問題。面對這一社會問題,圖書館如若選擇漠視,并且認為幫助解決這些問題將會給圖書館增加額外的“負擔”,解決這些問題并不是圖書館“分內應做之事”,那么勢必使得信息弱勢群體蒙受更大的損失。所以,若要“建立更為公平的信息生產和流通關系”,圖書館就應從社會責任的角度出發,主動承擔消除信息主體利用信息的經濟障礙和技術障礙,對“信息弱者”提供特殊服務,保障社會成員平等獲取信息的機會的社會責任。
5 “利益相關者理論”依據
利益相關者理論認為企業本質上是一種受多種市場和社會影響的組織,不應該只是股東主導的組織制度,應該考慮到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要求。它揭示出在企業的生存環境中還存在許多影響企業生存的利益群體。這樣,企業存在的目的就不能僅是為股東服務,還要承擔社會責任;承擔社會責任也不能僅僅限于公益、慈善和捐贈,更主要的是關注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如企業內部的員工、客戶、供應商、所在社區、政府等;還要承擔環境責任,提高資源利用率,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和對資源的過度利用。總之,利益相關者理論顛覆了“股東至上論”,為企業社會責任理論奠定了理論基礎。對于圖書館而言,其利益權人(即利益相關者)是指其利益與圖書館服務相關的個人、群體或組織。圖書館是在“與民眾、政府、企業(包括私人資本)及其他組織的相互作用中發展的”〔12〕。也正是圖書館與民眾、政府、企業及其他組織之間的互動式的社會關系,為圖書館社會責任奠定了一定的理論依據。圖書館占有和享受了民眾、政府、企業及其他組織所賦予的資源——社會支持、資金、自然環境、政策支持等,那么,圖書館為這些利益相關者作出一定的“回報”就成為一種必要的責任。同時,圖書館為了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就需要爭取利益相關者的支持,需要對圖書館利益相關者進行深入研究:了解不同利益相關者在圖書館發展中的利益所在;了解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相互關系甚至沖突;尋求平衡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以最大程度地聚合社會支持的途徑等。
6 結語
圖書館承擔社會責任是有利于圖書館自身、有利于社會及社會群體,負有使命感的圖書館應自覺尋求和承擔社會責任。對于圖書館社會責任,有人支持,有人反對,但它的存在卻是客觀的,它存在的合理性也不會因為有人支持有人反對就失去了其價值。圖書館社會責任的合理性的證明,屬于“價值判斷”范疇,因而應該允許存在不同價值觀之間的意見分歧。但無論如何,對圖書館社會責任的合理性問題的關注和研究,必將有利于圖書館社會責任問題研究的進一步深化和拓展。
1.Legaspi S,Kunichika D.Three Articles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Librarianship.〔2011 - 08 - 06〕.http://www.authorstream.com/Presentation/Tommaso-63358-Social-Responsibility-Three-Articles-Librarianship-Introduction-Situation-movement-Why-responsi-Sports-ppt-powerpoint/
2.范并思.圖書館社會責任專欄導語.圖書館建設,2010(7):1
3.于良芝等.如何理解“圖書館社會責任研究”.圖書館建設,2010(7):2
4.崔開華.組織的社會責任.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139
5.吳伯凡,陽光等.企業公民:從責任到能力.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Ⅶ
6.梁彗星.民法總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119
7.蔣永福,佟鑫.圖書館社會責任研究.情報資料工作,2011(4):36-40
8.周志忍,陳慶云主編.自律與他律——第三部門監督機制個案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7
9.〔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陽,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124
10,11,12.于良芝,李曉新,王德恒.拓展社會的公共信息空間——21世紀中國公共圖書館可持續發展模式.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