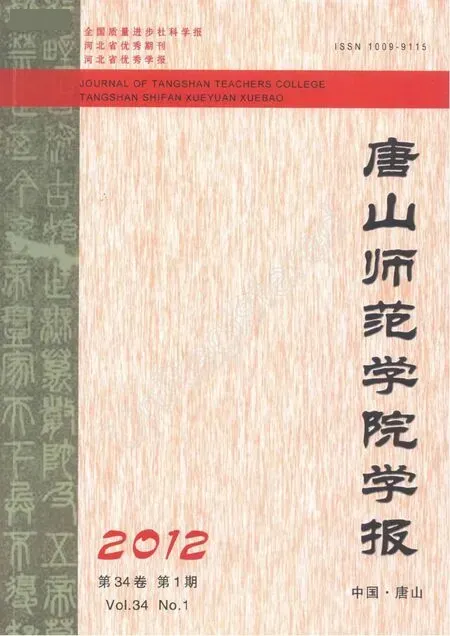晚清“詞史”意識與詞論建構及創作的關系
于廣杰,蘇 濤
(1. 河北大學 古籍整理研究所,河北 保定 071002;2. 天津城市職業學院,天津 300250)
晚清“詞史”意識與詞論建構及創作的關系
于廣杰1,2,蘇 濤2
(1. 河北大學 古籍整理研究所,河北 保定 071002;2. 天津城市職業學院,天津 300250)
“詞史”意識的形成源于風雅精神和詩敎傳統,與“史詩”創作遙相呼應。這種詞脫離傳統的“情愛”題材,用詞體特有的格調意趣、抒情方式、語言風格反映社會現實、歷史事件,表現士人的歷史責任感和政治擔當精神,從而使詞這種文學體裁與詩歌合流,尤其在晚清形成了一股強大的“詞史”創作的潮流。在梳理詩史與詞史的內在關系的基礎上,從推尊詞體的文學思潮、詞學理論發展的內部規律、詞史意識與實踐的角度對晚清詞史意識進行深入的剖析,以探討詞史范疇的形成及對詞論和創作的影響。
詩史;詞史意識;詞史
一、 從“詩史”到“詞史”
“詩史”作為傳統詩歌的創作和評價標準直接源于《詩經》的“風、雅”精神,并和漢代“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樂府詩相表里,體現了詩歌作者關心社會現實、國家政治命運和人民疾苦的態度,深沉的用世情懷,仁民愛物的儒者精神,以及處在時事、政教事件、社會環境影響下的士人、世人心史、個人心史。這是士大夫、知識分子悲天憫人、擔當國事,干預現實社會的愿望和沖動在文學藝術領域的深刻反映,是詩人“溫柔敦厚”的風人之致在詩歌創作中的具體體現,也是“詩教傳統”、“風雅精神”的傳承。“詞史”這一詞學批評范疇,是“詩史”這一范疇在詞學創作領域和批評領域的延伸與應用,其含義直接繼承了“詩史”要求詩歌關注社會現實、反映社會、國家、民族重大歷史問題、政教事件、關心人民生活境遇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內涵。論者謂:“詞史”是清代學者提出的詞學話語,意指兼具“實錄”精神與“《春秋》筆法”之詞作。又有論者說:“詞史”有一個從“詞史意識”到“詞史”理論的發展過程,具體表現形式為以詞存史,即通過輯錄和評論詞作與編輯詞人傳記材料,來保存歷史文獻和反映社會人情世態;以史入詞,“史外傳心之史”;以史存詞,即引入史傳的形式,保存詞作與詞人資料,反映一代詞壇風貌[1]。以上論述從“詞史”范疇的演變過程、內涵及創作特點諸方面對“詞史”進行了概括。實則從“詩史”精神到“詞史”意識的演變過程發端于南宋,越代接續完成于清初,而昌盛于晚清的民族變局中,并在晚清的詞家中形成一種影響極大的創作風潮。清代初年,陳維崧提出了“詞史”說,這是在文學批評領域第一次明確形成一個與“詩史”并立的概念。常州詞派周濟從理論上對“詞史”范疇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并與“比興寄托”理論結合起來,遺憾的是周濟和當時的詞家并沒有在創作上形成與他們的理論同樣輝煌的盛況。晚清以王鵬運為首的臨桂派詞人以史入詞敘寫時事,以史家晦筆反映敏感的政治事件,通過個體心靈的感受反映出國運陵夷時代的民眾心聲,用詞這一文學形態記錄著民族的巨變、國家社會的苦難,以及士人的幽微的心史,編著了一代政治史、社會史、心靈史,為晚清詞壇增添了新的亮色。
那么“詞史”范疇何以在清初出現,并流衍為晚清的一股頗有影響的文學思潮呢?葉嘉瑩先生為我們描述了三個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為詞這種文體具有“宜休窈渺”的美感特質,便于抒情,尤其是言外深隱的深衷。這很適宜處在政治敏感和高壓生存環境下的清初士人群體借小詞以澆塊壘,也為文人士大夫形成了一個以詞接續風雅傳統和詩騷寄托、比興精神的新傳統。其次,清代的社會環境變化也為“詞史”意識的深入士人提供了社會政治土壤,尤其是晚清的國家巨變,更是刺激了士人的擔當精神和愛國豪情。第三,詞學家的理論推演、詞學家和作者的學者身份,是“詞史”意識的被廣泛接受的學術和人文背景[2]。但是,詞史意識的形成與發展關系著詞學史、詞體認知、創作、審美上的諸多問題。對這些問題的深入探討將有助于我們理解詞體和詞史的很多未解之謎。
二、晚清“詞史”意識與晚清詞學理論建構及創作的關系
晚清是中國歷史上變化最為劇烈的時期,內亂頻仍,外敵入侵,整個民族危在旦夕。這激起了廣大士人深沉的憂患意識,也喚起了他們救亡圖存的政治愿望和行動。“詞史意識”就是此思潮滲入到文學創作領域的表現。晚清的很多詞家和詞論家對“詞史”范疇都有著深入、自覺地認識,并表現在詞學理論建構和詞的創作之中,形成一股頗有影響的文學思潮。
(一)“詞史”范疇的建構與推尊詞體的文學思潮有著密切的關系
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推衍張惠言的詞學主張曰“感慨所寄,不過盛衰,綢繆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饑,或獨清獨醒,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見事多,識理透,可為后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若乃離別懷思,感士不遇,陳陳相因,唾沉互拾,便思高揖溫、韋,不亦恥乎?”[3]周濟認為詞里是可以有感慨的,感慨和寄托主要都是關心朝廷、關心國家、關心政治的盛衰。摒棄了詞為“小道末計”的傳統認知,推尊詞體,將詞與詩歌在文體地位上等同起來。“詞史”范疇的建構與推尊詞體的文學思潮有著密切的關系。就其大端來說,正如劉崇德教授論述的那樣“至清乾嘉以來,經常州詞派的造化,詞亦成為文章之一體,終成正統。于是人們只辨汗漫,而不識河潢矣。”而就詞體與詞論本身來說,張宏生論曰:“‘詞史’說的提出,是自宋代以來尊體趨勢的一個發展……以往詞的尊體,向詩歌領域尋找資源,大致表現在創作實踐的層面,進入理論探討者尚少。陳維崧提出‘為經為史’和‘存經存史’,直入‘詩史’說的核心,成為與詩壇共時性的回應,這在以往詞壇上還少見。這一事實,充分說明,明清之際,關于詞的理論探討,已經進入了一個自覺的層面。”[4]鄭文焯在與友人論詞時提到,自張惠言提倡“意內言外”之旨以來,詞家大多能夠認同并付諸實踐,不敢“自蹈下流”。這正是晚清“尊體”觀念和“詞史意識”在理論和實踐層面融合的體現。
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認為在這國事日危、民生日蹙的嚴峻關頭,詞家只有“慨嘆時艱,本小雅怨悱之義”,才能使詞另辟一境,不朽于世:“今日者,孤枕聞雞,遙空鶴唳,兵氣漲乎云霄,刀瘢留于草木。不得以而為詞,其殆宜導揚盛烈,續《鐃歌》、《鼓吹》之音,抑將慨嘆時艱,本小雅怨悱之義。人歌有心,詞乃不朽,此亦倚聲家未劈之奇也。”[5]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晚清的“詞史”觀念之所以成為一種籠罩詞壇的詞學觀念、創作標準和詞美標準,正與這種推尊詞體的理論風潮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是詞家和詞論家主體感悟、理論闡發和自覺建構的一個過程。
(二)“詞史”范疇建構是詞學理論發展的內部規律
如果說清初的推尊詞體有著某種創作實踐和創作環境的需要,而清中期以后,尤其是常州詞派的表現則是一種自覺的理論建樹,也就是筆者所說的詞學內部發展規律。蔣兆蘭在談到晚清詞學發展格局時說:“嘉慶初,茗柯宛鄰,溯流窮源,躋之風雅,獨辟門徑,而詞學以尊。周止庵窮正變,分家數,為學人導先路,而詞學始有系統,有歸宿。逮乎晚清,詞家極盛,大抵原本《風》《騷》,謹守止庵(周濟)之說,其間特出之英,主壇坫,廣聲氣,宏獎借,妙裁成,在南則有復堂譚氏,在北則有半塘王氏,其提倡推衍之功不可沒也。”[6]陳乃乾《清名家詞序》又云:“毗陵二張,別標意內言外之旨,晉卿止庵,為之推衍發皇,半塘崛起,其實始副。”[7]三家大約論述了常州詞派發展的三個階段,即張惠言開派,周濟衍派,至王鵬運發揚光大之而臻于極盛。加以乾嘉考訂校讎之學的影響,詞家不斷編選前人的作品,評析訂正、審音酌字;詞的意境格律,更加成熟。此論龍榆生所作《晚近詞風之轉變》、《論常州詞派》等文章有深入闡發。常州詞派的發展過程也正是詞體日尊的過程,也是“詞史”觀念不斷流衍、深入人心的過程。這一過程首先是理論的建樹,標準的設立,其次是創作過程的自覺表現,以及理論指導下詞作藝術性的不斷提高。詞史范疇的建構體現的是詞學理論的自覺,是詞學發展的本身內部規律的自然過程。
(三)晚清的詞史意識指導著創作實踐活動,成為晚清詞人創作的自覺追求。
晚清的詞史意識不僅是理論的自覺建構,還深入指導著創作實踐活動,成為晚清詞人的自覺追求。晚清詞家身處亂世,他們不僅用詩歌、小說、散文記錄著社會的變遷、國家的變亂和民族的危機,寄寓個人的思考和感情。詞也成為他們熟練使用的一種文體,從而用詞記錄下這一家國天下的巨變。于是海內詞人,感時倚聲,猶有可觀者,國家大事,畢見于令慢之中,托諷顯微,不愧詞史。這一時期,作家群體也非常復雜,既有顯赫的朝廷命官,如鄧廷楨、林則徐等鴉片戰爭中涌現出來的民族英雄,他們的詞真實的記錄了當時親身經歷的歷史事件;也有詞壇的耆宿,如蔣春霖、王鵬運、朱祖謀、文廷式等詞學大家,在他們的詞中反映了當時的國政如何混亂,民生如何凋敝,國家如何遭受外族侵略;也有一些普通的讀書人,在民族危亡之時,挺身而出,除了英勇的跟侵略者斗爭,也用他們的筆觸記錄了下層百姓苦難的生活以及喜怒哀樂。庚子事變,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挾光緒帝出逃,生靈涂炭,慘不忍睹。當時王鵬運、朱祖謀等詞人困居北京城中,親眼目睹了八國聯軍的燒殺搶掠等罪惡行徑,他們寫成《庚子秋詞》一卷,最著名的有王鵬運的《鷓鴣天》、《眼兒媚》、《南歌子》,朱祖謀的《聲聲慢》等。趙椿年書大鶴山人《謁金門》詞后云:“樵風自戊戌后出都,旋卜筑吳門,庚子秋彊村、半塘、伯崇諸君留滯都下,圍城中相約填詞遣日,日限一闋,脫稿后彊村即分箋抄示夏孫桐閏枝,收入《刻燭零音》,后刊為《庚子秋詞》一卷,顧無樵風和章。今讀斯詞,每闕均有‘不忍思君顏色’、‘問君蹤跡’、‘問君消息’之句,沉郁悲涼,如《伊州》之曲,殆即斯時亂中聞訊之作。”[8]此段話就記錄了王鵬運、朱祖謀等人在庚子事變時困居京城,以詞寫哀的,以及與遠在蘇州幕府的鄭文焯往還唱和的事情。而王鵬運自己說來卻沉痛的多。他在與鄭文焯的書信中說:“困處危城中已余兩月,如在萬丈深井中。望天末故人,不啻白鶴朱霞,翱翔云表。又嘗與古微言,當此時變,我叔問必有數十闕佳詞,若杜老天寶、至德間哀時感世之作,開倚聲家從來未有之境。”[9]王鵬運與朱祖謀諸人在庚子事變時被困在京城,即以詞寫下了這一事變的所見所感,成《庚子秋詞》一卷。這是他們自覺以“詞史”意識創作的結晶。而此時的鄭文焯隱退江南,王鵬運在欣羨鄭氏逍遙云表的同時,也期其能效杜甫安史之亂時創作反映時變的詞作。從這一事件也可以看出,詞史意識確實已經經由理論的建構而深入的滲入詞的創作領域,從而影響甚至指導著詞家的創作。
[1] 巨傳友.論臨桂詞派的詞史:精神[J].學術論壇,2007(1):172-173.
[2] 葉嘉瑩.論清代詞史觀念的形成[J].河北學刊,2003(4):123-129.
[3] 周密.介存齋論詞雜著.詞話叢編[M].北京:中華書局, 1986:1630.
[4] 張宏生.清初詞史:觀念的確立與建構[J].南京大學學報,2010(1):101-103.
[5] 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詞話叢編[M].北京:中華書局, 1986:3361.
[6] 蔣兆蘭.詞說.詞話叢編[M].北京:中華書局,1986:4638.
[7] 陳乃乾.清名家詞(卷十)[M].上海:上海書店,1982:244-563.
[8] 戴正誠.鄭叔問先生年譜[Z].民國三十年刊本.
[9] 陳水云.清代的詞史:意識[J].武漢大學學報,2001(5):614-616.
(責任編輯、校對:王文才)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Notion of Hist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i in Late Qing Dynasty
YU Guang-jie1,2, SU Tao2
(1. The Institute of Ancient Works Organization,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2. Tianjin City Vocational College, Tianjin 300250, China)
Notion of History in Ci originated from the spirit of poetry and educational tradition. And it had connections with the Notion of History in poetry. This kind of Ci broke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love" theme. It used the unique style, charming words, lyrical languages to reflect social reality, historical events and the scholars’ historic and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So it formed a trend of creation of History of C in late Qing Dynasty. Based on sorting out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of poetry and History of Ci, the analysis of the features of Notion of History in Ci in late Qing Dynasty is made to discuss the impact on Poetry and creation.
history of poetry; history of Ci; notion of history in Ci
2011-06-10
于廣杰(1982-),男,河北滄州人,博士研究生,天津城市職業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宋元明清文學。
I207.23
A
1009-9115(2012)01-002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