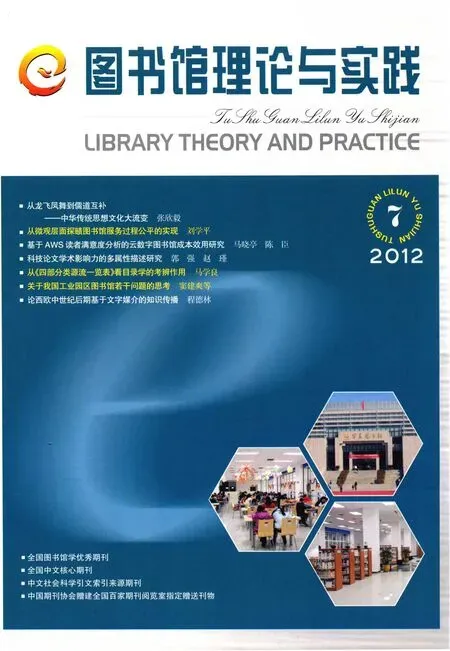從龍飛鳳舞到儒道互補——中華傳統思想文化大流變
●張欣毅(寧夏回族自治區圖書館,銀川 750011)
編者按:本期“特稿”欄目隆重推出寧夏圖書館常務副館長、本刊主編張欣毅研究館員的近期新作《從龍飛鳳舞到儒道互補》。是文也是作者近期赴國外舉辦的一個專場文化講座的稿本(參閱本期封二圖文介紹)。
張欣毅先生長期致力于本專業領域的基礎學科——文獻學之研究,逐步形成了文獻學與文化學雙向觀照的研究思路和學術風格,本世紀初年由他與丁力先生合作主創、榮獲全國第八屆“五個一工程”理論文獻專題片大獎的30集中華歷史文化電視專題片《跨越時空的文明》(簡稱《跨》片)是其這類研究的代表作。本期發文主要取材于《跨》片的《思想篇》(參閱本刊1997年第4期刊發的《跨》片文學本)。
在我國當代“文化強國”新國策中,圖書館事業已被明確納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如是居間,中華典籍普查、整理、保護及至數字化,或正在內化為某些基本業態,而深入發掘中華典籍的思想內涵以達當代“振民育德”之功或正在成為業界的一種職業文化自覺。本期“特稿”洵為這后一個方面富有建設性的“得意”之作。
話說“龍飛鳳舞”
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人類歷史的上古時期,出現了最早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古中國。我們現在常講,世界上也習慣了這樣的說法:中華文明5000年,大抵就是從“古中國”這個時期說起的。更有意義的是,在四大文明古國進而也就是在整個世界上,中國是唯一一個沒有發生文化斷層的國家。
今年,公元紀年的2012年,也是中國人傳統生肖紀年的龍年。從文化分層理論上講,生肖紀年、龍年之類當然是大眾文化層面的事情,但我們中國人、整個中華民族總是驕傲地自稱“龍的傳人”,顯然也說明,“龍”同時也是作為一種民族文化精神、文化傳統的符號化象征的且綿亙古今、跨越時空。
“圖騰”文化是人類上古時代及其以前的遠古時代的思想文化濫觴期的共同文化形態。“圖騰”,是借用印第安人的用語,意思是“我的親族”。就其表證的意義而論,當晚于自然崇拜、始祖英雄崇拜并綜合、融合了前者的文化要素。就中國人、中華民族的“龍圖騰”的起源、演變而言,它不僅僅是中華民族主體民族前身華夏族圖騰的抽象化,更重要的是它還有一個參照物、對應物—“鳳”圖騰。同樣更重要的是,龍與鳳都是一個想象物,按現在的說法,那是極富文化創意的。
“龍”圖騰的原型是“蛇”圖騰,“鳳”圖騰的原型是“鳥”圖騰。這可以從記載中國遠古圖騰文化最為豐厚、詳實的《山海經》中得到印證。按這本書的記載,大抵中國遠古傳說中的諸多先祖,如盤古、女媧、伏羲、軒轅等“皆人首蛇身”,帝俊、舜、少昊、后羿、蚩尤、商契等則多為“人首鳥身”。
近現代中國的諸多學者如郭沫若、聞一多等先生都認為,蛇—龍、鳥—鳳是遠古、上古中華大地上諸多部族聯盟長期征戰、兼并、融合歷史圖景在“圖騰”文化更高層面上的曲折反應。形象地說,以蛇為圖騰的部落(或聯盟)在與其他部落的長期征戰中不斷取得勝利。當征服了某一部落時,就把該部落的圖騰移植過來加在蛇身上。如此不斷取勝不斷增加,當這個劍眉虎眼、獅鼻鰱口、鹿角牛耳、蛇身鯉甲、鷲腳鷹爪、馬齒獠牙的“龍”的形象完成時,一個更為龐大的部落聯盟已經形成了。同理,當“鳳”這個有著雞頭、龍頸、燕頜、龜背、魚尾的五彩飛鳥的圖騰造就,也勢必標志著另一個同樣龐大的部落聯盟已經形成。
講“龍鳳圖騰”,當然可以講出太多太多的故事與傳說,但從梳理中華傳統思想文化大流變的視角說,“龍鳳圖騰”作為中華思想文化濫觴期的經典之作,我個人體會,至少有三個較大方面的認知意義與價值。
一是“龍鳳圖騰”與中華民族的自我認同有深層關聯。
當代的一些學者運用“人類遺傳血型學”的研究成果,對我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進行了全新角度的審視,發現并論證了中國遠古時代“民族”形成過程中存在著“血緣漩渦”現象。大意是:中華遠古大地上曾經存在過的若干血緣性氏族集團,從距今約1萬年前的時候開始,以黃河、長江中下游為地域中心,發生了大規模的“漩渦式”滾動遷徙及融合重組,進而形成了以華夏族(漢族前身)為主體的中華民族。
將“血緣漩渦形成中華民族”的動態歷史圖景與我們前面提到的“蛇—龍”“鳥—鳳”圖騰演變的歷史圖景重疊到一起,按史書的記載和近現代學術界的說法,大抵“蛇—龍”圖騰先是遠古中國東部后來是上古北部部落大聯盟的共同圖騰,“鳥—鳳”圖騰先是遠古中國西部后來是上古南部部落大聯盟的共同圖騰。《周易》上講“龍戰于野,其血玄黃”,當是對夏之立國和“商周革命”的歷史隱喻,《詩經》上就直接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從“龍鳳圖騰”的文化理性上講,它一方面深刻地昭示著,不但華夏民族從一開始就是多元融合的,而且中華民族共同體內的各古老民族也從一開始就是多元融合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龍鳳圖騰”是把始祖崇拜、圖騰崇拜用“血緣加地緣的二維框架文化意興化”了,因而,“同為龍的傳人”“同為炎黃子孫”就獲得了民族認同意義上的共通性。我們前面講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沒有發生過文化斷層的國家,“龍飛鳳舞”于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的中華民族的共同民族文化認同心理之中是一個極重要的原因。
二是“龍鳳圖騰”與中國的象形文化傳統有不解之緣。
龍飛鳳舞,這是飄揚在遠古華夏大地上的兩面圖騰巨纛。對這兩大圖騰文化思想內涵做更深層次的思考,一個比較精辟的說法是中國清朝大學者章學誠的“人心營構之象”一說。這大概可以看做是中國人傳統思維程式——“形而上”的最早的一個標本。我們現在的許多人在進行中西文化比較研究時,常愛說中國人擅長或喜愛形象思維、具象思維,疏于抽象思維。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誤解。象“龍”與“鳳”,應該說兼得形象與抽象、靜態與動態、感性與理性、形式與內容、“意會與言傳”等諸多對應性認知向度的。而正是依賴這種“一體兼得”的思維張力,“龍飛鳳舞”方能與同樣源遠深長的“易經八卦”、象形漢字一道成為標志中國人特有的思維表現方式——所謂“象形文化”的淵藪。這里的“象”,是“人心營構之象”,即精神外化之象;這里的“形”,是“形神兼備”“形意互見”之形。
三是“龍鳳圖騰”體現著中華民族的根本文化精神。
從我們前面極其梗概描述過的“蛇—龍”“鳥—鳳”圖騰演變史,除了前面講到的民族自我認同(民族向心力、凝聚力)和象形文化外,應該還能感受到這樣兩種中華民族最為難能可貴的民族共同精神:一是奮發有為、開拓進取,一是開放包容、精神認可。靠著包括這兩種具備根本性在內的民族文化精神,中華民族的文明史、文化史一方面能夠源遠流長、綿亙古今,一方面能夠既博大又精深,氣象萬千。這應該不是一個虛妄之言。
任何一個民族的根本民族精神大抵都是多元化、多樣化的。時間關系,這里不便展開討論。由于接下來要講到《易經》、講到孔孟和老莊,這里特別說一下中國歷史上被傳為美談的老子與孔子的“龍鳳會”。據說,孔子當年曾專門向老子求教關于“道”與“德”的問題。事后說:我見到了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他用龍來形容、稱贊老子靜動自如的神采和縱橫天地的思想。老子則說:“吾聞南方有鳥,取名為鳳,……左智右賢”,他用鳳來比喻孔子,贊嘆孔子具有智善和悅、仁德恭謙的品行。
話說《易經》
在外國朋友眼里,說中國古代的傳統文化,可能主要集中在3個“家”上,首推當然是“儒家”,即孔子創立、孟子光大的“孔孟儒學”;其次是“兵家”,即孫子領導的“兵法之家”;再次就是“道家”,即老子、莊子共同建立的“道家”學派。這當然是有道理的,孔孟儒學的精神旗幟是仁德禮治,專注于“治國治世”,是中國傳統的制度文化的綱領性的建構;“孫子兵家”集古代中國戰爭智慧、軍事文化之大成,在中國人眼里就是“玄武”之學;老莊“道學”更關心人世外的大千世界、宇宙自然、天文地理,是中國古人心目中的真正的哲學。殊不知,無論是儒家、兵家、道家,甚而“諸子百家”,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祖宗,一個共同的淵源,那就是《易經》。
在中國古人的文化理念中,所謂“哲學”就是“玄學”,屬于世界觀、方法論的“太極”“無極”境界。中國古人將《易經》視為“天下第一玄學”,足見其思想地位之高。
《易經》是后世參照宗教文化的觀念附會上去的名字。起初就單稱作《易》。“易”字是一個典型的象形、會意字,象上日下月之形,會日月變化之意,即變易。《易》的內容和功用主要是占卜問卦,預測兇吉、成敗,因此,《易》在性質上首先是一部巫史、巫術文化的記錄品。
傳說“伏羲始作八卦”。到了中國上古奴隸制時代的夏、商兩朝,巫史、巫術文化曾達到政教合一、無所不能的巔峰狀態。近世殷墟出土的數以萬片計的甲骨文又稱“卜辭”充分印證了這些。“卜辭”主要是占卜問卦的記錄,“易”則是“卦辭”與“爻辭”。形象地說,二者的關系一如現在學生們的作業與作業的參考答案的關系。傳說,夏、商、周三代《易》有三個較大的版本體系。這些都充分表明《易》在古代的巫史巫術文化中是十分盛行的。
《易》是卜巫之書還可以從后來秦始皇“焚書坑儒”未遭禁焚的事實中得到反證。《漢書》上說得明白:“及秦焚書,《易》以筮術之書獨不禁”。
往大一些講,《易》在夏商周的三個版本分別稱《連山》《歸藏》《周易》,據說主要是因為書中的八卦分別是從“艮”(山) 卦,坤(地) 卦、乾(天) 卦起始的,這同時又折射出上古華夏人在巫史巫術文化大的背景下從山林狩獵文明、農耕養殖文明到“天人合一”人文覺悟的“圖騰”式演化軌跡。或許,這就是歷史的辨證法。
十幾年前我曾主筆創作了一部30集的反映中華五千年歷史文化的電視文獻專題片《跨越時空的文明——中華五千年的文化記錄》。在創作過程中,我提出了中國古代“儒學”的“三級跳”的觀點。比附這個說法,我體會中國古代的“玄學”(即“形而上”之學,哲學)演變也存在著一個類似的“三級跳”的歷史過程。
中國古代“玄學三級跳”的第一跳,代表作就是《周易》。站在中華傳統思想文化大流變和中華傳統文化宏觀體系“頂層設計”雙向觀照的高度上看,作為“玄學第一跳”代表作的《周易》,應該說同時具有兩個方面的“里程碑”意義和價值:一是標志著中國上古三代巫史巫術文化登峰造極后的“盛極而衰”,一是標志著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宏觀體系以“君本為主導的人本主義”作宏大建構的開端。
這里側重說說第一個方面的意義與價值。
如果今天的人們能夠把殷墟出土的《卜辭》、殷商青銅禮器和那個時代的經典如《尚書·商書》弄清楚,人們一定會驚訝那時的中國的巫史巫術文化(原始宗教)之狂熱之霸道之登峰造極,同時也應該有一個基本的推理:接下來的西周大王朝理應把巫史巫術文化推到一個更高的境界。但中國人的思想史恰恰在這個時候竟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當然,從時間跨度上,這個大轉彎是漫長的,從周初到春秋歷六七百年,同時也是曲折的,充滿了太多的傳奇色彩。
在這段充滿傳奇、波瀾壯闊的歷史中,從周“文王拘而演《周易》”、《尚書》對“陰陽五行學說”的記載與闡發,到孔子刪定《周易》、老子與“春秋諸子”對“易經”的“理一分殊式”解讀,《周易》終于“涅槃重生”般地獲得了中華民族大文化的第一經典的極大升華。
從中西方歷史文化比較上看,中國的春秋戰國到秦漢兩朝的八百多年間,世界上的幾大文明古國大抵都在向封建社會過渡。同時,他們大都在原始巫術宗教的基礎上形成了封建神權統治的社會,即所謂“黑暗的中世紀”。與當時的西方(主要是歐洲)和東方的印度、古波斯的宗教興起的大勢恰好相反,古中國卻奇跡般的擺脫了“封建神權一統天下”的軌道。
在接下來的中國歷史進程中,歷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確實也發生過無數次的“封建造神”運動,尤其是經歷過道教的興衰消長,外來宗教如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強勢宗教的反復沖擊,但中國的“以君本為主導的人本主義”的思想文化體系卻從來沒有崩潰過,相反,卻以《周易》、孔孟儒學、老莊道學、先秦諸子共同筑起的思想文化根脈的綿綿內力將之化為無形。
概而言之,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周易》最重要的里程碑意義就在于終結了一個歷史,同時,又開啟了一個歷史、滋養了一個歷史。終結的那個歷史,如果可以稱作“圖騰異化”的歷史,那么,開啟的歷史、滋養的歷史,也可以稱作“龍飛鳳舞”的歷史。因為,《周易》的核心是“陰陽”,而龍與鳳便是“陰陽”的大隱喻、大寫意、大化身。
話說“儒道互補”
我們前面提到的《周易》作為“玄學第一跳”代表作的第二個方面的“里程碑”意義與價值,須得聯系列孔孟儒學和老子道學來說,因為,《周易》作為“第一跳”的落點是與孔孟儒學的“第一跳”合二為一的,而中國古代“玄學”的“第二跳”其實就是老莊道學的橫空出世。
《周易》由周文王所創大概是無疑問的,《周易》又在相隔數百年后的孔子手里得以刪定也應該是無疑問的。這就意味著《周易》是當時的幾代大思想家共同完成的。后世把《周易》改稱為《易經》,置于孔孟儒學六大經典之首,足見它在整個儒學體系中的崇高地位。
不獨有偶。后世被同時尊為“儒家六經”的另5部,即:《尚書》(亦稱《書經》)《詩經》《禮經》《樂經》《春秋經》,大抵都是在西周時期成型,最終在孔子手上完成定稿的。從這個意義上看,說孔孟儒學是西周時期甚而上古三代華夏多元文化精華的集大成者應該是不過份的。
當然更重要的是繼往后的開來。孔子自言:吾道一以貫之。這個“道”,在《周易》里就是“天命論”“天道觀”和“君子之道”;在《尚書》《春秋》中就是影響中國2000年封建社會政治結構的“大宗法制度”和國家統一大業的“正統史觀”;在《禮》《詩》《樂》中,便是影響更為深遠重大的封建禮制。如果說,以“仁”為核心、以“禮”為形式、以“中庸”為尺度是孔孟儒學最本質特征,那么,仁、義、禮、智、信、忠、孝、節、悌便是孔孟儒學奉獻給整個中華民族、全體中國人的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足以鍛造“中華”之國魂與民族脊梁。關于孔孟儒學中的“儒”字,歷來有兩種解釋。一是古代相禮之人,猶如現在的“司儀”之職。一是大學者、大學問者。這里我想按象形文化的思維方式提出第三種解釋:人最需要的人。在我心目中,至少孔子、孟子是真正意義上的仁德圣賢之人,原汁原味的孔孟儒學更是真正的“人學”,事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事關對人對人的社會的全面的“終極人文關懷”。
史載:“孔子晚而喜《易》,韋編三絕,曰:假我以數年則于《易》彬彬矣”。這顯然意味著孔子晚年對其創立的儒學的某些缺陷、缺失是有所反思的,只是天不假年,難以再有大的作為了。那么,孔孟儒學整體架構上究竟有哪些缺陷與缺失呢?如果站在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大流變的高度,其實答案是明確的。總體上講,孔孟儒學也講“道”,卻主要長于治世之道、倫理之道,疏于對天道和自然之道的關注與研究。按現在的說法,孔孟儒學更關注社會科學、人文科學,而疏于自然科學。而孔孟儒學之短又恰恰是老子道學之長。這大概是“儒道互補”能成為秦漢以后中國兩千多年傳統思想文化大流變中的一條重要脈絡的最大原因。
從時間順序上,先秦諸子,首推老子。傳說老子西出函谷關隱退前遺書《道德經》(又稱《老子》),雖僅5000字,卻包容了老子哲學思想的全部立論,以閃爍著不朽光芒的“天道自然”學說豎起了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繼《易》之后第二面哲學“元”理論的巨纛,而《列子》《揚子》特別是《莊子》則進一步在“道之法則”上開拓,完成了“道法自然”的宏大哲思。老子、莊子被現代的西方學者稱為古代東方的先哲,想來并非過譽。
中國古代思想界、文史界一般把《易經》《老子》《莊子》合稱為“三玄”,這當然是對它們分別所達到的哲學認知高度的無上贊許了。而在我看來,因為老莊道學是一個整體,又相對獨立于《周易》或者說直接來源于老子應該看到的那個原初的《易》,說老莊道學是中國古代“玄學三級跳”中的“第二跳”應該也是成立的。
“玄學三級跳”的“第三跳”當然就是被現代中國哲學界視為“清流階段”的魏晉玄學。這里的所謂“清流”,我體會也應該有兩層意思。一是形容魏晉玄學家們“越名教任自然”,一如古希臘思想家們將哲學視為“熱愛智慧”一般,在當時與洶涌而至的具有極高哲學水準的佛教哲學的交流與對話中,自覺地追求中國本土哲學無上的“清高”境界;另一方面也可專指魏晉玄學家們以前所未有的思想熱情、嚴肅態度,自覺地對中國本土思想文化的三大主流體系《易》儒道進行徹底的、全方位的“清理”。在這兩種思想文化取向的共同作用下,易學、孔孟儒學、老莊道學最高貴、最精華的哲學“元”建構第一次真正走到了一起、融合到了一起。甚至,在魏晉玄學里,不但易、儒、道是互補而共存的,中土之學與外來的佛教哲學也第一次達到了真正意義上的“互補”與“共存”。
講中國古代的“儒道互補”,除了魏晉玄學這種最為典型的“認知模式”外,大體上還可以有三個較大的“認知模式”。
先說“儒學三級跳”與“玄學三級跳”在大時空意義上的交錯與并行體現出來的“儒道互補”。如果說,《周易》與儒學立派這“第一跳”還錯綜復雜地膠著在一起,那么,在西漢武帝時期“獨尊儒術”這“儒學第二跳”之前,以“黃老學派”面目出現的老莊道學至少已有近百年的尊崇與風光;如果把魏晉玄學視為“玄學第三跳”,那么,它又先于程朱理學在宋朝時再定“獨尊”這個“儒學第三跳”,在東晉尤其是大唐王朝數百年間雄踞“中央官學之尊”。史載,東晉太元年間,魏晉玄學第一圣王弼的《周易注》就曾正式列為國學教本。有唐一朝,中央官學規模宏大,有著名的“六學二館”和“東西崇玄學”。其前者,即“儒學”等“六學”歸禮部下屬的國子監管理,而“東西崇玄學”則直接由唐中央最高行政機構“尚書省”管理,足見唐時“玄學”地位之獨尊。如果再往深里說,宋元明三朝,以程朱理學面目出現的“儒學”被尊為官學之首,與之并存的張王氣學、陸王心學也廣有市場。理學、氣學、心學雖然都打著孔儒之學的旗號,但在他們各自的思想體系中,其實早已分不出什么是《易》,什么是儒與道了。
再說說中國古代大眾思想文化層面上的“儒道互補”,特別是“士”階層(相當于今天的知識精英階層),這一傾向則更為明顯。表面看來,儒道是離異而對立的,一個入世,一個出世;一個樂觀進取,一個消極退避,但實際上,他們剛好相互補充而協調。不但“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經常是后世士夫們的互補人生模式,而且悲歌慷慨與憤世疾俗、“身在江湖”與“心懷廟堂”也經常是中國歷代知識分子的常規心理和文化心態。
再說說“各領風騷”這一綿亙數千年的“儒道互補”文化意興。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這里的“風”原指先秦《詩經》中的“十五國風”,“騷”原指戰國時期南方楚國(今湖北省一帶)偉大詩人屈原創作的抒情長詩《離騷》。西歷今年的6月23日是中國農歷的端午節(也稱端陽節)。中國民間有在這一天吃粽子、賽龍舟的習俗,相傳就是為了紀念屈原于公元前278年農歷五月五日投汨羅江以身殉國,足見屈原和他的《離騷》在中國傳統文化傳承體系中的特殊而深遠的影響。
站在“儒道互補”的視角,可以說,“風”、“騷”也代表著中國這一“詩國”中以“詩歌”為載體且橫貫宮廷文化、士文化、民俗文化的兩種思想文化追求之極致。《詩經》是儒家經典之一,“風”“雅”“頌”是《詩經》的三種基本類型。所以,“風”就是集龍圖騰文化、先秦北方“理性主義”地域文化、儒家“詩言志,文載道”的文化藝術傾向等于一身的一種文化“標桿”。與前面講過的“儒學第一跳”和“玄學第二跳”同期,屈原和他的《離騷》則是集鳳圖騰文化、先秦南方“浪漫主義”地域文化、老莊道學“高尚其事,不事王侯”文藝旨趣為一身的另一種文化標桿。既然中國人講究和推崇“各領風騷”,當然就意味著在更加深刻而廣泛的層面上追求“儒道互補而共榮”。
站在當今中國與世界思想文化交流與對話的視角,我們似乎也可以按現在世界上廣為流行的認知科學的先進理念,把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大流變中的“儒道互補”理解成某種“吁請結構”。過去的“佛教中國化”、“伊斯蘭教中國化”,近代的“基督教中國化”,現在的“西方文化中國化”“世界文化中國化”,大概都可以看做是“儒道互補”這一“吁請結構”的某種“理一分殊”。
最后,我愿引用孔子在《周易》里說過的三句至理名言做結束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我體會,它們是中華思想文化從龍飛鳳舞到儒道互補大流變中的三大主基調或言三大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