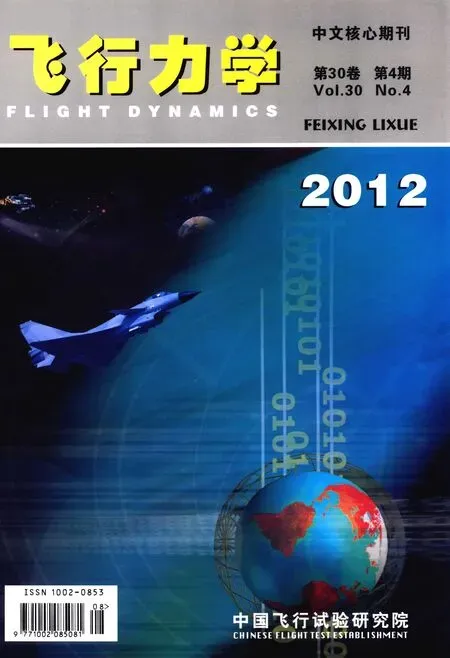導(dǎo)彈的直接力/氣動力控制系統(tǒng)設(shè)計
楊文駿,張科,張云璐
(西北工業(yè)大學(xué)航天學(xué)院,陜西西安 710072)
引言
臨近空間一般指的是距地面20~100 km,普通航空器飛行空間與衛(wèi)星軌道之間的空域[1],與普遍認(rèn)為的大氣層不同,臨近空間大氣稀薄,在該空域飛行的飛行器所能獲得的氣動過載較小[2]。現(xiàn)代戰(zhàn)爭中除了大量使用巡航導(dǎo)彈、戰(zhàn)術(shù)彈道導(dǎo)彈和超高空偵察機(jī)等,還要面對遠(yuǎn)程洲際彈道導(dǎo)彈的威脅[3]。這些武器都有顯著的特點:大部分飛行時間都處于臨近空間范圍內(nèi);飛行馬赫數(shù)高;機(jī)動性強(qiáng)。這就對超高空防空導(dǎo)彈提出了更高的制導(dǎo)控制精度要求,因此引入直接側(cè)向力控制技術(shù),能夠滿足導(dǎo)彈機(jī)動過載需要,降低制導(dǎo)控制系統(tǒng)的過載響應(yīng)時間,有利于提高防空導(dǎo)彈的制導(dǎo)控制精度。
文中以某臨近空間防空導(dǎo)彈為背景,引入直接力進(jìn)行導(dǎo)彈末端直接力控制,形成了直接力/氣動力復(fù)合控制系統(tǒng),并通過仿真計算分析了系統(tǒng)性能。
1 導(dǎo)彈氣動控制系統(tǒng)
1.1 氣動控制系統(tǒng)數(shù)學(xué)模型
彈體的運動可看成其質(zhì)心移動和繞質(zhì)心轉(zhuǎn)動的合成運動,可用牛頓定律和動量矩定律來研究。但導(dǎo)彈并不是一個剛體,其運動比剛體的運動復(fù)雜的多,為使問題簡化,在此作如下假設(shè):
(1)略去導(dǎo)彈變形、質(zhì)量變化等因素,引入“固化原理”,把導(dǎo)彈當(dāng)作質(zhì)量恒定的非形變物體;
(2)轉(zhuǎn)動慣量恒定,推力和重力作為外力;
(3)引入小擾動假定,忽略二階以上的微量以及氣動力、氣動力矩的次要因素;
(4)在擾動過程中認(rèn)為未擾動參量是不變的,可由彈道計算結(jié)果中直接取得;
(5)導(dǎo)彈為軸對稱,側(cè)向運動參量與縱向相比為微小量。
采用固化系數(shù)法,選擇彈道中有代表性的特征點進(jìn)行研究,研究區(qū)間只限于短周期,忽略未知量和小項,可得導(dǎo)彈簡化的縱向周期擾動運動方程組為:

偏航通道與俯仰通道對稱,故偏航通道傳遞函數(shù)不再進(jìn)行推導(dǎo)。
同理可得到滾動運動的擾動運動方程組為:

狀態(tài)方程為:

上述式(1)~式(5)中各符號含義參見文獻(xiàn)[4]。
導(dǎo)彈采用過載控制,只控制導(dǎo)彈的俯仰和偏航兩個通道,導(dǎo)彈在導(dǎo)引律的引導(dǎo)下向指定目標(biāo)飛行。
1.2 導(dǎo)彈控制系統(tǒng)設(shè)計
設(shè)被控系統(tǒng)S0的狀態(tài)方程為:

根據(jù)該狀態(tài)方程,可以配置出理想的極點位置,計算出所希望的配置極點位置的反饋矩陣k。
2 直接力控制系統(tǒng)設(shè)計
常規(guī)防空導(dǎo)彈是靠空氣舵實施對導(dǎo)彈的控制,時間常數(shù)在150~350 ms,這在目標(biāo)高速、大機(jī)動的條件下難以保證高控制精度[5]。但是在氣動力/直接力復(fù)合控制的導(dǎo)彈中,直接力裝置的時間常數(shù)一般在5~20 ms[6]。因此在氣動力基礎(chǔ)上疊加直接力控制,能夠增強(qiáng)導(dǎo)彈在超高空末制導(dǎo)末段的機(jī)動性,可以高精度地命中目標(biāo)。
2.1 直接力裝置操縱方式的選取
一般地,導(dǎo)彈的直接力裝置可以有三種不同的操縱方式:姿控方式、軌控方式和姿軌控方式。由于操縱方式不同,在導(dǎo)彈上的安裝位置不同,因此提高導(dǎo)彈控制力的動態(tài)響應(yīng)速度的原理也是不同的。
姿控方式(力矩操縱方式)和軌控方式(力操縱方式)的原理可參見文獻(xiàn)[7],其示意圖如圖1和圖2所示。

圖1 力矩操縱方式

圖2 力操縱方式
姿軌控方式的側(cè)向力作用時間較長,在改變姿態(tài)的同時,也會產(chǎn)生較為明顯的側(cè)向機(jī)動加速度。
由于姿控方式首先改變導(dǎo)彈的姿態(tài)角,繼而改變導(dǎo)彈的運行軌跡,讓導(dǎo)彈快速機(jī)動,控制效果明顯,但數(shù)學(xué)模型涉及導(dǎo)彈6個自由度,較為復(fù)雜;軌控方式并不改變導(dǎo)彈姿態(tài)角,而直接改變導(dǎo)彈的運動軌跡,數(shù)學(xué)模型較為簡單,效果也很明顯;而姿軌控方式的數(shù)學(xué)模型建立要更為復(fù)雜一些。因此綜合考慮,采取了軌控的直接力控制方式。
以AIM-120作為外形參考,在導(dǎo)彈的第二級質(zhì)心位置放置直接力裝置,其外形如圖3所示。

圖3 導(dǎo)彈外形簡易示意圖
2.2 直接力控制系統(tǒng)數(shù)學(xué)模型
直接力控制系統(tǒng)在之前并不工作,只在末制導(dǎo)末段,當(dāng)導(dǎo)彈氣動控制系統(tǒng)所提供的過載不能滿足擊中目標(biāo)的制導(dǎo)精度后,再開啟直接力控制系統(tǒng)。
以彈目相對距離dis作為直接力控制系統(tǒng)開啟的識別參數(shù)。Rd表示允許直接力控制系統(tǒng)彈目相對距離,根據(jù)具體條件,設(shè)置Rd=10 km。當(dāng)彈目距離dis>Rd時,直接力控制系統(tǒng)一直是關(guān)閉的;當(dāng)dis≤Rd時,開啟直接力控制系統(tǒng)。
直接力控制系統(tǒng)的參考輸入為導(dǎo)彈的俯仰和偏航兩個通道的需用過載nc和氣動舵所能提供的最大氣動過載nm。當(dāng)nc≤nm時,表明氣動舵所提供的氣動過載能夠滿足此時導(dǎo)彈的過載需求,故直接力控制系統(tǒng)此時雖為開啟狀態(tài),但直接力發(fā)動機(jī)并不工作,不輸出脈沖直接力;當(dāng)nc>nm時,表明氣動舵所提供的氣動過載不能滿足此時導(dǎo)彈的過載需求,故直接力發(fā)動機(jī)工作,輸出脈沖直接力。其控制流程如圖4所示。

圖4 直接力控制流程圖
設(shè)脈沖直接力為Tc,其控制規(guī)律如下:
當(dāng)dis>Rd時,Tc=0;

直接疊加導(dǎo)彈直接力和氣動力的控制作用,形成直接力/氣動力復(fù)合控制系統(tǒng),可有效地增大導(dǎo)彈的可用過載,具體的指令型復(fù)合控制器形式如圖5所示。

圖5 指令型復(fù)合控制器
圖中,K0為歸一化增益;K1為氣動控制信號混合比;K2為直接力控制信號混合比。通過合理優(yōu)化控制信號混合比,可以得到最佳控制性能。
2.3 直接力發(fā)動機(jī)性能估算
固體脈沖發(fā)動機(jī)工作時間極短,推力大,且要求點火延遲、燃燒時間和總沖散布小,因此宜采用高燃速推進(jìn)劑。
根據(jù)質(zhì)量分析及經(jīng)驗公式粗略估算可知:
(1)直接力機(jī)構(gòu)總質(zhì)量為19.1 kg;
(2)藥柱質(zhì)量為11.62 kg;
(3)直接力機(jī)構(gòu)總沖為25 094 N·s;
(4)單方向總沖為6 274 N·s。
考慮導(dǎo)彈末制導(dǎo)末段,直接力控制系統(tǒng)已開啟,導(dǎo)彈與目標(biāo)速度均較大,假定此時目標(biāo)速度為Ma=5,導(dǎo)彈速度為Ma=5,則相對速度最大為Ma=11,而之前設(shè)置了Rd=10 km,因此可估算末段攻擊時間:

假定:(1)每個方向直接力機(jī)構(gòu)提供軌控力的持續(xù)時間te=2 s;(2)燃燒劑采用電子點火脈沖方式燃燒,燃燒占空比為50%;(3)每片燃燒劑燃燒時間為20 ms;(4)每組發(fā)動機(jī)有4個平行裝藥筒,每個方向有兩組發(fā)動機(jī)。
經(jīng)分析,直接力裝置可以采用8組固體發(fā)動機(jī)結(jié)構(gòu),在導(dǎo)彈第二級質(zhì)心位置縱向互相垂直的4個方向提供推力控制,每個方向為2組發(fā)動機(jī),工作時同一方向上的2組發(fā)動機(jī)同時提供推力。
通過計算可得直接力機(jī)構(gòu)參數(shù)如表1所示。

表1 直接力機(jī)構(gòu)參數(shù)
3 仿真結(jié)果及分析
假定目標(biāo)在臨近空間區(qū)域內(nèi)做高速巡航飛行,并作“S”形機(jī)動,發(fā)現(xiàn)目標(biāo)后,戰(zhàn)機(jī)攜帶導(dǎo)彈到一定高度發(fā)射,攔截目標(biāo),具體的仿真流程和仿真初始參數(shù)如圖6、表2所示。

圖6 仿真流程圖

表2 仿真初始參數(shù)
使用上述條件的仿真結(jié)果如圖7~圖11所示。

圖7 導(dǎo)彈和目標(biāo)的三維飛行軌跡

圖8 導(dǎo)彈俯仰和偏航通道過載
圖7所示的是導(dǎo)彈和目標(biāo)的飛行軌跡。圖8為導(dǎo)彈俯仰和偏航通道的過載大小隨時間變化的曲線圖,其縱坐標(biāo)的正負(fù)號代表相反的兩個方向。不難看出,在末制導(dǎo)末段,直接力控制系統(tǒng)處于開啟狀態(tài),導(dǎo)彈的需用過載隨時都可能超出導(dǎo)彈氣動控制系統(tǒng)所能提供的最大過載(=10),當(dāng)需用過載大于10時,直接力裝置開機(jī),輸出脈沖直接力,直接與氣動過載疊加,形成氣動力/直接力復(fù)合控制,增強(qiáng)了導(dǎo)彈末端的機(jī)動能力,提高了制導(dǎo)精度,導(dǎo)彈才得以成功擊中目標(biāo)。
圖9為導(dǎo)彈俯仰和偏航兩個通道所輸出的直接力過載曲線。從圖中可以看出,直接力控制系統(tǒng)輸出的是脈沖直接力,其過載為6,周期為40 ms,占空比為50%,符合所設(shè)計的直接力控制系統(tǒng)的要求。

圖9 導(dǎo)彈的直接力過載
現(xiàn)在同等條件下,將直接力控制系統(tǒng)的作用去掉,再進(jìn)行仿真,其仿真結(jié)果如圖10、圖11所示。

圖10 導(dǎo)彈和目標(biāo)的飛行軌跡

圖11 導(dǎo)彈俯仰和偏航通道過載
由圖10和圖11可以看出,同等條件下,去掉直接力控制系統(tǒng)之后,在末制導(dǎo)末段,由于大氣稀薄以及氣動舵自身強(qiáng)度等因素,最大為10的氣動過載并不能滿足需用過載的要求,又沒有脈沖直接力的彌補(bǔ),導(dǎo)致導(dǎo)彈末端機(jī)動能力不強(qiáng),未能擊中目標(biāo)。
從上述仿真結(jié)果可以看出,文中所設(shè)計的導(dǎo)彈直接力/氣動力復(fù)合控制系統(tǒng),使得導(dǎo)彈在大氣稀薄、氣動力提供不足的臨近空間區(qū)域有更強(qiáng)的機(jī)動能力,可以成功地攔截目標(biāo)。
4 結(jié)束語
文中以某臨近空間防空導(dǎo)彈為背景,設(shè)計了導(dǎo)彈的直接力/氣動力復(fù)合控制系統(tǒng)。在所建立的數(shù)學(xué)模型基礎(chǔ)上,運用MATLAB/Simulink平臺,對導(dǎo)彈攔截目標(biāo)的過程進(jìn)行了仿真。導(dǎo)彈在處于臨近空間這樣的大氣稀薄區(qū)域時,該復(fù)合控制系統(tǒng)可提供更多的機(jī)動過載,能夠滿足導(dǎo)彈需用過載的要求,增強(qiáng)了導(dǎo)彈的機(jī)動能力,提高了導(dǎo)彈的制導(dǎo)精度,使得導(dǎo)彈能夠成功地攔截高空目標(biāo),相比于其他沒有直接力控制系統(tǒng)的導(dǎo)彈具有更大的優(yōu)勢。
[1] 李楨,李海陽,雍恩米.臨近空間動能武器彈道特性分析[J].彈箭與制導(dǎo)學(xué)報,2009,29(3):183-185.
[2] Marcus Young,2d Lt Stephanie Keith,Anthony Pancotti.An overview of advanced concepts for near space systems[C]//45th AIAA/ASME/SAE/ASEE Joint Propulsion Conference & Exhibit.Denver,Colorado,USA,2009.
[3] 李錚,趙大勇.美軍臨近空間平臺的開發(fā)利用及對我軍的啟示[J].火力與指揮控制,2009,34(8):2-3.
[4] 錢杏芳,林瑞雄,趙亞男.導(dǎo)彈飛行力學(xué)[M].北京:北京理工大學(xué)出版社,2000.
[5] David B Doman,Brian JGamble,Anhtuan D Ngo.Quantized control allocation of reaction control jets and aerodynamic control surfaces[J].Journal of Guidance,Control,and Dynamics,2009,32(1):13-24.
[6] 朱龍魁.防空導(dǎo)彈直接力和氣動力復(fù)合控制技術(shù)研究[D].長沙:國防科學(xué)技術(shù)大學(xué),2008.
[7] 楊軍,楊晨,段朝陽,等.現(xiàn)代導(dǎo)彈制導(dǎo)控制系統(tǒng)設(shè)計[M].北京:航空工業(yè)出版社,2005.